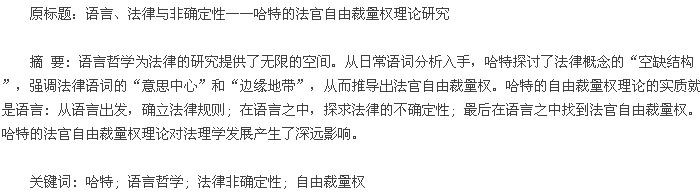
从语言到法律规则是哈特探讨法律问题的基本思路,哈特对法律语词的分析展示了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在法学领域的无限空间。哈特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理论正是植根于其对语言、法律概念、法律规则的研究之中,是其法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哈特从日常语词分析入手,探讨法律概念的“空缺结构”,强调法律语词的“意思中心”和“边缘地带”,是其推导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逻辑前提,也是其法官自由裁量权理论的基本内容。采用一种描述社会学方法探讨语词各种使用背景,实际是在于建构法官诠释与理解法律的一种方式。总之,把法官自由裁量权纠缠在语言之中,是哈特法理学及其法官自由裁量权理论一个最为显着的特征。探讨哈特自由裁量权的有关理论,对进一步认识 20 世纪西方法理学重要问题以及对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基本思路是从哈特法律思想的哲学基础着手,深刻分析其逻辑论证过程以及最终结论。从表面看来,哈特直接论述法官自由裁量权问题的地方不多,但从实质内容来看,法官自由裁量权问题始终是哈特法律思想的基本隐含,是其理论推导的必然。
一、从语言到法律: 哈特分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基本进路
1953 年哈特发表了题为“法学中的定义及理论”( Definition and Theory in Jurisprudence) 的就职演说,这标志着日常语言哲学运用到法理学研究中的开始,成为战后实证主义法学的方法论,并导致了一场新的法学运动。1961 年,哈特的代表作《法律的概念》一书出版,该书直接开启了法律实证主义的新时代。他在这本重要着作的“序言”中,明确交代了他所使用的日常语言哲学的立场和方法。他指出: “本书研究的中心论题是: 如果没有理解不同陈述之间的某些核心差别,就无法理解法律或社会结构形式———我把这两种陈述称之为‘内在的’陈述和‘外在的’陈述。只要社会规则得到了遵守,这两种陈述就存在。”当然,仅仅探究语词的含义也不足为训。对于语词的区别及其使用方法的探究,离不开社会背景、社会关系的分析。因此正如奥斯丁( J.L. Austin) 所言: “我们正是通过加深对语词的认识与理解,来加深对社会现象的理解。”[1]序言通过对语词的深化认识去加深我们对法律现象的理解,成为哈特法学理论的基本思路。《法律的概念》充满了对语词“使用”的讨论。在该书第一章“纠缠不休的问题”中,哈特详细讨论了定义的界定方法。顾名思义,定义就是运用独立的语词对事物给出语言上的界说。一方面,定义就是关于语词的正确用法,另一方面,定义所使用的语词与事物发生关联,正是这些语词不断表达着事物的特征。于是,定义就成了用其他易懂的语词取代定义该词的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事物的特征不断得到呈现。
哈特认为,法律的词语并没有确定的、一成不变的意义,而是依其被使用的环境、条件和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只有弄清这些词语、概念被使用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和方式,方能确定它们的意义。哈特严厉批判了法学中传统的定义方法,指出人们不要抽象地回答“什么是法律?”“什么是法人”之类的问题,而应当通过弄清这些概念被使用的背景和条件去阐释它们[2]13 -16。哈特的理论深受语言哲学的影响,他本人是语言哲学中“牛津学派”核心成员之一。据哈特自己的介绍,二战后他在牛津教授了 7 年哲学,而那时正是语言哲学在牛津和剑桥最有影响的时期。
自然,他将当时流行于牛津大学哲学系的语言哲学纳入他的法学方法论中。哈特运用语言哲学来分析法律语词及其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的理论基础,是哈特对法理学的重要贡献。就法官自由裁量权理论哲学根基而言,哈特与维特根斯坦( Wittgenstein) 、威斯曼( Weismann) 、奥斯丁( J. L. Austin) 等语言哲学家的思想一脉相承。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认为,词语的功能是指向某物,用作世界上真实事物的真实写照。
一言以蔽之,语言描绘了现实。这种语言指示理论认为每个词都有一个固定的意义,这种意义和语言相互关联,实际上是语言所代表的物体。威斯曼的许多思想源于维特根斯坦中后期的哲学思想,而威斯曼对哈特的理论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威斯曼用一种更加易于理解的形式展现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并且对维特根斯坦的许多概念都作了一些实质性拓展。威斯曼和维特根斯坦一样,不赞成语言的形而上学实在论者的方法,但与许多非形而上学实在论方法保持一定距离[2]。
哈特提出“空缺结构”这一重要法律概念,就深受威斯曼的影响。在威斯曼那里,“空缺结构”被用来阐释可证实理论( verification theory) 的一个特殊问题。他认为,正是因为“空缺结构”是经验性概念,因此,物质对象的陈述不能转化为感觉材料的陈述。同时,经验性陈述也就不能被最终证实[3]。虽然可证实性是威斯曼分析“空缺结构”的语境,但是“空缺结构”这个概念不仅仅是可证实性问题。事实上,威斯曼在其着作《语言哲学的原则》一书中更多的是在哲学上关注陈述的有效性以及规则不圆满性。他在论述“空缺结构”时说: “任何时代的法律需要适应当时具有支配性地位的特征、趋势、习惯于需求。有人认为法则是一个恒久的、封闭的制度体系,能解决所有能想象得到的问题,事实上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根基的乌托邦式的幻想。事实上,每个法则体系都有漏洞。……因为语言不会为所有的可能性做出准备,哀叹语言缺陷只会导致误导。”[4]总体而言,哈特的法理思想与上述哲学思想一脉相承,他们都赞成: 概念无法被完全地界定,或全面地限制,或充分地证实。就哈特的法律与语言的关系观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1) 语境原则。( 2) 多样性原则。( 3) 语言的模糊性。( 4) 语言的施事效用。这四个方面都从不同角度隐射了法官自由权的存在空间。哈特正是以语言哲学为基础,完成了“描述性”的法律概念,最终证成了他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理论。这是哈特分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基本进路。
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显现: 哈特通过语言分析法律问题的尝试
哈特在《法律的概念》等着述中列举了大量的语词,并且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对这些语词进行了独到而生动的分析,这些分析显现着哈特的思维模式以及推理过程,隐含着法官自由裁量的可能性空间。现在此罗列一些他对这些语词的分析,一是再现哈特的分析法官自由裁量权问题的独特视角; 二是印证笔者的观点,即法官自由裁量权是哈特法学理论一个暗含和必然的结论。法律规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普遍性,也就是说法律规则针对的不是某一个人作出个别的指示,而是针对整个社会成员作出一般性的指示; 法律规则所指向的是多类人、多类行为。“任何族群的规则、标准和原则都是抽象的,都是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不可能给任何独立的个人以特定的指示。”法律规则对社会的控制力取决于一般的普遍的规则广泛扩散到个体的人和个别的事之上。这一扩散的过程可以看成是一个规则传递的过程: 规则的发出者通过言语或示范性动作把意思传递给接收者。这传递过程在哈特看来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制定成文法律。二是法院判例。对于判例能否准确传递,哈特深表怀疑。在小孩模仿父亲脱帽时,他说,行为必须模仿到什么程度? 如果用左手而不是用右手摘帽子,有重大关系吗? 慢慢地摘帽子,还是轻轻地摘帽子? 帽子放在座席下面吗? 在教堂里不应该重新戴帽子吗? 下面是小孩自问的一些问题: “在哪些方面,我的行为必须和他的行为相似才能成为正确的行为?”在理解其父亲的示范时,这个小孩注意的是某些方面,而不是所有方面。他这样行为,是受关于一般性事务的常识、知识、和成年人认为重要的目的的指导,也受到了他自己对该特殊情况的一般性和与之相对应的行为的评价的指导。
大多数法学家认为立法在传递意思的时候是清楚的、可靠的和确定的。哈特则认为,即使使用文字制定的一般性规则,在特定的具体的案件中仍然可能突然发生不确定的情况。为此,哈特列举大量类似的例子加以说明。他说,那些看似具有确定意义的成文法规则,在许多时候却变得千疮百孔,形同虚设。法官们在审判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对这些规则的争辩,而争辩的最终结果就是回到规则用语的本身中去。无论是成文法还是判例法的规则,它们所包含的答案都不只一个,法规的用语通常具有两可的意义。哈特把这些不确定性归咎于语言自身所固有的现象,他说: “不仅在规则领域,而在所有经验领域,普通语言所能提供的指引都有其固有的限度,这是由语言内在本质决定的。”[2]124 -126法律是由普通语言来表达的,而一般词语的使用本身并不是明白无误的,这些词语本身也需要解释,但是语言不能解释自己本身。这些语言的不确定留给了法官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空间。
通过上述的例证分析之后,哈特马上从理论上进入到了对法律语言中的“空缺结构”的精彩探讨:“任何选择用来作为行为沟通的工具,无论是判例还是立法,不管他们在大量普通案件中如何顺利地进行沟通,都会在某些适用的时候出现争议,将表现出不确定性: 它们将具有空缺结构的特征。”空缺性结构是人类语言的普遍特征。在立法中,关于事实问题任何形式的沟通都使用了普通的分类性语言,这就造成了法律边界的不确定性,这是立法必须付出的代价[2]128。
法律的“空缺结构”是哈特关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理论最为突出的贡献。虽然哈特的“空缺结构”的理论来源于威斯曼等语言哲学家的论述,但是哈特在“空缺结构”理论方面作出了一些改善,使得这一理论更加适合法律分析。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分析方法上,哈特采用了比较保守的态度。维特根斯坦、威斯曼等哲学家在分析语言“空缺性结构”时都走向了极端,最后都变成了xuwuzhuyi和极端主义。
而哈特采用了一种折衷主义的方法,既相信语言的空缺性、模糊性,也相信语言的确定性。第二,哈特在“空缺结构”理论基础之上,开拓出了“意思中心”( core of meaning) 与“边缘地带”( penumbra area) 等新的理论,进一步丰富了“空缺结构”理论。
总之,哈特对日常语言的分析无不蕴含着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享有自由裁量权的空间。他以语言哲学作为其论述的理论基础,以法律规则的构成作为基本法律原理,论述了法律规则既有“意思中心”,又有“空缺结构”,法律规则是有限的确定性规则,法官自由裁量权是在规则之下的有限的自由裁量。
三、语言的“错误”与哈特法官自由裁量权理论的实质
关于法官自由裁量权问题的思考与争执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反复强调“法治非善,人治唯善”,主张实行“哲学王”之治。柏拉图提倡人治、反对法治的一个最主要的根据就是诊断出法律自身存在着病根。他认为法律恒求于定一,犹如刚愎无知的暴君不允许有任何违反其意志的表示,纵使情势发生变更,也不允许采用应急变革措施。法律条文束缚了哲学王的手脚,就像强迫有经验的医生从医学教科书中抄袭处方治理病人一样。追随着古希腊哲人的道路,致力于国家治理理论与法律理论的思想家们无不对法官自由裁量权问题进行了一番深刻的思考。
在此背景之下,哈特的法理学基本任务就是论证法律在司法过程中的运用。借助边沁功利主义原理和日常语言哲学的基本理论,哈特在批判奥斯汀法律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对批判法律实证主义的其他批判者进行了应有的回击。哈特法官自由裁量权理论的基本思路是: 首先,哈特依赖维特根斯坦的语言与规则概念,提出自己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理论,以回击富勒等人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批判; 其次,为了消除法官自由裁量权自身的缺陷,哈特提出了法律由主要规则与次要规则构成的思想。总体上而言,哈特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理论是在批判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
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现实主义是 19 世纪末一直到 20 世纪主要的法学流派,他们以司法过程为法学理论探讨的出发点,以法官自由裁量权为焦点,对司法性质与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在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问题上,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现实主义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极端。哈特利用语言哲学的基本方法,对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现实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哈特认为,法律形式主义与法理现实主义都在语言上犯下了“错误”,导致了他们的理论与司法现实不相符合。
19 世纪末法律形式主义开始盛行,法典化的思潮席卷整个欧洲: 各国都试图制订一部包罗万象的法典; 而法理学家的目的就在于打造完美无缺的法律概念,他们声称法官在审判案件的时候无需求助法律之外的其他规则或社会资源。法律形式主义的基本主张是: ( 1) 法律是一个由封闭的、意思固定的规则与原则组成的体系构成,强调法律的确定性与圆满性; ( 2) 在司法过程中,主张进行严格的三段论推理; ( 3) 法官通过逻辑推理寻找在法律中先前已确立的案件判决,无需行使自由裁量权。按照法律形式主义者自己的话说,法律具有确定性、客观性、统一性、可预见性的特点,司法就是一个机械的操作过程,法官在此过程没有任何自由裁量权[5]。
法律现实主义是在批判法律形式主义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与法律形式主义完全相反,法律现实主义主张: ( 1) 法律不是一个抽象的、理想的封闭体系,而是为了实现某些社会目的而确立的社会制度,强调法律的非确定性与非圆满性。( 2) 在司法过程中,法律逻辑是应该被抛弃的刻板之物; 法官不必遵守成规,可以凭借自己对案件的直觉判决。( 3) 法官的个性、社会因素直接影响了案件的判决,法官是法律的宣示者,行使着几乎无限制的自由裁量权。
奥地利大法官葛美林( Gmelin) 明确指出: “真正的正义不能在冷酷无情的三段论推理中去寻觅,也不能从那些灰尘满布的所谓的书本上去发现。”他认为,只有把法官的理性与情感、脑与心紧密结合在一起,用法官个人的正义感软化冷酷无情的法律逻辑,司法公正才有可能[6]。
哈特在很大程度上对法律形式主义采取毫不容忍的态度,认为法律形式主义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但在对待法律现实主义的问题上却采取了一种同情的态度,认为现实主义正确地认识到法律推理不能是“完全逻辑性的”,但是在批判的方法上犯下了同样的错误———不管是法律形式主义,还是法律现实主义都在语言上犯了“错误”。哈特认为,法律形式主义者的症结在于对语言的态度———坚信抽象的法律语词与法律概念在逻辑上是封闭的、无懈可击的,不存在模糊地带与开放结构[7]269。形式主义者认为法律概念的边缘意思产生法律解释问题是不可想像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语词完全是确定和限制的,只存在意思中心的区域。
法律形式主义者这种理论给司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法律形式主义者在客观性与逻辑先定性面纱下,唆使立法机关不断进行立法以及法官造法的勾当。哈特描述了在法律形式主义理论支配下的法官裁判的过程。哈特认为,“法律形式主义者的法官”不肯或不能承认由法律语言的“开放结构”所提供的社会目的、社会价值及其结果的慎重选择。“法律形式主义的法官”错误的本质是他或她对法律规则进行一般的分类,法律解释受制于社会政策、价值和逻辑因果关系[8]。不肯承认法律规则的开放结构,只考虑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去填补既定的目标与社会价值,这样,法官就会发现语词的意义是先定的,他们的任务是发现法律。
完成了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判之后,哈特马上转入到了对法律现实主义的批判。法律现实主义者一个重要的论断就是: 法律只不过是对法官将做什么的预测而已。法律现实主义者高举“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不在于逻辑”的旗帜,在对法律规则的怀疑与谩骂声中,四处鼓励法官“造法”。在自由裁量权方面,哈特在许多场合是与法律现实主义者站在一起的。但是面对法律现实主义者的张狂,哈特鞭辟入里地指出了法律现实主义的错误所在。哈特认为,法律现实主义在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判方法上是根本错误的。法律现实主义者错误地抛弃了逻辑论证和理性推理,认为逻辑与案件判决是不相关的,有时甚至阻碍了案件的公正判决。这样,他们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夸大了法官的直觉,混扰了人们的视线。哈特认为,法律形式主义在理论上“错误”的根源不是逻辑而是语言[8]64。逻辑就其本身而言不存在什么错误与正确可言。逻辑仅仅在假设的情况下告知你: 假如你给某个语词一个解释,然后一个确定的结论就出来了。逻辑对怎样给事物的细节进行分类时保持沉默,而这正是司法的核心问题[8]67。
表面看来,法律形式主义强调逻辑,事实上,法律形式主义却忽视了逻辑。哈特认为,法律形式主义把逻辑的重要性是摆在第二位的,因为他们假定的前提是所有的法律概念都是圆满的,每个法律制度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紧密体系,根据一系列基本的法律规范与复杂推理,所有法律意义或解释都能确定[7]289。因此,法律形式主义的前提性错误就是对“语言”本身的认识,而不是法律现实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逻辑”。与法律形式主义一样,法律现实主义的错误根源也在于对语言的理解上。法律现实主义把法律中的语词看成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洞物,只有在法官的判词中才具有意义。法律现实主义者同样没有看到法律的“空缺结构”与“意思中心”。这样,哈特就完成了对法律现实主义的批判。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哈特借助法律的“空缺结构”理论,对法律形式主义和法律现实主义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哈特认为,因为任何法律都有一个“意思中心”,又有其“空缺结构”; 规则怀疑主义正确地注意到了规则的“空缺结构”,却忽略了规则的“意思中心”,结果是否认了法律规则的存在,走向了法律“规则的神话”,因此,法官的自由裁量变成了任意裁量,无限制地扩大了法官自由裁量权。而形式主义怀疑论则仅仅注意到了规则的“意思中心”,却忽略了规则的“空缺结构”,结果是凝固了法律规则的意义,走向了法律的“概念天国”,因此,法官只不过是机械的操作手,毫无自由裁量权可言。从实质上来看,哈特自由裁量权理论就是语言:
从语言出发,确立法律规则; 在法律规则之中,发现法律的不确定性; 在法律的不确定性之中,找到法官自由裁量权。法律形式主义试图在法律逻辑中寻找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答案,结果是一无所获; 而法律现实主义试图在法官直觉中寻找答案,结果遍地都是;只有哈特在语言中寻找答案———法律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法官自由裁量权都是语言的“错误造成”的。逻辑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 直觉则完全脱离了事实的羁绊。只有语言,才是法官自由裁量权存的真正根基。语言的空缺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为法律的空缺结构以及不确定性埋下了祸根。哈特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理论是深刻而独特的。有些学者认为他在法官自由裁量权方面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方法。事实上,无论对法律形式主义,还是法律现实主义,哈特都采取了一种毫无妥协的态度。
他的理论是在一种严格的逻辑论证的情况下得出的。哈特是用语言的世界彻底包围了“法律的帝国”,虽然后人对他的法律“空缺结构”及法官自由裁量权理论提出了尖刻的批判,但是由于哈特的出现,法学出现了“语言”的转向,人们在拥护或批判的时候,不得不走向语言的世界。
哈特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理论对后来法理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法理学家,其代表人物有德沃金( Dworkin) 、富勒( Fuller) 、莱昂斯( Lyons) 、拉兹( Raz) 等知名学者,针对哈特提出的法律“空缺结构”及其法官自由裁量权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哈特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形成了各自的法理学研究理论。富勒认为,第一,法官通常需要解释的是法律的整个条款,而不是几个语词; 第二,法律规则中语词的“中心意思”来自对立法时立法者的意图的考量[9]。富勒的批评实际上并没有击中哈特的要害。
富勒过分强调了意义与理解中语境的重要性,但是有些语词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也存在着“意思中心”。莱昂斯对法律与日常语言之间作了一番类比后,认为即使法律存在着不可简化的“空缺结构”,但法律还是允许我们寻找确定法律结论的进一步资源。莱昂斯断言: 在规范语言中,我们能超越纯粹的语词去发现意义,类似地,法官能超越法律规则去发现法律的意义[10]。德沃金与哈特的争辩最为激烈,他们的争论主导了英美法理学长达 40 年之久。在这 40 年中,众多的法理学家参与到了这场争论之中,引发法律实证主义阵营的分野,形成了以拉兹为代表的“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理论”( exclusive legalpositivist theory) 和以科尔曼为代表的“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理论”( inclusive legal positivist theory) ,以及德沃金的“法律阐释理论”( interpretivist theory oflaw) 。同时,德沃金也修正了自己在《规则模式 I》( The Model of Rules I) 中的观点,并在《法律帝国》中得到全面的发展,引领了 20 世纪西方法学理论发展的高潮。
参考文献:
[1] 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Press,1994.
[2] Brian Bix. Law,Language And Legal Determinacy[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11.
[3] F Waismann. Verifiability,Proceeding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M]. vol. 19,1945: 120 -125.
[4] F Waismann. The Principle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M]. R.Hare,ed. ,St. Martin Press,1965: 74.
[5] J M Kelly . A Short History of Western Legal Theory[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311 - 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