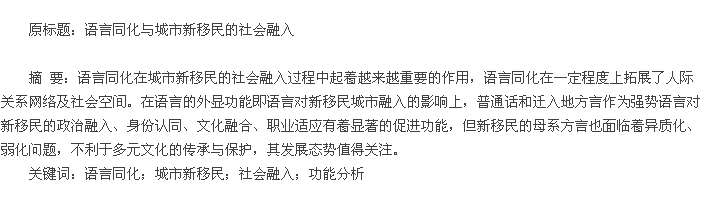
“城市化程度日益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伴随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大量人口不断涌入城市,一个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庞大社会群体构成了城市新移民群体,他们既为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资源,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矛盾和冲突。城市新移民的利益诉求与融合现状之间存在较大落差,城市新移民与当地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冲融现象,城市新移民“融城”问题已成为政府、学界关注的焦点。其中,从语言视角分析城市新移民融城问题逐渐引起关注,取得一定进展,丰富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
一、城市新移民的语言变异、语言同化和语言使用态度
语言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语言传递信息,实现其交流工具功能;另一方面,语言寄托着言语者对某种文化的情感,实现其文化载体功能。新移民城市融入过程中必须经历行为模仿到心理接纳再到内化至个体行为阶段,而语言是促进新移民个体融入群体并与群体实现有效互动的核心元素(樊中元,2011)。由于言语能力、文化水平、年龄及外出务工年限等因素影响,“语言一定程度上成为新移民适应并融入城市生活的障碍”P130),为克服语言障碍,新移民语言使用中出现同化现象。本文“语言同化”指:一个语言地区的外来人口为适应迁入地的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缩小与迁入地社会主流群体的语言距离,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其属地语言(母方言),语言使用趋向当地方言或国家共同语的现象。
宏观上,“语言变异”指一个语言区域的语言状况因各种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微观上,“语言变异”指语言使用者因语境、场合、言语对象、语言表达目的不同而导致同一个内容的语言变异[3](P104)。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异质有序的组合聚合体。语言变异有的与地域相关,有的与语言使用者的社会身份相关,有的与语言使用场合相关,有的与语言对象相关。语言是说话者建构、维持以及区分自己的社会属性界限和自己身份的途径。社会语言学中以实践共同体视角进行的语言变异研究,“强调语言变异是一种社会实践,它们把说话者的语言变体分析与整个社会实践结合起来”[4](P23)。
社会学中,同化论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优势文化面对弱势民族或部族时以强制性手段使其接受自己传统文化的一种思想或理论。其观点认为,移民会逐步适应并最终融于迁入地主流文化之中。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因而社会学中的同化理论也被应用于对语言同化进行解释。20世纪 60 年代,社会语言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美国建立,至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研究社会语言问题时也借鉴了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如韩清林认为,语言同化是语言发展变化的重要现象,“其作用体现在经济强势同化、政治强势同化、文化强势同化以及教育强势同化四个方面”[5](P49-51)。城市新移民进入迁入地后,语言发生了变异和同化现象,二者不是割裂或呈阶段性变化,而是呈交叉螺旋状。当移民语言在一个新的社会区域重新落户时,不可避免地与当地语言相互作用,使移民语言实现了再社会化。移民不可能始终保持同一种语言形式。在经过本土化过程的改变后,移民语言变异不可避免。且在生活和工作中,移民也开始使用普通话,甚至学习使用当地方言。这表明,移民群体进入新的社会区域之后,其语言受流入地语言环境影响有异于母方言,呈现向迁入地方言和普通话同化的趋势。
语言态度是指人们对语言的主观认识,在双语和多语社会中,是人们对一种语言或多种语言的社会价值形成的一定认识或评价(王远新,1999)。语言态度包括价值评价和行为趋向(陈建伟,2007),在语言生活中表现为语言评价、语言能力、语言使用、语言倾向等方面内容。[6](P56)生活在同一区域的不同群体由于成长环境、生活社区、职业特点、母语影响等因素,在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等方面会产生一定的差异。
本世纪初以来,不少研究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城市外来人口的语言生活状况。研究结论一般表明,城市新移民群体有着较强的语言适应能力,其语言使用和态度上呈现以下几个特点:(1)由原属地单一方言语码使用逐渐转为多种语码共同使用(普通话、迁入地方言);(2)语言使用的“二重性”,在不同场合会进行语码选择或转换,呈现内外分异与趋高避低的特点;(3)原属地方言逐渐异化、弱化,普通话和迁入地方言逐渐固化,新移民双方言人比例升高。
流动的生活经历使城市新移民对语言具有比较开放的态度。他们既愿意保持对家乡方言的忠诚,又高度认同普通话及当地方言在人际沟通中的重要地位。双语行为或多语行为是外来农民工为更好适应城市生活环境而做出的语言行为选择。当然,大量研究也表明,“对普通话的高度认同并不完全等同于在实际生活中的优先应用,在开放的语言态度与有所保留的语言实践之间甚至存在一定的背离”[7](P132)。王玲认为造成这种“悖论”的主要原因是“情感障碍”。夏历的研究表明,在京农民工进城务工后,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发生了群体性变异和同化:根据交谈场合和对象的不同,语言选择呈现出规律性。
城市新移民学习普通话和当地方言的主要原因是人际沟通和工作的需要。在非母语方言区,新移民面临语言障碍相当严重,许多人遇到过因语言不通而影响工作的情况,其学习本地方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较强。语言同化,这是城市新移民为适应职业需求而做出的主动或被动选择。
二、语言同化与新移民的人际关系网络、社会空间
社会交往关系状况往往是测量不同群体融合程度的重要指标。在中国,城市新移民大多是依赖血缘、地缘等“强关系”网络寻找工作,尤其是农民工群体,他们交往群体、社会关系网络同质性非常高。
一些城市出现“浙江村”“、河南村”“、平江村”,这是一种典型的反移民化产物。究其原因,语言障碍是重要因素。奇斯威克等人认为,部分对迁入地语言不熟练的移民往往会尽量避开当地语言,因而他们在选择居住地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优先考虑使用他们母语的聚集地。从经济学角度看,反移民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移民融入迁入地的语言再社会化资本,但也阻碍了移民的融入速度和质量,导致移民人际关系网络同质化、单一化,社会空间狭窄化,不利移民与当地社会的融合。
(一)语言同化与政治融入语言不单单是交际工具,它还承载着特殊的社会功能,语言使用背后必然隐含着政治、经济或者文化权力的因素。普通话是政府以国家意志推行的全国通用的标准语和共同语,它具有政治整合作用。在国家范围内,相比较各种方言,普通话成为强势语言,它借助政治的力量和书面标准语的作用具有一种绝对优势,对其他语言起着政治强势同化作用。
新移民进入移居地后的社会融入必然伴随其政治参与需求的觉醒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而这一过程与语言同化密切相关。美国移民语言政策的变迁就充分论证了这一点。美国移民语言政策变迁经历了最初的不干涉阶段到“唯英语论”阶段,再到多语言合法共存三个阶段。各种力量此消彼长,围绕英语对移民同化作用的争论最为剧烈,这主要是出于政治考量。在美国,种族主义、国家主义、为少数民族争取平等权力等诸多政治性因素不断影响着移民语言政策变迁。在美国,英语地位之争实质就是政治之争“,语言同化甚至成为美国同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8](P144)。在一定历史时期,语言同化有助于移民参与迁入地宗主国的政治生活,争取自己应有的政治权利,但如果语言同化是以国家意志强加于移民身上,则成为移民政治权利缺失的一种表现,更加证明移民在宗主国政治上的弱势地位。
(二)语言同化与身份认同“移民”为动词时意指:居民由一地或一国迁移另一地或另一国落户;为名词时意指:迁移到外地或外国去落户的人。由于中国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壁垒的设置,许多研究者视角落点更多关注新移民的户口身份,即“落户”问题。当前,城市新移民群体身份上多元混杂,社会保障以及制度上难以获得迁居地的市民权,他们不被迁入地城市完全认同,身份陷入一种尴尬境地,具体表现为现实生活中的户口身份不时提醒他们仍停留在制度限定的农民身份或外地身份上。基于此,积极学习、使用普通话甚或流入地方言的行为表现对于城市新移民而言,不仅是一种生存策略,更是一种最易获得的城市身份认同的有效手段。
Giles Johnson 提出种族语言认同理论,认为个体为获取积极的社会认同会采用各种策略,语言在社会生活中作为群体成员身份和社会认同的一个显著的标志,有可能促使个体作出改变原属地语言而去适应迁入地语言的选择。[9](P199-243)对于社会地位而言,城市新移民利用语言资本的逐步积累实现个人认同进而扩展到群体认同,原有的社会背景对他们在流入地的言语活动起到制约作用,因此学习、使用当地方言或普通话不仅是新移民在迁入地进行有效交流沟通的重要媒介,也是他们适应身份变化、扮演新角色的表现(埃米尔·涂尔干,2009)。对于大多数新移民而言,身份认同仍是影响他们语言使用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来源属地经济程度不同,他们认为使用普通话可以掩盖乡音,避免母方言中隐性信息泄露,而“普通话容易使交流双方地位趋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4 年第 2 期平等,双方身份会更快地被对方认同”[10](P408)。
(三)语言同化与文化融合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在社交网络中,个体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文化载体,一言一行都投射其文化背景。语言是文化的象征,是重现或追溯民族文化最直接的方式,它具有文化身份。“使用一种语言,就是选择一种文化,并以这种文化身份存在。”[11](P81)在文化身份方面,重塑文化身份及如何解决文化冲融问题是城市新移民必须面临的难题。大多数城市新移民受其经济地位、文化观念等方面影响,其交际对象主要限于内群体,与迁入地城市居民难以进行全面的社会互动,为改变这种现状,不少新移民努力搭建语言平台,并通过语言同化进行自我包装,尝试克服社会流动中遇到的文化隔阂,这是新移民实现与迁入地城市文化融合的重要渠道之一。
普通话作为国家共同语,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最重要载体;迁入地方言作为当地社会的主流语言,是当地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普通话和迁入地方言占有优势地位,它们借助文化手段,使其语言强势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实现同化、融合其他种类语言或方言目的,城市新移民会潜意识地向着具有隐性威望的语言形式靠拢。[12](P50)现代西方哲学与社会学中的法兰克福学派把语言比作意识的重要社会过滤器,认为移民的语言同化现象是文化融合的重要内容,是反映移民与迁入地社会关系的重要指标之一。西方学者在研究荷兰移民政策时发现,荷兰从实行融合政策开始就设立了多元文化的融合目标,意图构建一个包含移民的多元文化社会,但移民群体由于社会文化上保持特性和独立的政策更加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移民群体尤其是穆斯林逐渐成为荷兰社会的“问题”群体,为此,荷兰政府进行了反思并开始制定新政策,要求移民接受荷兰文化,学习荷兰语言,标志着荷兰的移民融合政策走上了同化的道路。[13](P1)可见,语言同化对文化融合有显著的促进功能。
(四) 语言同化与职业适应目前,城市新移民中职业适应最为艰难的群体当属农民工群体,这已引起政府和学界的高度关注。谢俊英和曾晓洁认为,母语能力缺失现象在农民工群体中普遍存在,加之迁入地城市语言环境影响,农民工交际范围和就业选择具有较大局限性。然而,获得职业机会往往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初步骤,职业能力的不断提升无疑是农民工继续城市生活的重要环节,和谐的劳动工作关系是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社会的根本保证(杨黎源,2011)。农民工是社会就业的弱势群体,他们的职业发展之路异常尴尬,既融不入城市,也回不去农村,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选择是:通过职业能力提升进一步市民化最终融入城市,而职业能力提升的第一步就是语言障碍的克服。
职业适应是新移民城市融入中获得职业肯定、提高职业能力的核心因素,它相对其他层次的社会适应更直接。对于城市新移民而言,利用职业获得物质基础,从而完成经济层面社会适应是其实现“融城”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大量研究表明,新移民从事的工作大都处于职业结构分层的中下层,当他们的语言无法与主流社会语言趋同时,会导致其职业发展机会减少,职业发展通道不畅。而且,语言障碍也会影响新移民在职场的利益诉求。总之,新移民与迁入地当地居民的互动因职业结构、居住空间、语言习惯等差异而很少发生,即使发生,这种接触也只是一种表层性的社会交往,这种表层性的社会交往因“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而不可能深入和持久”[14](P41-42)。
三、语言同化与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进程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城市新移民的城市融入研究亦取得显著成果。以语言为切入点成为一个新颖的研究视角,语言在新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生活空间中所发挥的功能问题,是这一研究领域关注的中心话题。语言同化是一把“双刃剑”,考量语言同化对于城市融入功能时,应看到其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积极意义,但它也存在负面影响。值得关注的是:
第一,语言同化在新移民城市融入过程中发挥功能作用的同时,也使得新移民母方言呈现异质化、弱化,甚至消亡的趋势。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任何一种方言的消亡或流失都是人类社会文化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如何保护地方方言值得关注。
第二,城市新移民中双语(老家方言与流入地语言)使用者比例非常高,根据交际对象和场所的不同而选择或转换语码。同时,在非正式场合里,掺杂式语言的使用也相当普遍,即在同一个场合面对同一个语言对象会使用两种语码。
第三,城市新移民在迁移流动过程中,自我同一性不断面临挑战,尽管当中许多人力图通过语言同化融入到城市的社会生活中,他们希望能借助权威语言力量实现向上流动,但他们对自我身份认识的思考和困惑将长期存在。
第四,城市新移民语言同化对迁入地语言生态变迁存在影响。迁入地语言生态变迁是一个动态过程,大规模外来人口的流入使得城市原有的语言生态面貌发生变化。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口母方言的排斥心理逐渐降低,本地居民使用普通话的比例逐渐升高,在以普通话为共同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多方言并存的语言社会。
第五,国内外学界对国际移民的理论解释与研究方法等发展得比较成熟,从多维的分析视角进行移民语言研究,对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是,中国城市新移民是发生在一国内部的跨地域流动,其内部的流动与国际移民存在明显的边界。因此,如何借鉴国际移民语言研究成果值得探究。
参考文献:
[1]陈柳钦.为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进谏[EB/OL]./2013-05-13.
[2]秦广强,陈志光.语言与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6).
[3]朱学佳.家庭语言变异现象分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0).
[4]芮晓松.称谓语研究述评———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视角[J].中国社会语言学,2009(1).
[5]韩清林.语言的强势同化规律与强势语言的先进生产力作用[J].语言文字应用,2006(1).
[6]屠国平.宁波市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语言态度比较研究[J].中国社会语言学,2009(1).
[7]秦广强,陈志光.语言与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6).
[8]王双利.美国少数民族及移民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0(4).
[9]Giles H,Johnson P.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Ethnic Group Formation[A]. Intergroup Behavior[C].Oxford: Basil Blackwell,1981.
[10]葛俊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新移民语言状况调查与分析[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
[11]黄亚平,刘晓宁.语言的认同性与文化心理[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12]韩清林.语言的强势同化规律与强势语言的先进生产力作用[J].语言文字应用,2006(1).
[13]许赟.荷兰移民融合政策变迁———从“多元文化主义”到“新同化主义”[D].华东师范大学,2010(4).
[14]马清.反移民化:社会资本与社会结构的双向契合———以上海市劳动力新移民的社会适应为例[D].华东师范大学,20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