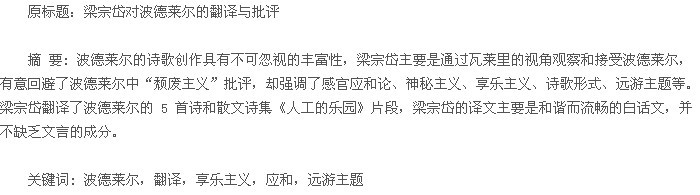
梁宗岱对白话新诗的建设是高度自觉的,在法国文学上的选择,主要偏向于象征主义。从象征主义回溯到波德莱尔、马拉美与魏尔伦的象征主义,事实上承袭了自雨果、波德莱尔而来的探索精神,这也融合在瓦莱里的视野中。梁宗岱主要是通过瓦莱里的视角观察和接受波德莱尔。
一、粱宗岱对波德莱尔的批评波
德莱尔的创作具有不可忽视的丰富性,现代中国对波德莱尔及其诗歌的揭示则较多偏向于恶魔的、颓废的、怪诞的方面,并移植了“腐尸诗人”这一称呼。早期的翻译和批评主要包括徐志摩翻译波德莱尔《死尸》(1924. 12. 1),金满成翻译《死尸》(1924. 12),张人权翻译《腐尸》(1924. 12),李思纯翻译《腐烂之女尸》(1925. 11),可知此诗一时较为流行。(彭建华,2008:210-38)梁宗岱表达了对《恶之花》全新发现,《象征主义》一文写道:“从题材上说,再没有比波特莱尔底《恶之花》里大部分的诗那么平凡,那么偶然,那么易朽,有时并且———我怎么说好? ———那么丑恶和猥亵的。可是其中几乎没有一首不同时达到一种最内在的亲切与不朽的伟大。无论是佝偻残废的老妪,鲜血淋漓的凶手,两个卖淫少女互相抚爱亲昵与淫荡,溃烂臭秽的死尸和死尸上面喧哄着的蝇蚋与汹涌着的虫蛆,———透过他底洪亮凄徨的声音,无不立刻辐射出一道强烈,阴森,庄严,凄美或澄净的光芒,在我们底灵魂里散布一阵‘新的颤栗’———在那一颤栗里,我们几乎等于重走但丁底全部《神曲》底历程,从地狱历净土以达天堂。因为在波特莱尔底每首诗后面,我们发现的已经不是偶然或刹那的灵境,而是整个破裂的受苦的灵魂带着它底对于永恒的迫切呼唤,并且正凭借着这呼唤底结晶而飞升到那万籁皆天乐,呼吸皆清和的创造底宇宙:在那里,臭腐化为神奇了;卑微变为崇高了;矛盾的,一致了;苦涩的,调协了;不美满的,完成了;不可言喻的,实行了。”(梁宗岱,2003: II. 79)波德莱尔(例如《契合》)揭示了物象经过感官的捕捉之后,在心灵(esprit)的观照之下,发生超验的意象,而这种超越性的意象与客观物象便形成了象征的关系,这是从宗教释义方法中移植而来的诗学发现,也是客观事物在无限的未知确立自身方位的简捷方法。而后,兰波重申了对未知的预言(Je dis qu'il faut être voyant,se faire voyant)。较早的,魏尔伦在《论波德莱尔》中(Baudelaire,L'Art I,no. 5,1865)赞叹了波德莱尔在美学上的新探索,而后瓦莱里主张把波德莱尔纳入象征主义,所以梁宗岱的《象征主义》一文更为集中地探讨“象征”和波德莱尔的《应和》一诗所表现的新的象征美学。
梁宗岱对波德莱尔的应和论做了理性而明析的中国化解释。“我也很能了解波特莱尔底‘契合’(Correspondances)所引出来的官能交错说,而近代诗尤重视诗形底建筑美,如波特莱尔底《黄昏底和谐》底韵是十六行盘旋而下如 valse 舞的……但所谓‘契合’是要一首或一行诗同时并诉诸我们底五官,所谓建筑美亦即所以帮助这功效底发生,而断不是以目代耳或以耳代目。”(梁宗岱,2003: II. 38-39) “可是这时候的心灵,我们要认清楚,是更大的清明而不是迷惘。”(梁宗岱,2003: II. 99)“所以一切最上乘的诗都可以,并且应该,在我们里面唤起波特莱尔所谓:歌唱心灵与官能底热狂的两重感应,即是:形骸俱释的陶醉,和一念常惺的澈悟。”(梁宗岱,2003:II. 73) “有时候自我消失了,那泛神派诗人所特有的客观性在你里面发展到那么反常的程度,你对于外物的凝视竟使你忘记了你自己底存在,并且立刻和它们混合起来了。波特莱尔底《恶之花》是最显着的例。”(梁宗岱,2003: II. 78)
二、波德莱尔的诗歌翻译
梁宗岱翻译了波德莱尔的《祝福》( Bénédiction — Lorsque,par un décret des puissancessuprêmes) 、《契合 》( Correspondances) 、《露台 》( Le balcon — Mère des souvenirs,ma?tresse desma?tresses) 、《秋 歌 》二 首 ( Chant d'automne — 1 . Bient?t nous plongerons dans les froidesténèbres;2 . J'aime de vos longs yeux la lumière verd?tre),这些译诗均收入《一切的峰顶》。梁宗岱《象征主义》一文中引用了波德莱尔的散文诗集《人工的乐园》(Les paradis artificiels,opium et haschisch,1860 ) 中的《塞拉芬剧院》( Le thé?tre de Séraphin) 选段。梁宗岱的选译在倾向上明显区别于李金发、李思纯。李金发《微雨》附录波德莱尔译诗 3 首:《快乐的死者》、《用她光彩而闪耀的衣裳》(Avec ses vêtements ondoyants et nacrés)、《你将全宇宙放在你的小路里》(Tu mettrais l'univers entier dans ta ruelle)。(李金发,1986: 226-29)李思纯的《仙河集》(1925),《仙河集》选入了波德莱尔的 10 首诗,主要突出了波德莱尔的颓废、恶与怪诞:《鬼》(Le Revenant)、《鸱枭》(Les Hiboux)、《血泉》(La Fontaine du sang)、《腐烂之女尸》(Une Charogne)、《猫》( Le Chat)、《破 钟》( La cloche fêlée)、《凶 犯 之 酒》( Le Vin del'assassin)、《密语》( Causerie)、《赭 色 发 之 女 丐》( ? une mendiante rousse)、《暮 色》( LeCrépuscule du soir) 。( 李思纯,1925 )
梁宗岱选译的 5 首诗歌大致再现了波德莱尔诗歌的三种倾向(见《韩波》):其一,“那亲密的感觉以及那神秘的情绪和肉感的热忱底模糊的混合”,《露台》、《秋歌》之二表现了这一拉丁主义的倾向;其二,“诗底形式和技巧上的绝对的纯粹与完美”,《契合》并不完全表现了这一后浪漫主义的形式追求,《露台》一诗则表现出优美的音乐性,《契合》发现了神秘的、象征记符的观感,在心灵(esprit)上奇异的意象和影响力,这种显明的心理主义美学,带来了象征主义诗歌的革新运动;其三,“那出发底狂热,那给宇宙所激起的烦躁的运动,和那对于各种感觉和感觉之间的和谐的呼应。”(梁宗岱,2003: II. 179-80)《秋歌》二首都是源自秋天的忧伤思绪,即“那给宇宙所激起的烦躁的运动”,也都暗示了“出发底狂热”。此外,《祝福》表现了波德莱尔经常出现的,(如《信天翁》),对资产者社会的诅咒及孤独和理想的诗歌之王等内在的心灵冲突。
《阳台》是一首优美的歌咏女性的诗歌,波德莱尔把爱情称为“不朽的事物”(impérissableschoses)。(Baudelaire,1923 : 59)梁宗岱的译诗是极严整的12 字诗行,另作白话韵式,但是明显回避了“抚爱亲昵与淫荡”的成分。召魂/召灵(évoquer)是一个不容易被白话传达的意象,梁宗岱没有忽略这个波德莱尔式的用法,“面纱下晕红的玫瑰”(voilés de vapeurs roses)是一个传统的譬喻,却被微妙地替换了。(梁宗岱,2003: III. 80-82)
1859 年 11 月 30 日《秋歌》之一( Chant d'automne,? M. D. ) 最初发表在《现代评论》上,是一首献给玛丽·迪布朗的爱情诗,这首诗表现了一个被夸张的“及时行乐”(carpe diem)的拉丁式主题。(Baudelaire,1923: 92)梁宗岱的译诗同样是极严整的 12 字诗行,另作白话韵式,偶尔引用了汉语文言诗词的意象,“这神秘的声音响起了,仿佛新的出航”(Ce bruit mystérieux sonnecomme un départ. ),不恰当地被消除了。( 梁宗岱,2003: III. 82-83)《秋歌》之二最初刊行于《恶之花》1861 版,在主题上与《阳台》一诗更接近,混杂了三种波德莱尔式的倾向,表现出艺术上的不完美。(Baudelaire,1923: 93)梁宗岱的译诗一般是比较整齐的诗行,韵式较为随意。(梁宗岱,2003: III. 83)
梁宗岱在《象征主义》中写道:“我们内在的真与外界底真调协了,混合了。我们消失,但是与万化冥合了。我们在宇宙里,宇宙也在我们里:宇宙和我们底自我只合成一体,反映着同一的阴影和反应着同一的回声。关于这层,波特莱尔在他底《人工的乐园》里有一段比较具体的叙述。”“正如颜色,芳香和声音底呼应或契合,是由于我们底官能达到极端的敏锐与紧张时合奏着同一的情调,这颜色,芳香和声音底密切的契合将带我们从那近于醉与梦的神游物表底境界而达到一个更大的光明—一个欢乐与智慧做成的光明,在那里我们不独与万化冥合,并且体会或意识到我们与万化冥合。”(梁宗岱,2003: II. 72-73)
以下迻录《塞拉芬剧院》一文的第十五段,梁宗岱翻译了前半部分有关自然意象的揭示,却删略了后半部分有关吸烟的释义。波德莱尔强调了鸦片或者哈息斯所带来的自我与外物的契合(或者想象力),这超出了应和论的诗歌美学。(Baudelaire,1869: 180)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引入中国道家和禅宗的主观理念,梁宗岱对此的释义偏离了波德莱尔的主体投射和自我幻化观念。(梁宗岱,2003: II. 73)
有时候自我消失了,那泛神派诗人所特有的客观性在你里ICI发展到那么反常的程度,你对十外物的凝视使你忘记了你自己底存在,并日立刻和’已们混合起来了。
你底眼凝视着一株在风中摇曳的树:转瞬间,那在诗人脑里只是一个极自然的比喻在你脑里竟变成现实了。
最初你把你底热情、欲望或忧郁加在树身上,它底呻吟和摇曳变成你底,不久你便是树了。同样,在蓝天深处翱翔着的鸟儿最先只代表那翱翔十人间种种事物之上的永生的愿望;但是立刻你已经是鸟儿自己了。
我想着,一边吸着烟。你的注意力很长时一间会平息下来,在烟斗上冒出的浅蓝的烟雾上。
对十蒸发的观念,‘漫慢的,连续的,永恒的,占据了你的心灵。不久,你将这个想法应用到自己的沉思和你沉思的材料上。
因为这奇异的含混,因为换位或智力误解,你会觉得你在蒸发,你凝神令注十你的烟斗,(于此你会感觉到蹲下,像烟草一样的卷紧),你吸烟便有了奇特的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