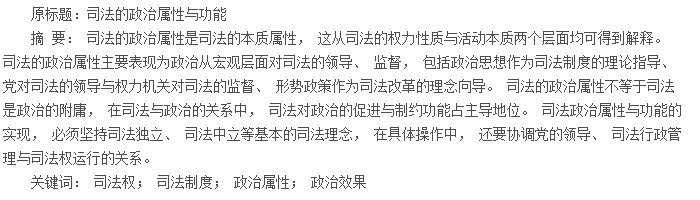
***总书记在2014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 “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强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发布的《中国政治发展报告(2013)》(以下简称《蓝皮书》)指出,受政治结构的影响,“我国的司法权力在政治上要服从党委结构的影响,在法律上要对人民代表大会机关负责”;司法系统奉行的诸如“能动司法理念”“调解优先原则”分别来源于“服务大局”的政治需要与中央关于建立诉讼和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要求。 司法改革的重要地位与司法权力的运行空间及司法对政治需要的回应,无不反映了司法在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属性。 从历史上看,纠正“不走群众路线、手续烦琐,不关心政治问题”等旧有的司法作风,在我国1952年6月至1953年2月的司法改革中,便已作为改革的重要议题,以期明确司法的政治属性,纠正当时司法机关存在的政治、思想不纯问题。 据此看来,司法的政治属性似乎是无须言明的,司法改革考虑政治需要也是理所应当的。 尽管如此,在“权力分立运行”这一普适理念的背景下,若未能正确认识司法“政治属性”的内涵、不能清晰界定司法“政治属性”对司法运行的影响界限,诸如将司法的政治属性与司法行政化混为一谈,借司法政治属性之名以行政权力干预司法,搞“以权压法、以权代法”,将司法的政治性与依法治国、独立行使司法权相对立等,司法的有效运行便会成为空谈。 《蓝皮书》基于对我国2012年司法运行的经验总结,便强调“司法的政治属性与独立行使司法权如何调和”的问题是司法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之一。
基于此,本文拟对司法政治属性的渊源、体现与运行效果进行分析,以获得对司法这一“不言自明”之属性更为准确的理解。
一、司法为何具有政治属性
从语义学角度来看,“司”有掌管、处理、承担之意,如《说文解字》的解释“司,臣司事于外者也”,元代徐元瑞的《吏学指南》也提到“职掌曰司”,现代汉语中司籍、司架、司机等词语中的“司”也是掌管之意。 同时,汉语中的“司”在名词层面上使用,表示某种官名,如司令、司律、司禄、司寇等。 因此,在中文语境下,“司法”可以理解为适用法律、掌管法律,也可理解为与法律相关的一种职业。 据此,司法的政治属性一方面可从权力层面,定位于特定主体的一项职能进行解读;也可从活动层面,定位于法律纠纷解决的一系列行为、过程加以解读。 在权力层面,司法的政治属性蕴含于权力来源与权威保障两方面;在活动层面,司法的政治属性蕴含于活动主体,即司法的组织设置与人事任免制度、规则及司法活动的经费保障等方面。 具体而言包括:
第一,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纠纷解决经历了由原始社会及国家出现早期的血腥复仇、同态复仇等私力救济模式,到由国家作为排他性的第三方、依据某种“外在”规则予以主导之公力救济模式的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司法活动成型并逐渐发展成为国家权力维护社会秩序的一项重要制度。因此,从权力渊源来看,司法权是国家权力介入纠纷解决的结果。在司法权确立之后,其行使遵循“国家垄断原则”,即司法权及司法职能只能由国家司法机构独占享有并承担,在司法领域排除其他机构对具有司法性质之权力的行使。司法权作为一项国家权力,构成了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此来看,司法的政治属性是其不可摆脱的本质属性之一。
第二,司法的权威保障依赖国家强制力。司法通常被视为“社会的平衡器”“权利的最后救济屏障”。 因此,司法的首要功能在于解决纠纷,恢复被破坏的利益平衡。 从这一层面来讲,司法的有效运行依赖社会公众的信仰与服从,即司法必须具有权威(authority)。 美国学者泰勒(Tom .R.Tyler)在20世纪80年代围绕“人们为何遵守法律”这一问题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公众守法存在以“威慑”(deterrence)文化为基础的工具化原因,与关注“人们所认为的、和其自身利益相关的合理或合乎道德事项之影响”的规范化原因。 时下,我国司法权威的实现更多强调在规范化原因的背景下通过提升司法公信力获得解决。 这固然无可厚非,且司法正义也理应成为司法权威实现的主要路径。 但是,正如有学者所言:“司法的权威是权力和威信的统一,也是强制和自愿服从的统一,司法公信力和执行力是衡量和判断司法权威的两个标准。 ”即虽然司法权威不等同于威慑,但司法权威的实现是离不开其威慑力的,这尤其体现于司法裁判、决定的执行依赖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之中。 从这一方面来讲,“司法权威说到底是政治权威的一个方面”。
第三,司法组织设置与人事任免对政治的依附性。国家司法人员及司法机构的职责权限、法律地位、组织活动原则及行政管理方式等,深受国家历史背景、政治环境、经济基础及国家权力结构的影响。 基于此,司法制度可依所在的政治体制为标准予以分类,比如西方国家“三权分立”体制下以“分权制衡”原则为指导所建立的司法制度、我国以“议行分工”为原则设立的司法制度。在这一分类背景下,各国司法的组织设置与人事任免都深受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以我国为例,根据《宪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我国的权力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各级人民法院及人民检察院均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法院、检察院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 在国家机关职能分工原则的指导下,各司法机关之间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并相互制约。 在人事任免方面,各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免权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享有;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及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由同级人大常务委员会任命,同级人大常务委员会同时对上述人员享有罢免权。 因此,司法主体设置对政治权力结构的反映,也表明政治属性是司法的本质属性。
第四,司法规则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司法规则一般可分为司法组织规则与司法活动规则。前者重在规范司法主体的设置,内容涉及司法权主体的性质与任务、司法机构的人员构成与组织结构以及各司法机构的工作机制等。 后者主要规范司法权力的运行,包含相关的具体制度、程序法则及司法据以裁断的规则。 以审判权为例,包括审级制度、审判监督制度、合议庭程序以及作为裁判基础的刑事、民事立法等。 这些司法规则主要表现为立法的形式,其实质是通过法定程序固定的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亦即国家意志的反映。 鉴于政权结构对司法组织与人事任免的影响,司法组织规则的政治性自不待言。 司法活动规则的政治性,主要以其蕴含的司法思想为基础。 司法思想是司法主体法律知识结构中抽象层面的意识与理念,一般受制于司法环境,与社会法律文化背景、政治理念相关。 比如协商性司法、恢复性司法等近年来司法改革所遵循的理念,即是在和谐社会、和谐司法的政治背景下提出的。 审判公开、人民陪审制度的确定与发展,从根源上来讲,也是司法活动中强调人民参与性这一民主理念的结果。 从这个层面来讲,不仅“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实际影响着司法的运作过程”,而且“司法承载着重要的政治功能。 政治意志有赖于司法权得以实现”。
第五,司法经费主要由国家税收予以保障。 现代国家一般以税收的形式从社会无偿取得一部分产品及国民收入,据以支撑其制度的运作,实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 在司法权由国家垄断行使的原则背景下,鉴于“无救济即无权利”这一基本法理,国家负有为其国民解决纠纷、提供权利保障的义务。 从司法救济的经济负担角度考虑,司法机构不应以营利为目的,司法运作的大部分费用应由国库开支,而国家只针对相关当事人以必要为原则、以成本额为参考收取一定的费用。 因此,司法经费一般由国家税收来负担,提供司法服务亦是国家的重要职能。 如学者所言“诉讼……是不可或缺的国家福利设施,是国家塑造社会的工具”。
因此,“司法部门归根到底还是国家的一个部门”。
二、司法政治属性在我国司法制度中的体现
尽管政治属性是司法的本质和应然属性,但毋庸讳言的是司法归属于法律系统,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司法的政治属性并非简单等同于司法是政治的附庸。准确把握司法的政治属性,应认清政治介入司法的维度与限度。 具体而言,司法的政治属性在我国司法制度中,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政治思想是司法制度的理论指导。 我国司法制度是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为背景,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法律与人权的思想及列宁有关法制统一和法律监督思想等政治思想的理论指导,逐渐发展完善的。 比如,(1)司法贯彻“群众路线”的政治思想。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工作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 ”《刑事诉讼法》则明确将依靠群众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司法以为民为宗旨,深入了解群众的司法需求与司法期待,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借助群众的支持与帮助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 (2)司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政治思想的指导。 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律师法》 中均明确规定司法活动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司法秉持“有错必纠”的原则,针对两审终审制度设置审判监督制度而作为司法错误的补救机制。 (3)司法受列宁法制统一思想与法律监督思想的影响。 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第129条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目前,我国检察机关担负着通过职务犯罪侦查制度、审判监督制度及刑事诉讼的参与等多种途径维护法制在司法层面的统一。 (4)司法坚持“民主集中”政治思想的指导。 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 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 ”我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3条第2款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委员会。 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 如果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可以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即我国司法机关分别通过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的形式贯彻“民主集中”这一政治思想,在法院、检察院内部实行集体负责制。
第二,党的领导是司法工作坚持正确方向的保证。 “在西方国家,先市民社会后政治整合的自主发展逻辑使他们的政党及政党制度仅扮演着新政治秩序的体现者和完善者的角色;而在中国,民族危机所决定的先政治整合后市民社会的非自主发展逻辑使中国共产党不仅承担着应对社会政治危机的重任,而且扮演着国家现代化的领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 ”源于此,我国司法制度区别于西方司法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即在于 “坚持党在司法领域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因此,党在司法领域的领导作用主要是政党资源对司法的支持以及保证司法工作坚持正确的方向。 这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得以实现:(1)通过立法程序将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定;(2) 通过向国家权力机关推荐司法干部人选及对司法中的党员干部实行监督的方式,实现党对司法人员的领导;(3)各司法机关内部设置党组织,执政党通过各级政法委与司法系统内党组织的联系实现其在宏观层面对司法的引导。
第三,权力机关的监督制约是司法权有序运行的保障。 在我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一种,对其规范在权力机关权力所辖范围内。司法民主理念及司法贯彻群众路线要求司法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司法机关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与制约。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司法机关由权力机关产生并向权力机关负责,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职责也为《宪法》所明确规定。 权力机关对司法的监督主要包括:其一,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指导审判工作、检察工作之司法解释、规定、办法及工作计划、工作报告等进行审查,以查明上述文件是否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其二,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工作中是否依法行使职权、正确适用法律进行监督;其三,监督由人大选举或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是否有违法失职行为。这些监督主要通过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人事任免权,对司法工作报告的审议与对司法机关的质询、询问权,听取司法专向汇报及通过司法信访工作机制受理群众的控告申诉等实现。国家权力对司法权的这种制约、制衡,是司法有序运行的基本保障。
第四,形势政策是司法改革的理念导向。 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转型期,鉴于“转型期法治的有限性”,即“法的资源与法的能力有限”,以及转型期“社会问题的产生、社会纠纷的形成有复杂的因素”,社会纠纷的处理“不仅要考虑现实的合法性,也要考虑形成纠纷的复杂社会因素,同时兼顾纠纷处理的社会效果”。 有学者据此指出,现实可行的法治发展战略,“不在于理性建构与自发演进之争,而是要理解转型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和法秩序建构原理”。 基于形势政策对社会需要的即时回应性特征,“转型期的司法应该是政策指导型司法,而不是法规中心型司法”。
形势政策理应成为司法改革的路径指引。 形势政策具体在司法领域中,一般体现着政治基于社会形势与需要而对司法提出的要求与期待。 以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度公布的十大司法政策为例,其内容涉及冤假错案的防范、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应对、处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诽谤、敲诈勒索,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等案件的意见以及“践行司法为民、加强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推进司法公开”的意见。 这些政策规制的重点无不与诸如“打击虚假新闻”“农民工讨薪”“网络大谣”“微博庭审”“张氏叔侄冤案的平反”等媒体评选出的2013年度社会发生的热点事件休戚相关。 司法对相关政策的贯彻实施会形成司法发展的特色,进而成为司法改革的理念向导。
三、司法的政治功能与运行效果
政治属性作为司法的本质、应然属性,还体现于司法的功能层面。 如前述,司法的首要功能是解决纠纷,即在纠纷产生后,为当事人提供充分表达意见的场所与机会,并基于对纠纷的中立调查与评判,以司法机制、司法规则对纠纷进行衡量,在揭示纠纷实质的基础上得出合理的处理结果。 该功能的实现,从过程上来讲,理性、程序化的解决方式可将纠纷暂时搁置并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围内,排除私力以暴力对抗方式解决纠纷的可能,从而实现社会控制;从结果上来讲,公平、正义的处理结果可对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进行一定程度的修复、对偏离社会秩序的行为进行纠正、对失衡的社会关系加以协调,进而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同时,司法对相关司法机制,如各类诉讼程序与制度以及司法规则的适用,本身便是对实现国家政治意志的努力。
因此,司法的政治功能可以说是司法运行直接或间接的一种效果。 此外,作为社会纠纷解决的最终手段,随着法治的发展,司法在国家运行中的政治功能会进一步延伸并日渐重要。 如托克维尔对美国社会民主发展趋势的预言:“在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或道德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 ”行政诉讼制度以及司法审查制度在世界各国的确立与发展,使司法权直接作用于行政行为与立法便是最好的例证。
有学者指出:“司法的政治功能体现了司法对于国家政治要求的回应,即司法在调整与国家政权相关的各种利益关系时如何适应国家政权的要求, 在促进社会管理和社会稳定中发挥作用。 ”依拙见,上述观点仅指出了司法对政治之积极推动的功能,而未涵盖权力间相互制衡这一权力运行逻辑下司法对政治的制约功能。 因此,笔者认为,司法的政治功能包含政治对司法的依赖与司法对政治的制约两个方面。
第一,政治对司法的依赖。 其一,政治体系存续的基本前提是“合法性”,而现代政治一般将“人权”作为合法性的价值基础。 尽管“人权”在政治哲学上的确定性仍存争议,但在现代社会,诸如言论自由、选举权等政治性权利,劳动权、受教育权、财产权、住宅及通讯自由、人身自由等社会性权利,救济机制中的申诉权、起诉权、辩护权、申请回避权、获得公开审判权等程序性权利,已然上升至法律权利的高度,获得了应有的法律地位,并受到以权利救济为职能之司法的有力保障。 因此,可以说,是司法为政治提供了合法性的资源,使政治体系的存续存在现实可能。 其二,司法权的运行使纸面上的法应用于实践,使政治意志得以实现。 政治对司法的介入使司法的规则要素有了政治意志的烙印。 但规则仅在司法对其予以适用时才能实现其所预设的价值、理念,形成体现政治意志的社会法律秩序。 因此,政治与司法在规则层面的关系中,政治对司法的依赖是主要性的。 其三,司法通过个案裁判将制度蕴含的政治理念生动地展现给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并就特定社会、道德争端形成价值导向,塑造社会的价值观念。 如学者所言:“依赖法院和司法技艺来解决核心的道德困境、公共政策问题和政治争端,已成为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前期政府治理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 ”政治引导着司法运行及改革的方向,司法则将此作用于社会,完成政治思想、理念的宣传与贯彻。
第二,司法对政治的制约。司法的政治属性与功能,并不等同于“司法服务于政治”,司法与政治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 司法从其渊源来看,是独立于国家议事机能、行政机能的第三机能,且与议事机能、行政机能有不同的职责范围,三者之间互不隶属,这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便已确定。 经近代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汉密尔顿等人的发展,司法独立及司法与行政、立法相互制衡成为司法的应然之义。 从司法权的运行来看,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司法解释权与司法审查权三项基本权能。
这些权能的运用,使司法在政治领域实现了对官员的监督、对行政行为的诉讼以及司法审查功能。因此,司法对政治的制约也是司法权运行的必然结果。鉴于司法的程序化特征与机制,司法是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来规约政治权力,这也使得司法成为制约政治权力最为恰当的方式。
四、协调司法政治属性与相关司法理念的冲突
前文的论证已表明,司法制度的确立与发展深受政治环境的影响。 司法的政治属性主要从立法、组织与人事、权力行使方式及范围等方面得以彰显。 不论是从司法的权力性质来讲,还是从司法的活动本质来讲,“司法与政治发生关系具有不可避免性”,“完全独立于政治的司法,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尽管如此,政治对司法的介入主要限于宏观层面对司法的领导与监督;作为对政治的回应,司法运行不仅使政治意志得以贯彻,也使政治权力有了制约,这对于国家政权的存续与社会的稳定发展而言,是不可缺少的。 在具体操作层面,如下问题还应进一步明确:(1)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和确保政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 “司法权威是制度的权威而非个人的权威。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是司法运行的基本法理,亦是我国明确的政策主张。 但在权力运行实践中,政治权力机关会有意无意地忽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政法领导工作中的重要性,进而出现“以权压法、以权代法”的现象,尤其是过多地插手和干预司法个案。 对此,在明确“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并非对立”的基础上,我们仍要探讨党对司法的领导方式。(2)司法具有的政治属性与司法行政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司法的政治属性更多通过司法机构、司法制度设置及人事任免等特征得以体现,但中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以行政方式操作司法”的现象。 后者抹杀了司法权区别于行政权的“交涉性”特征,即相较于行政权以单方行使为特征,司法权更强调多方的参与性。 司法行政化的泛滥,会损害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使包括政治功能在内的司法功能无法实现。 在坚持司法独立、司法中立等司法基本理念的前提下,探讨法院审判管理、司法行政事务管理与司法权的关系,逐步实现司法的去行政化,这些问题的厘清有待专门研究。
参考文献:
[1]卢上需,王佳.论我国司法权的政治属性和基本功能[J].法学评论,2013,(2).
[2]吴卫军.司法改革原理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3]R.Tyler:why people obey the law[M].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 and London,1990.
[4]蒋超.论司法权威[D].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5]江必新.司法与政治关系之反思与重构[J].湖南社会科学,2010,(2).
[6]施鹏鹏.司法无偿是所有人的正义[N].法制日报,2011-12-07.
[7]〔意〕莫诺·卡佩莱蒂着,徐昕,王奕译.比较法视野中的司法程序[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8]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9]龙宗智.转型期的法治与司法政策[J].法商研究,2007,(2).
[10]钟瑞庆.司法与政治———“转型期法治”全国研讨会综述[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3).
[11]2013年度最高法院十大司法政策[N].人民法院报,2014-01-04.
[12]〔法〕托克维尔着,董国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3]陈琦华.当代中国司法政治功能内涵及其价值[J].政治与法律,2013,(1).
[14]马克斯·韦伯着,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5]程竹汝.论现代司法的政治制度化功能[J].政治学研究,2002,(2).
[16]扶摇.司法治理与政治司法化———读赫希《迈向司法治理———新宪政主义的起源与后果》[J].清华法治论衡,(14).
[17]周永坤.政治当如何介入司法[J].暨南学报,2013,(11).
[18]胡夏冰.司法权:性质与构成的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
[19]汪建成,孙远.论司法的权威与权威的司法[J].法学评论,2001,(4).
[20]龙宗智,袁坚.深化改革背景下对司法行政化的遏制[J].法学研究,20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