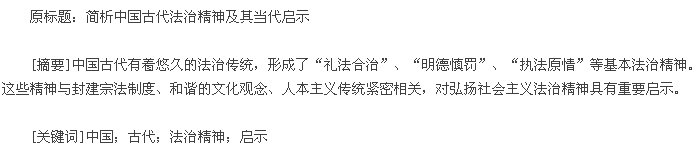
一、中国古代法制传统与法治精神①
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运用法律进行治国理政的传统。早在上古时期,就出现了专门主管氏族部落内部刑罚事务的人员,并制定了著名的“流宥五刑”(大辟、劓、刖、宫、黥),用以维护氏族部落内部的治理秩序。到了夏商两朝,国家司法制度初现雏形,设置了相应的司法官吏,如夏朝的“士”(或称“理”)、商朝的“司寇”.西周取代殷商之后,司法制度更趋完善,建立了相对成熟的审判制度和诉讼制度,形成了较为系统国家司法体制。春秋战国时期,更出现了以先秦法家为代表的古典法 治 思 想,其 核 心 内 容 在 于 “为 国 以法”、“以法为本”、“依法治国”,用以反对彼时儒家的“德治”和“礼治”,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奠定了法治思想基础,并对后世封建法制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秦统一六国之后,古典法治思想成为国家统治思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管理的方方面面都已“皆有法式”(《史记·秦始皇本纪》)。代秦而起的西汉,鉴于秦朝严刑峻法之弊,在国家法制建设中先后经历了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儒法合流的新儒学、神权法学及反神权法学的斗争等阶段。后至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名法之学、玄学法哲学等思想,建立了尚书台、廷尉和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为中国古代的封建司法体系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统治者致力于国家法典的建设,先后形成了《开皇律》《五经正义》《唐律疏议》等,更在审判、诉讼等方面建立了成熟完备的制度,并广泛为后世所沿用。及至宋明两朝,理学思想作为国家哲学成为法制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政治改革家和理学反对派,主张“立善法”、“以法绳天下”.
满清时期,社会变动,民间和官方都孕育着新的法制思潮;在民间,涌现出黄宗羲、顾炎武等带有启蒙精神的法制思想,主张批判君权,破除旧制,“以天下之法”代替君主“一家之法”;在官方,统治者在总结继承历代法制建设基础上,建立了相当完备的封建法制体系,甚至还因地制宜、因俗制宜地建立了边疆少数民族法律。
纵观中国古代法制传统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法治思想及实践虽然朝代各异、接续发展,但蕴含于各种法治形式之中的基本价值、核心观念与实践原则保持了相对的长时段的历史稳定性,这些价值、观念和原则构成了中国古代法治精神。正如许章润教授所言,汉语法学虽多转折,“但是,总体来看,其文明品格和内在义理,于折中损益中脱胎换骨,却一脉沿承,不绝如缕。”[1]
然而对于“其文明品格和内在义理”亦即法治精神的具体内涵的概括,则见仁见智。如张晋藩教授将之概括为“礼法互补、综合为治',德主形辅、明德无讼,执法原情、法情并重,立法等差、良贱有别,皇权至上、法自君出,漠视权利、详订义务诸端”[2].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古代法治精神主要还在于“慎重刑狱”、“礼乐政刑相互为用”[3].概而言之,我们似乎可以从“礼法合治”、“明德慎罚”、“执法原情”这三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法治精神的基本要义。
所谓“礼法合治”就是将“徳礼”与“刑法”共同作为国家治理工具。“礼”表现为一系列以一定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为内核的典章、制度、规范和仪节,对君王相臣和平民百姓都具有相对的内在约束力。“法”则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与儒家“礼治”相对的法家之“法”;二是指具体的法律制度,如律法、条令等。“礼法合治”既是指中国古代在法治实践上“德礼”与“刑法”的交融共通,也是指二者在精神层面的贯通互补。礼是通过道德准则、伦理血亲、宗法秩序等内在精神规范来维护社会秩序及阶级统治,属内在调控力;法通过国家权力厘定人们的义务和权利,建构和维护在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所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属于外在约束力;礼与法都是维护社会稳定和阶级统治的工具,但一内一外、一刚一柔、一外显一内敛、一无意一有情,二者交融共生,形成了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法治工具体系。
“明德慎罚”出自《尚书·康浩》中的“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4],原意是崇尚德惠而宽缓刑罚,与“礼法合治”一脉相承。“礼法合治”更多强调法治的治理手段和统治方式问题,而“明德慎罚”则关注于法治所要达到的治理效果及最终目的---即彰显德性、教化 民众而非惩罚恶行。对此有学者曾有过明确解释:“明德,倡导本阶级伦理道德并用忠、孝等道德观念教化灌输百姓,使社会成员的头脑中形成预防犯罪的精神堤坝,有效地遏制犯罪。慎罚,在适用法律与实施刑罚时,保持克制与审慎。除不得不杀的重大犯罪外,一般都可以宽缓处理。”[5]
“所谓执法原请,就是希望司法官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既依法断案,也要考察流行于社会而被广泛认同的情理、人情,做到法情允协,既减少推行法律的阻力,又宣传了明刑弼教的立法宗旨。”[6]具体而言,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强调官吏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法律。如秦朝时就将是否“明法律令”作为区分“良吏”与“恶吏”的判断标准,对不“明法律令”的官吏处以“失刑”、“不直”、“纵囚”等罪。二是强调官吏在办案过程中不能只依据法律条文,而应根据优良习俗、世道人心酌情而定、顺情而为。如中国古人常讲的“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刑”(《盐铁论·刑德》,“宥过无大,刑故无小”(《尚书·大禹谟》)等理念,就是“执法原情”的重要体现。
二、中国古代法治精神的文化阐释
瞿同祖先生曾说:“法律是社会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它维护现存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它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7]1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法律及其背后价值精神说到底都是特定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习俗传统的集中反映,植根于社会文化之中。同样中国古代法治精神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紧密相关。
封建宗法制度是中国古代法治精神的制度基础。宗法制度产生于以农耕文明与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倡导“亲亲”、“尊尊”,以“重视宗族血缘关系”、“尊重服从等级差异”、“重人情轻法律”等为基本特征。在宗法制度下,家国一体,政治权力更具延展性和统摄性,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相辅相成。家庭不仅是社会结构中的基本生产单位,也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管理单位。封建家长或宗族长承担着调节宗族关系、稳定家庭秩序的责任。国家稳定正是依托普遍的家庭和睦来实现。在封闭且以血亲关系为主的宗法制度中,维护晚辈对长辈的尊重服从是秩序可控的关键点。为此它一方面强调代际间的等差性,另一方面又重视宗族内的亲情关系。在治理手段上,相比于只能维护等差但无法兼顾亲情的“法”,相对温情的“礼”则既可以维护尊卑之间的等差性,又可以强化和稳固家族内的亲情关系,更适用于调节包含着普遍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的矛盾纠纷。在治理的目的上,相比于强调震慑和惩罚的“刑法”,宗族之人则能具备萌发自内心的“亲亲”、“尊尊”之德,由此达致宗族内部的治理和教化。所以“礼”作为教化工具可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8],“德”作为教化旨归可以使人“有耻且格”.“礼法合治”与“明德慎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兼顾并行。除此之外,宗法制度催生的“熟人社会”,使“人情”成为维系社会秩序有效运转的轴心,在人情与法律出现冲突的时候,人们往往会秉持“执法原情”的理念,通过凸显人情地位来强化和巩固宗法制度。
注重和谐的文化观念是中国古代法治精神的哲学基础。和谐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都对其进行过相关论述,并在各自的学说中应用甚广。这一观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即社会生活的和谐)以及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等四个方面”[9],表达了中华文化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关系深刻而独到的理解。“礼法合治”、“明德慎罚”和“执法原情”集中体现了这一文化观念。例如“明德慎罚”可以视作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天人合一---的体现。一方面,天人合一既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包含了人应该效法自然、顺应自然规律的意味,以最终达到天道与人道的合一。运用到国家治理中,就是强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民之所欲、天必丛之”(《尚书·泰誓上》)。由此天人合一便与德政、仁政联系起来,天道秩序便成为“王天下”的基本遵循。而过度使用刑罚只会破坏天人合一的和谐秩序。良性的国家治理应该通过彰显德行、减少刑罚来使社会处于有序和谐的运转中。再如,“礼法合治”可以视作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体现。“礼”与“法”都是统治阶级用于统治社会、教化社会的工具,也是将个人与社会规范连接起来的中介和渠道。法律的实质在于运用国家权力的强制力与权威性来达到管控的目的,而礼的实质在于运用人心与人情的内在约束力以达到自律的目的。当人与法律形成冲突时,以强权为基础的强制力管控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人与社会的内在矛盾,而礼则用相对温和的教化方式使人与社会达到较为和谐的关系,从而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和谐相处的特征。
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传统是中国古代法治精神的价值基础。以人为本、关注生命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传统,它不仅构成了中国人务实厚重、疑天保民的价值取向,也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治理国家、建立盛世的价值遵循。管子曾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而国固”(《管子·霸言》)。相比于西方文化关注的“彼岸世界”,中国古代文化更注重“此岸”的现实世界,致力于实现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幸福,由此生成了直觉性的人本主义传统。在这一传统观照下,以“人性”为基础的“礼”似乎更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逻辑,而中国古代法治精神正是凸显了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及关注。如,“明德慎罚”将提高人的道德素养作为旨归,力图规避会对人造成伤害的刑法,突出了人的地位。“执法原情”则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努力保障民生,在刻板的法律中注入鲜活的人情,将维护人的利益与尊严作为法治的最终旨归,是“仁政”和“保民”思想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这种以直觉性人本主义为基础的法治 精 神 也 带 来 了 一 定 的 问 题。比 如 在 促 进“情”与“法”、“德”与“法”和谐统一的同时,也为封建人治传统打下了基础。再如中国古代法治精神所强调的“以人为本”往往停留在对治世、盛世的理论憧憬和价值规约之中,然而在现实却仍坚持皇权至上、等级观念,而缺乏个人本位的民主法律思想。这大概是中国古代缘何没有发展出现代法治精神的根源之一。
三、中国古代法治精神的当代启示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是新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重要任务。***同志指出:“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传统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10].这就要求我们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过程中,应积极借鉴中国古代法治精神的有益做法,努力增强法治建设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应该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中国古代法治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儒家化”,亦即是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法律化。对此瞿同祖先生明确指出:“古代法律可说全为儒家的伦理思想和礼教所支配”[7]353.当然中国古代法治并非一开始就受儒家思想支配,如秦汉法律基本上就是延循法家思想而来,但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开始作为一种国家哲学而统摄法治发展,并由此开启了“引礼入法”的儒家化进程。这一过程有力确保了中国法治传统的历史稳定性。究其原因,是因为法律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形式,具有鲜明的价值判断性与政治倾向性。
不同国家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法治精神,同一国家的不同阶级或政治集团也总是会提出不同的法治诉求。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法治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自觉将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联系起来。否则就会南辕北辙、事倍功半。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应该重视发挥道德力量。中国古代法治精神重视发挥道德对法治建设的支撑作用。所谓“不知耻者,无所不为”(欧阳修《魏公卿上尊号表》)。无论是“礼法合治”还是“明德慎罚”,其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德治思想。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法治精神的德性传统,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发挥法律对于社会道德的规范作用,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特别是注重将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基本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着力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强化道德作用、筑牢道德底线,提升法律的道德意蕴和人文关怀[11].同时,还要发挥道德对法律的教化作用,用道德精神滋养法治精神,增强道德对法治氛围的营造作用和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着力通过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构筑现代道德体系,提升社会道德水平,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道德基础。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应该对古代法治精神进行积极扬弃。如何对待古代法治精神,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法治文明传统的国家来说,是个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同志所说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应该成为我们对待古代法治精神的指导原则。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新时期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特点和要求,对古代法治精神中具有现代价值的内涵和形式进行改造,赋予其以新的时代内涵及表达形式。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新时期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发展新成就,对古代法治精神的内涵进行深入开掘和完善发展,并通过各种方式使之深入人心,筑牢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弘扬的历史文化根基。做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对中国古代法治精神进行实事求是而非责备求全的研究,既要看到中国古代法治精神植根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之中,顺应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富有“人治”色彩,与现代法治精神并不相互吻合,不可直接搬用;也要避免妄自菲薄,言必称希腊,将西方法治传统当作中国法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应立足中国法治建设的历史文化传统,挖掘古代法治精神的本真意涵和当代价值,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法治言说体系。
[参 考 文 献]
[1]许章润。汉语法学论纲[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5-72.
[2]张晋藩。论中国古代法律的传统[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4(2):62-68.
[3]陈景良。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法律的历史借鉴[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2):30-39.
[4] 王 世 瞬。尚 书 译 注 [M].成 都: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1982:149.
[5]樊鸣。论“明德慎罚”及其对后世的影响[J].法制与社会,2007(4):750-751.
[6]张晋藩。中国古代司法文明与当代意义[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2):20-30.
[7]瞿 同 祖。中 国 法 律 与 中 国 社 会 [M].北 京:中 华 书局,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