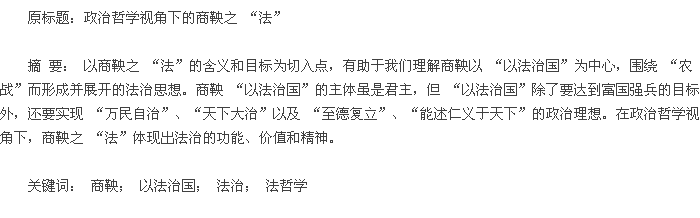
商鞅是先秦时代早期法家著名代表人物,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围绕 “农战”所制定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仅使秦国实现了 “富国强兵”的目标,也为秦国后来统一六国夯实了基础。商鞅制定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之所以能被贯彻落实并取得成效,靠的是“刑赏”的推动,而 “刑赏”则是 “法”得以实施的重要手段。换言之, “法”既是具体的法令、政策,也是商鞅政治思想的理论核心或核心理念,又是 “农战”和 “刑赏”的内在规范。因此,在法哲学视角下审视并反思商鞅之 “法”①的含义和目标,有助于理解商鞅政治思想的要旨,并为当前的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借鉴。
一、商鞅之 “法”的含义
《商君书》中,有关 “法令”、 “法制”以及 “法”的表述非常多,比如: “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1]131; “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1]130,“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1]144; 等等。从基本语义层面分析,商鞅所描述的“法令”、“法制”和 “法”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禁令。商鞅所制定的一系列有关农战的奖惩措施,就是比较具体、明确的法律、禁令,如 《垦令》中颁布的 20 条垦荒法令。同时,商鞅对“法”也有明确的定义,即 “法者国之权衡也”[1]83.这一概念从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层面道出商鞅之 “法”的含义,即 “法”不仅是一种理想的治理国家、组织社会、建立秩序的政治原则、路线和方略; 而且又具有 “使法必行之法”的深层意涵---制定相应制度以保障 “法之必行”并最终实现天下大治。正因如此,商鞅所主张之法律的规范性、公开性、公平性、通俗性等特征[2]42-44才得以凸显,他的一系列政治原则、路线和方略也有了可以实施或实现的载体。
( 一) 政治思想层面的含义---使 “法之必行”
在政治思想层面,商鞅之 “法”指的是一种理想的治理国家、组织社会、建立秩序的政治原则、路线和方略,体现了商鞅系统而完备的法治思想理论。较之基本语义层面上的 “法”,政治思想层面上的 “法”更能凸显商鞅政治思想的特质。在 《商君书》中,商鞅将其表述为 “缘法而治”[1]130、“任法而治”、“以法相治”[1]137、“垂法而治”[1]61等,意指依靠法律的强制性和规范性来约束臣民乃至君主,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并最终实现天下大治。就此而言,商鞅之 “法”是对《管子》“以法治国”①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即 “以法治国”作为商鞅之 “法”的深层结构,其含义主要是: “明主治国,惟法是视,不仅要立法创制,而且要坚守法令度量,做到动无非法,依法赏诛而不阿贵不遗贱。”[4]2亦如有学者所言: “法家政治哲学,有一个共通的原则,便是认定 ‘法'为一切之规范,为治国之张本。”
[5]4同样,在政治思想层面商鞅之 “法”也以此为 “张本”,并通过 “法的统治”将其实现。
政治思想层面的 “法”,即商鞅的法治思想包含了 “以法为治”, “生法者君也”, “法之必行”,“救世、富强、致治、尊君”等四大互相关联的要义。[4]8其中,“法之必行”是商鞅法治思想的关键; 无此,即使有法可依,也难以实现 “救世、富强、致治、尊君”的政治理想。那么,商鞅如何使 “法之必行”呢?
其一,要使 “法之必行”,必须使所颁布的法律、禁令取得公众的充分信任,即具有公信力。
商鞅认为, “法在推行和严格执行过程中是一个严肃性、权威性和有效性的诚信问题。这是迈向’法治‘最为关键的一步,因为这事关法律的威慑力。一旦身处上层的权贵破法不罚,身处下层的民众就难以建立起对新法和国家的信赖”.[2]43《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商鞅 “徙木立信”的故事正说明这一点。同时,商鞅也道出了新法乃至国家获得公众信赖的重要性, “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1]82; “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敌矣”.
其二,要使 “法之必行”,必须保证所颁布的法律和禁令完全公开、通俗易懂。商鞅主张公布成文法,并在 《定分》篇再三强调其 “法”要 “明白易知”; 同时,又主张 “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以利于法律、禁令的普及,使妇孺皆知。因此, “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1]146可见,完全公开、通俗易懂的法律、禁令,不仅是 “法之必行”的前提,也是实现万民自治的基础。从秦国 “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6]71可以看出,普法教育的确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
其三,要使 “法之必行”,必须坚持法的公平性。商鞅将法的公平性视作 “壹刑”,也就是司马迁所称的 “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8]3291.商鞅对此的定义是: “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 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1]100-101在商鞅看来, “法之必行”的关键在于 “上”和“贵”,只有自 “上”、自 “贵”行法,“刑无等级”才不致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商鞅将 “法之不行”归于 “自于贵戚”[9]205和 “自上犯之”,并 “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10]2231以惩太子犯禁之过。
其四,要使 “法之必行”,必须保证 “权制断于君”.商鞅认为,权势只有集中在国君一人之手,所颁布的法律、禁令才具有威慑力,才能保证 “法之必行”,才能顺利推行 “法治”.他说:“国之所以治者三: 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 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
对于国君而言,不仅要独揽大权、树立威势,还要 “重信而不以私害法”,即做遵法、守法的表率,才能称得上 “明主”,才能使所颁布的法律、禁令具有威慑力,进而推动 “法之必行”; 对于民众而言,“从令”是 “尊君”的最好表达方式,因为 “君尊则令行……民不从令而求君之尊也,虽尧、舜之知不能以治”[1]130.
( 二) 政治制度层面的含义---“为法置官吏”
商鞅在 《画策》篇指出: “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 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
[1]109他认为,要使 “法之必行”,除所颁布的法律、禁令应具有规范性、公开性、公平性等特征外,还应有 “使法必行之法”以及 “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作保障。那么,“必行之法”以及 “必得之法”中的 “法”指的是什么呢?
在商鞅看来,实施 “为法置官吏”制度,就是 “使法必行之法”以及 “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在 《定分》篇,商鞅详细论述了 “为法置官吏”制度的方法、目标和意义。他认为,从中央到地方统一设置法官、法吏,既可达到 “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的普法目的,又可形成 “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的人人守法的良好社会秩序,还可杜绝类似于 “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能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等违法、贪腐案件的发生。
[1]144同时,该制度又以 “重刑”作保障,即对知法犯法的法官、法吏施以严酷的刑罚,用商鞅的话来说就是 “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依此观之,商鞅首先是要在臣与民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从而营造一个人人知法、人皆守法的良好的社会秩序; 其次,这种机制和社会秩序的形成之时,也就是万民自治、天下大治之时。所以,商鞅所指 “必行之法”的 “法”既是一种制度的支撑,也是在这一制度支撑之下的法治的根本精神和价值的体现。
虽然这一制度是在 “重刑”的保障下实施的,但是仍对法治社会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商鞅之 “法”在制度层面的深层意涵也正表现在于此。
总之,商鞅之 “法”的含义,除在基本语义层面泛指法律、禁令外,在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层面指的是一种治国方略、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即 “法治”.其中,“法之必行”是 “法治”思想得以实施的关键,而 “法之必行”除需要以法律的规范性、公开性、公平性及 “权制断于君”
二、商鞅之 “法”的目标
商鞅之 “法”的目标可以分为两个层级,第一层级目标是实现 “富国强兵”,第二层级的目标是实现 “天下大治”.第二层级的目标建立在第一层级目标的基础上。在商鞅的政治规划中,这两个层级的目标都以 “法”为前提,以 “壹赏”、“壹刑”、“壹教”为目标原则加以实现。
( 一) 商鞅之 “法”的目标
商鞅之 “法”的目标分两个层级逐步推进,第一层级的目标是由 “法”致 “强”,即实现富国强兵; 第二层级的目标是由 “法”致 “治”,即实现天下大治。商鞅除重 “法”、崇 “法”、行“法”外,还是十分注重 “力”和 “刑”的作用,认为 “力”可实现富国强兵,并将 “农战”作为实现 “富国强兵”目标的主要途径,极力倡导。故而,他说: “故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
并在 《农战》篇再三强调说: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同时,商鞅的 “农战”又是靠 “法”推动的。以 “法”推动 “农战”,通过 “农战”实现 “富国强兵”,商鞅之 “法”第一层级的目标在此架构下得以实现。“力”除了能使国家强盛、君主有权势和威望外,还可使全国乃至全天下形成一种道德风尚,即 “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
对此,商鞅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 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 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效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也就是说,一国家之内用 “力”和 “刑”,可实现国内政治秩序的有序运行; 两国同时用 “力”,则国与国之间就会相互制衡,致战乱不发; 所有国家都有 “力”,道德就会蔚然成风,故此可 “述仁义于天下”.在商鞅看来,“法”和 “力”既可以实现国家强盛,也可实现天下的 “大治”,并且这种“大治”状态是以国家的强盛为基础,以 “德”和 “仁义”为前提和表现形式的。这样,第二层级的目标也被商鞅设计出来。
( 二) 目标的实现原则
商鞅之 “法”目标的确定乃至政治体系的建构是从 “定分”开始的。 “定分”即确定名分,而 “名分”则是与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紧密相联的焦点问题。战国时期,“土地私有的国民富族正催促着以血族纽带为基础的土地国有制发生变化”,[11]20-21从而使战争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七国纷战犹如 “众人逐兔”一般,看似在争夺霸主之位,实质则是要确定土地的权属 ( 名分) .那些 “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1]145的祸乱现象,均源于 “名分”之不确定。基于此,商鞅认为:“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1]52这样,在 “土地私有与公权制度以及法律相为联带的关系”[11]21之下,“分定→立禁→立官→立君”逆向承接,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治理架构。在这个治理架构内,国君管理群臣,群臣执行法令,法令保障之下的土地、货财、男女等 “名分”问题得以确定,乱和争随之止息。同时,在 《修权》篇,商鞅为使 “公私之分明”,还以 “立法明分”的方式将 “名分”法律化。他指出:“先王知自议私誉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
[1]84正如蒋礼鸿所言: “商鞅之道,农战而已矣。致民农战,刑赏而已矣。使刑赏必行,行而必得所求,定分明法而已矣。”[1]19可见,“定分明法”之后,君主治理国家的依据和臣民行为的规范都更加明确, “致民农战”的手段更加集中,富国强兵的目标也更加明确。为实现这一层级的目标,商鞅提出 “教民作壹”的主张,并通过 “壹赏”、“壹刑”、“壹教”三项原则,以统一思想认识,驱使人民于农战之中。“壹赏”,即统一奖赏的标准,以此来规范人民获取利禄官爵的途径。商鞅指出, “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1]96; 亦即 “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1]129.也就是说,受赏的原因除有功于农战之外,再无其他。这样,才能聚民力于农战之上,从而收到 “民见上利之从壹孔出也,则作壹; 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1]20和 “边利尽归于兵者强,市利尽归于农者富”[1]129的效果。“壹刑”,即统一刑罚标准并平等地适用法律,以保障 “法”之实施。商鞅所言之 “壹刑”,是对其法的公平性的最好诠释。因为只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才具有公信力,才会成为全社会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壹教”,即以法为教,是指通过法令的形式统一教育内容,打击和取缔不利于农战及违背法令的思想言论,从而起到规范和统一人们思想认识的作用。商鞅认为,由于儒家所倡导的仁义道德不仅 “不足以治天下”,[1]113而且会直接影响到农战,即 “农战之民千人,而有 《诗》、 《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
因此,“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 《赏刑》) 之流,非但不能 “富贵”、“评刑”、“独立私议以陈其上”[1]104还要予以取缔; 而 “富贵之门”则只为那些在战场上杀敌立功者敞开。同时,商鞅将 “壹教”与 “法”之公开性、通俗性和公平性相关联,通过“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1]146对人民进行普法教育,从而使法律成为约束臣民行为的唯一准则。
在 “壹赏”、“壹刑”、“壹教”的合力之下,商鞅之 “法”第一层级的目标得以实现。对于商鞅之 “法”第二层级的目标---天下大治,商鞅认为是通过人民的 “自治”得以实现的。那么,人民何以 “自治”呢? 这仍需要 “定分”和 “明法”或者说是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来实现。商鞅认为,社会上之所以产生 “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1]145的现象,主要是因为 “名分”之不确定。因此,用法律的形式将 “名分”确定下来,同时让人人都知晓法律的利、害之处,不仅纷乱和争斗自然会随之止息,而且人民也会安于 “自治”.正所谓 “名分定,则大诈贞信,民皆愿悫而各自治也”,以及 “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1]146但是,无论是从 “定分”到 “自治”,还是从 “避祸就福”到 “自治”,都要通过法律的强制性使外在的 “硬约束”变为人民内在的行为习惯。也就是说,“人们行为习惯在法律这种稳定性及明确性的制度约束下,经过长期潜移默化地熏陶,将由外在的行为规范逐渐转化为个体内在的自律,并且最终内化于心成为无意识的行为习惯,法作为对权利的保护和对过错的防范将让人们产生发自内心的信仰”.
[11]95这时,社会开始进入 “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于家”和 “治不听君,民不从官”[1]40,41的自治而有序的 “万民自治”、“天下大治”[1]146状态,并经此迈入 “天下行之,至德复立”[1]57和 “能述仁义于天下”[1]82的 “至德”阶段。令人扼腕的是,这种 “至德”的理想社会形态的设计还未及成型,即随着商鞅身遭 “车裂”之刑而陨灭于萌芽状态,从而留给后人的只是一个 “由非人格化的法律机制、’技术‘和神秘的权势支配”[13]359的 “乌托邦”梦想。然而,就是这个 “梦想”让人体悟到,“社会完全法治化之日,恰恰又是社会高度道德化之时,至大至刚的法之精神与至善至美的伦理境界水乳交融”,所形成的 “仁义的真正底蕴”,[14]32正是当今社会孜孜以求和亟需实现的目标。
( 三) 目标实现原则的特质
政治哲学的社会功能在于提出和论证时代所需要的政治价值,而 “政治价值以具有特定社会文化内涵的 ’人‘及其本质特征为基本内容,构成人类政治生活的价值标准与价值目标”.[15]76商鞅之 “法”的政治目标---富国强兵和天下大治,正是其价值目标的体现; 而政治目标的实现原则--- “壹赏”、“壹刑”、 “壹教”,也是围绕价值目标所形成的价值标准。在 “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价值标准服务于价值目标,二者共同构成秦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因而,从商鞅的“进化观”、“人性论”、“力治说”入手,分析商鞅之 “法”的目标的实现原则及其相互关系,有助于在政治哲学的视角下理解商鞅之 “法”的特质。
首先,从价值标准的制定来看, “壹赏”、 “壹刑”、 “壹教”的提出和实施不仅有理论支撑,而且还具有 “特定性”.商鞅 “壹赏”、“壹刑”、“壹教”的制定,完全以 “历史进化观”、“好利恶害人性论”和 “力治说”为依据。其一,在 “历史进化观”的支撑下,新法的制定有了理论基础; 以新法为工具,“壹赏”、“壹刑”、“壹教”的提出和实施也就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同时,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以 “求富求强”为目标而展开的变法活动,是顺应社会历史发展变化而出现的一股政治潮流。在这股大潮的推动下,商鞅根据秦国国情以 “壹赏”、“壹刑”、“壹教”为原则形成的 “农战思想”,呈现出显著的 “特定性”---既与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相一致,又以秦国的社会现实为基础。可以说, “历史进化观”是实施 “壹赏”、 “壹刑”、 “壹教”的前提。其二,提出“壹赏”和 “壹刑”的出发点就在于人民具有 “好利恶害”的本性。战国中期时的秦国,是一个地处偏远边境的 “半野蛮国家”; 在这个国家,只有上层阶级才有条件 “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
在商鞅看来,这一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大多数秦人都具有 “好利恶害”的本性。因此,根据人好利的本性,将人们普遍追求和向往的 “利禄官爵”仅限定在 “农战”的范围之内,即 “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1]139以利于在短期内实现富国强兵的价值目标。其三,人民在 “刑”与 “赏”且是 “刑”大于 “赏”的利、害权衡之下,“壹赏”最终将富国强兵的价值目标实现,即 “利出壹孔→作壹→民不偷营→多力→国强”.这样,蕴藏在 “壹赏”之中的 “力治说”也便清晰地呈现出来。总之,“教”、“刑”、“赏”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来规定和实施,使政治生活的价值标准与价值目标,即 “壹赏”、“壹刑”、“壹教”和 “富国强兵”,很快成为秦国臣民的共识。
其次,从 “壹赏”、“壹刑”、“壹教”各自的功能来看,“富国强兵”目标的实现也有赖于这三项价值标准间的相互配合和相互补充。对于 “壹赏”、“壹刑”、“壹教”各自的功能,商鞅总结说: “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
可见,“壹赏”、“壹刑”、“壹教”三者逆向依次递进而又相互补充,即由 “下听上”实现 “令行”,由 “令行”致 “兵无敌”,从而成为实现商鞅之 “法”第一层级目标---富国强兵的有力推手。也就是说,“壹教”不仅强化了人民的法制意识,同时又使商鞅所制定和树立的价值标准与价值目标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 在 “壹刑”的强制作用和 “壹赏”的利益引导下,这个 “全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标准与价值目标”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最终将 “富国强兵”的价值目标变成现实。
三、政治哲学的视角下的审视与反思
在国家治理中,法律是实现依法治国、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核心,而依法治国又是实现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前提和主要手段。
①同时,在依法治国过程中,法治本身即包含法律的基本特征,因而法治在工具价值和治理功能上自然也就体现出法律的强制性特征。这种强制性作用将人的行为以及国家权力的运行逐渐由他律转化为自律后,法治的发展进入到法治国家阶段,其间也需要道德的内化作用。在法治国家阶段,法治在工具价值和治理功能上主要体现出自律性特征。当国家与社会完全依靠法治及道德的自律性作用运转时,即社会完全法治化和高度道德化时,法治的根本精神和价值得到充分发展和体现,法治的发展开始进入法治社会阶段。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在法治国家还是在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或者是在二者共同建设的过程中,法治的强制性作用都没有消失或被弱化,而是内隐于其自律性特征或根本精神价值之内。依此观照商鞅之 “法”,商鞅 “以法治国”的主体虽是君主,但 “以法治国”除了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外,还要实现 “万民自治”、“天下大治”和 “天下行之,至德复立”及 “能述仁义于天下”的政治理想。因此,商鞅之 “法”在其形成、发展和实践过程中体现出法治的功能、价值和精神。
既然 “以法治国”是 “运用和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16]16那么商鞅之 “法”自然也就兼具时代性、必要性、公开性、公平性、强制性等法律的基本特征。第一,商鞅以历史进化观为依据,认为治国不应恪守陈规、照搬旧法,而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法律。以法治的功能和作用反观商鞅 “度俗而为之法”,[1]63虽没有 “忠实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反映人民的根本意志”,但却是根据秦国的社会现实 “努力改造人民群众中的某些落后意志”.[17]
列宁指出: “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18]252这种 “最可怕的势力”一旦上升为法律,将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的良性发展。
从这个意义来说,商鞅之 “法”所呈现出的时代特征,才使 “以法治国”具有了现实针对性和可行性。第二,要 “运用和依照法律治理国家”,必须充分认识 “法”的必要性。在商鞅看来,法律是 “民之命”和 “治之本”,[1]144只有慎重立法,做到 “立法明分”,才能使 “民不争”,[1]82,84才能实现 “治”的目的。商鞅对 “法”的必要性的认识,是其 “运用和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前提。
在此基础上,“以法治国”也就具有了实施的可能性,而不终落为一种理论的设想。第三,法的公开性既有助于加快法治发展的步伐,又有利于维护安定的社会秩序。商鞅主张公布成文法并为此设置 “法官”,以使臣民明确知晓法的内容并按其要求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令臣民主动守法的目的。同时,也能在臣、民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机制。而人人知法、人皆守法的良好社会秩序以及相互监督制约的机制,不仅是 “使法必行之法”运行的最优环境和最佳制度支撑,也是 “法治国家”阶段的基本特征。第四,法的公平性、强制性是 “以法治国”的要旨所在。商鞅认为,法代表的是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利益,因而必须兼具有公平性和强制性,赏与罚应一律平等,不能因人而异。这样,坚持法的公平性和强制性才能将人性好利这种 “可资因循利用的人性弱点”[19]330发挥到极致,才能将人民驱使到农战之中,进而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第五,商鞅之 “法”中还含有通过法治实现 “万民自治”和 “天下大治”的政治理想。商鞅认为,通过法治的工具价值和治理功能,尤其是表现于其上的强制性作用,不仅可以实现富国强兵,还可以使秦国进入 “法治国家”或 “法治社会”阶段。商鞅理想中的 “法治国家”或 “法治社会”的标志是“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于家”和 “治不听君,民不从官”的 “天下大治”状态,特征是 “至德复立”和 “述仁义于天下”.同时,这一特征恰恰又是以社会完全法治化和高度道德化为标志,进而充分体现出法治的根本精神和价值。从以上分析来看,商鞅对法之时代性、必要性、公开性、公平性的认识和阐述,体现的是法治的工具价值和治理功能; 在法的公平性、强制性作用下,刑、赏共同实施于农战之中,使法治的工具价值和治理功能充分发挥作用,从而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及进入 “法治国家”阶段奠定了基础。同时,商鞅以 “法”致 “德”的政治理想设计,也体现出法治的根本精神和价值。
对于法治主体的认识程度和实践程度,决定着以法治国体系、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建设程度。在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就是以全体中国公民为主体,从中国实际出发建立起来的法治体系”,[20]即 “人民是法治的主体”的观点已成共识,故而中共中央作出“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21]的重要论断。从这种共识角度来看,法治建设的依靠力量是人民,法治所要保障和满足的是整个社会之上的全体人民的利益而非某个人利益。因此,法治的价值也不应是个体价值的体现,而应该是社会价值的体现。作为君主专制的倡导者,商鞅把君主定位为全国唯一的、最高的立法者,由君主独断并制定的法令,所维护的也只能是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君主专制制度下的 “以法治国”,自然也就成了君主的 “以法治国”.如果法治的主体---君主不变,那么商鞅之 “法”终将是 “王令”的体现,法无例外的平等实施也是将生杀大权有效集中到君王手中,树立君主绝对权威的需要。这样的 “以法治国”实质上是对人民的控制、驱使和镇压,其注重的仅仅是 “法治”在工具价值和治理功能上所体现出的强制性特征而已; 而法治的根本精神和价值却只能停留在理想状态,无实施更无实现的可能。在此意义上而言,商鞅的一系列政治主张随着秦朝的速亡而融于 “外儒内法”的绥靖政策之中,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若要使 “以法治国”真正体现出法治的功能、价值及精神,必须将法治的主体回归于社会,回归于人民。
参考文献:
[1]蒋礼鸿。 商君书锥指 [M]. 北京: 中华书局,1986.
[2]吴保平,张晓芒。 商鞅之 “法”及其刑名逻辑 [J]. 武汉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6) .
[3]黎翔凤。 管子校注: 中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2004.
[4]程燎原。 先秦 “法治”概念再释 [J]. 政法论坛,2011,( 2) .
[5]陈烈。 法家政治哲学 [M]. 上海: 华通书局,1929.
[6]何建章。 战国策注释: 上 [M]. 北京: 中华书局,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