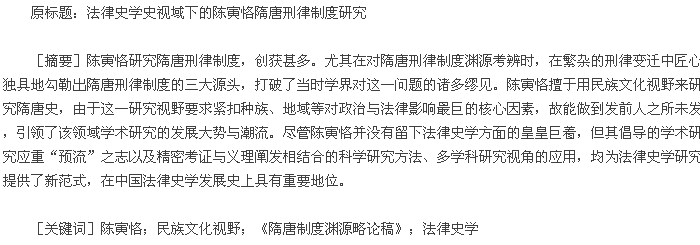
作为近代中国史学巨擘,陈寅恪一生着述甚丰,主要着述有《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
其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论稿》被学界视为最能代表其学术水平的两部着作。正如学者言,上述两部着作“不仅牢固地确定了陈寅恪在当时史学界中的崇高地位,而且也基本上奠定了他在近代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两《论稿》也使陈寅恪达到了他本人学术生涯的顶峰,因为从纯粹的学术价值上讲,他在以后所撰写的学术着作,都比不上两《论稿》”①。单就隋唐刑律这一研究领域而言,上述两书不仅多有阐发昔贤所未及见到之种种问题,书中所用民族文化视野治史路径,史观与考据兼长的阐释特色,更对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现代中国法律史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启发。因《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饱含对隋唐史的诸多创见,又能做到“鞭辟近里,发前人未发之覆”,故被学界赞誉为“唐代政治史的光辉的有洞察力的着作”②。陈氏也因之在隋唐制度史研究领域享有盛名。
一 匠心独具:隋唐刑律三大渊源考辨
相比较礼仪、职官部分而言,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陈寅恪对刑律着墨并不算多,仅在该章之首,用“隋唐刑律之渊源,其大体固与礼仪、职官相同,然亦有略异者二端”③等寥寥数语予以扼要概括。表面看来,关于礼仪、职官与刑律三者在着者心目中之地位高下之分似乎可谓一目了然,然事实并非如此,着者如此安排系经过深思熟虑,可谓别具匠心。在制度理论阐发层面,由于陈寅恪从繁杂的制度因革背后抓住了儒学这一关键因素,因此他特意把受儒学影响甚深的礼仪、职官与刑律列为先后联缀的三章进行考证与分析,以便突出它们的共同特点。另外,为了避免陷入相互重复之嫌,在刑律之部,对于在礼仪、职官部分已经详加考证且与刑律相同的内容就不再进行过多表述,而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刑律独具的内容上。这种精妙安排反而更凸显了作者的识见与匠心。故此,要考察陈氏对隋唐刑律考证所做贡献,我们须结合他在礼仪、职官部分的精妙卓识一并进行。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与刑律渊源问题密切相涉者主要有三个部分。
在是书序论部分,陈寅恪从宏观上概括出了隋唐制度的三个源头:一是(北)魏、(北)齐;二是梁、陈;三是(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
①这一识见对当时较为流行的隋唐制度直接源于“汉魏”的观点有所突破,凸显了陈寅恪治学之发展眼光。
尤为重要的是,陈寅恪在此还关注到了北魏、北齐之源中的河西文化因素,这一观点实发前人之所未发。关于梁、陈之源,他解释说:“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② 陈寅恪着重对南朝后半期文物制度之变迁进行了考察,由于王肃等人北入并未把这一时期南方的文物制度成果带入北方,因此北魏、北齐渊源中并没有把它包括在内。这种分析又突出反映了其分析问题较为全面的特点。对于西魏、北周这一渊源,他做了如下的解释:“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或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③ 关于这一渊源对隋唐制度的影响,他用了“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等语进行了总结。陈寅恪的这一观点颇为耐人寻味,突出反映了他在民族与文化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有了独到而深邃的见解。这种观点又对旧史中所持李唐之法制为(西)魏、周之遗业的偏颇看法进行了厘定与发展。至此,陈寅恪较为清晰地为我们梳理出隋唐制度因革的三条线索,也为我们总体把握隋唐刑律渊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同书礼仪部分,陈寅恪对隋唐礼仪源流的详细考辨为我们爬梳刑律之源提供了重要依据。陈寅恪采取了以礼仪为个案进行详加考证与分析,从而达到为其他相关制度渊源提供线索的研究思路。
因为陈寅恪明确指出刑律之渊源与礼仪渊源略同,因此,陈寅恪对礼仪渊源的考证就成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刑律制度渊源的突破口。在该部分,他先是通过梳理《资治通鉴》、《通典》、《隋书》、《魏书》、《北史》、《北齐书》、《魏书》、《南齐书》、《陈书》、《唐会要》等历史典籍的相关记载,并结合参与当时礼仪制度修订的关键人物的传记等相关资料,然后再经过充分考证、缜密分析,为礼仪三源论点提出了充分的证据。陈寅恪的结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北魏孝文改制吸收了汉魏、东晋以及南朝前期的礼仪制度;其次,通过对当时参与礼仪改革的关键人物,如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明克让、裴政、袁朗等人的身世、从政经历、学术渊源等进行考证分析,进而得出“隋修五礼,欲采梁、陈以后江东发展之新迹,则兹数子者,亦犹北魏孝文帝之王肃、刘芳,然则史所谓‘采梁仪注以为五礼’者,必经由此诸人所输入,无疑也”④ 的令人信服的观点;最后,陈寅恪用苏威父子的事迹为例论证了隋唐礼仪制度同样具有西魏、西周渊源。
陈寅恪对礼仪渊源的考证用力最多,所得观点也令人折服,对人们了解包括刑律制度在内的各具体制度的因革提供了甚大的帮助,备受学界赞誉当在情理之中。如朱绍侯说:“经过陈老的反复论证,不仅对隋唐的礼仪渊源探讨得一清二楚,就是对隋唐其他制度的来龙去脉也有所了解,这也是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大贡献。”⑤论及于此,我们已经更为详细地了解了隋唐刑律制度渊源的发展线索。
在刑律考证部分,陈寅恪对刑律发展的突出特点进行了着重强调。此处,他着重考证了刑律与礼仪、职官部分不尽相同的部分,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元魏正始以后之刑律虽其所采用者谅止于南朝前期,但律学在江东无甚发展,宋齐时代之律学仍西晋之故物也。梁陈时代之律学亦宋齐之旧贯也。隋唐刑律近承北齐,远祖后魏,其中江左因子虽多,止限于南朝前期”⑥ 。这一观点修正与发展了程树德所坚持的南朝刑律之渊源至隋唐制定刑律时已经断绝的论点。第二,“北魏之初入中原,其议律之臣乃山东士族,颇传汉代之律学,与江左之专守晋律者有所不同。及正始定律,既兼采江左,而其中河西之因子即魏晋文化在凉州之遗留及发展者,特为显着,故元魏之刑律取精用宏,转胜于江左承用之西晋旧律”①。上述二观点,进一步剖析了刑律发展过程中独有的特点,对我们更加深入把握刑律的渊源尤为重要。
二 民族文化视野:把握学术发展大势的新思路
陈寅恪治学的兴趣点在中古时期以来的民族文化之史,这从他的“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②一语中便可得到佐证。而从他对学界产生的影响来看,其在此领域取得的成就当然也最大。长期对民族文化问题的深入思考,使他在民族与文化关系问题上产生了独到见解,也养成了用民族与文化视角研究历史问题的治学特色。正如陈寅恪所说,种族与文化“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③ 。这一治学特色在其考证隋唐刑律制度时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用儒家文化发展的总势来考证刑律制度的流变。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问世之前,法史考证名家程树德曾就隋唐刑律之源头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自晋氏而后,律分南北二支:南朝之律,至陈并于隋,而其祀遽斩;北朝则自魏及唐,统系相承,迄于明清,犹守旧制。”
④由于程树德是当时着名的法律史专家,学术地位颇高,因此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然从学术渊源讲,程树德提出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拘囿于前人,即通过考察各自律例名称是否相同来梳理其渊源,其本人于此并无太多创见。如他在考证北齐、隋、唐律制相沿时曾明确指出:“律目之相同,而可知也。”而与程氏通过观察刑律名目异同来判断刑律制度是否变迁的方法不同的是,陈寅恪另辟用民族文化视角考辨刑律制度因革变迁之新路径,紧扣引领晋至唐时期社会发展的主流文化———儒学来追溯刑律发展流变过程。他认为:“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北)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律不祧之正统。”⑤ 言下之意,刑律儒家化是东汉以降中国古代社会刑律制度的总体特征。
换言之,儒法合流与并盛是当时文化的普遍现象,儒家文化发达地区的刑律制度也必然发达,同时,这一区域的刑律制度也往往成为那些儒家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刑律制度改革时所争相模仿的对象。
以此为思维基点,陈寅恪不唯高屋建瓴地指出了这一时期中国刑律制度的发展大势,同时还深入阐发了北魏正始修律后,南朝刑律制度对北方刑律影响日益式微的论点。深究起来,陈氏此论尚有商榷的空间,但比之包括程树德在内的同时期其他学者而言,陈寅恪的观点显然要较之更为全面与谨严⑥。
我们从当时其他学者的论点似乎也能够验证陈氏此论点的科学性。当时法律史学名家杨鸿烈在论及隋唐刑律发展因革时,也与程树德的“律分二支”说产生抵牾,如在商榷此论时说,“从汉代以迄清朝的末叶,所有盈千累百的成文法典,其支配法律内容全体的基本精神总之是同样”⑦,因此,“要勉强说‘南北律系’立法的根本原理彼此不同无充分证明,很为危险的”⑧ 。杨鸿烈此处所指的“支配法律内容全体的基本精神”,毫无疑问便是儒学。如此看来,尽管杨、陈出发点不同,但却得出了惊人一致的论点。
如果我们再结合陈寅恪早前所提出的“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⑨ 的观点,我们更容易发现,陈寅恪已经切中了中国刑律变革原因的关键因素———儒学,凸显了他在民族文化问题的思考上已经形成了不起的创见。
其次,家族(家世)与地域是陈寅恪民族文化视角所倚重的两大核心因素。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取得了统治地位,这一政治特色对当时的学术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一切学术文化,必以当时门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当时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由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有发展。门第在当时历史进程中,可谓已尽其一分之功绩”①。陈寅恪认为:“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者不可分离。”②陈寅恪此论似乎意在表明,以某一历史阶段的家族与地域为切入点,是把握这一时期学术与文化的又一关键因素所在。
正因为陈寅恪认识到了这一时代政治与学术之特殊关系,故此,在追溯其法律制度变化时,陈氏紧扣家族与地域这两大核心因素,经过条分缕析,层层严密考证,最终能够做到发前人之所未发,提出诸多引领该学术领域的论点。
如在考证北魏孝文太和之前的初次律制改革情况时,陈氏就把当时议定刑律诸人的家世、学术、乡里环境作为考证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崔宏、崔浩、胡方回、高允、游雅之等参与当时议律之人家世、学术传承以及他们在此次议律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等问题进行详细考察,最后得出“拓跋部落入主中原,初期议定刑律诸人多为中原之士族,其家世所传之律学乃汉代之旧,与南朝之颛守晋律者大异也”③ 的结论。再如,在考证北魏刑律制度的河西文化因子时,陈寅恪同样采取从参与修律之人的家族以及地域为切入点,参与太和第二次刑律改革者主要为李冲与源怀二人,李冲是当时太和新律总主持,他与河西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源怀虽非汉族,然其家子孙汉化特深,当时人都把他当作汉人。另外,李冲与源怀二人之间又有着紧密的学术渊源关系,他们都保持有河西文化的遗风。通过论证,最后得出“太和第二次定律河西因子居显着地位,观此可知矣”④ 的确论。
地域因素是影响当时文化及刑律的另一重要因素,通过对河西文化之考察,陈寅恪同样发前人之所未发,提出影响甚巨之论点。正如陈其泰所讲:“河陇地区在文化上于南北朝据有突出的地位,由于中原长期战乱,许多世家大族避居河陇,把文化带到偏僻之区,中原连年大乱的结果,遂造成原先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与僻居一隅的河陇地区文化学术上新的巨大反差,造成朝廷太学与世家大族教育上新的巨大反差,以往落后的河陇地区反而成为保存传统文化的重要先进地区。这是陈寅洛钩稽史乘、深入探析而勘破的千余年学者未予注意的历史隐秘。”
⑤陈寅恪上述认识更对爬梳中国刑律制度发展沿革帮助甚巨,因为它颠覆了那种落后民族地区的刑律制度必然落后的传统观点。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复杂的社会因素或许能够促使曾经一度落后的地区成为保存传统文化的重地,该地区的刑律制度因吸收先进文化之影响而获得重大发展,进而成为影响其他原来曾相对先进地区的刑律制度。即便放在今天,这一观点依然不失其科学性。
由于陈氏在地域与民族文化之关系上具有如此灼见,诸多论点今天依然被人信服。如,陈寅恪在概括元魏刑律时说:“总之,元魏刑律实综汇中原士族仅传之汉学及永嘉乱后河西流寓儒者所保持或发展之汉魏晋文化,并加以江左所承西晋以来之律学,此诚可谓集当日之大成者。”⑥ 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何以能够在刑律制度上取得如此成就,陈寅恪给出了一个较为精准的答案。其中,中原地区因战乱导致文化衰落,自不必再论。此外,他这样分析:“就南朝承用之晋律论之,大体似较汉律为进化,然江左士大夫不屑研求刑律,故其学无大发展。且汉律之学自亦有精湛之义旨,为江东所坠失者,而河西区域所保存汉以来之学术,别自发展,与北魏初期中原所遗留者亦稍有不同,故北魏前后定律能综合比较,取精用宏,所以成此伟业者,实有其广收博取之功,并非偶然也。”⑦ 通过陈寅恪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用民族先进与否来断定刑律制度之优劣的做法是偏谬的,它不可能正确认识到刑律制度的本质,更不用说对其做出客观评价了。
综上所述,陈寅恪之所以能在隋唐刑律制度研究中取得如此深邃的论点与识见,主要因为他采用了民族文化视野,紧扣了种族、地域等影响政治与法律文明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一做法,也为我们法律史学研究者提供了重大的启发意义,即研究者只有切中引领学术发展大势的关键因子,才能为最终发前人之所未发提供可能。三“预流”之志与科学之法:法律史学研究的新范式。。
陈寅恪治学,在佛教文献、西北史地、魏晋南北朝史以及隋唐史研究诸领域建树颇多,至今为人所仰视。由于关注的焦点不同,陈寅恪在中国法制史研究领域并没有像同时代的杨鸿烈、瞿同祖等法律名家那样留下影响深远的皇皇专题巨着,同时,他也没有针对法制史研究提出引起轰动的论点,但我们通过考量其深邃之治学动机、科学之史观以及独辟蹊径的理论与方法,依然可以获得诸多指引法律史学健康发展的宝贵财富。
首先,所阐“预流”之志及学者应重视“关系民族盛衰学术兴废”之学等对法律史学极具启发意义。
早在1930年,陈寅恪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①表面看来,陈氏似乎是专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所序时的有感而发,充其量是对我国文献资料之大量流失所衍生出的一种愤慨之情。然实则未必,此论饱含着者更深层次的殷切爱国之意。
设若我们把这句话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去考察,其深意便愈加凸显。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一些学者便在我国西南、西北边疆地区大肆搜集、掠夺我国史地资料,以期达到歪曲历史,伪造史实,为其侵略政策张目之目的。面临国外学者的险恶用心,部分中国学者却浑然不觉,反而欣然接受从国外获取我国传统文化之事实。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学者为配合日本军国主义武力侵略中国之目的,他们大肆渲染“中国本部”理论,妄图在世界范围内制造舆论,把我国的边疆地区分离出去。
诸多中国学者不仅没能窥察出他们的险恶用心,反而以使用“中国本部”等概念、理论为向西方学习的标志。有鉴于此,部分有使命感的学者倡导“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理论,同时把治学的兴趣点转移到中国古史研究领域与搜集整理我国古代文献等,他们此举的目的除有揭露日本及国外反动学者的阴谋外,还有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良苦用心。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论稿》便是在这种社会与学术背景下问世的。结合陈寅恪所阐发的“预流”论点,我们便很自然得出如下观点,即陈寅恪把包括隋唐政治、法律制度在内的那些“关系民族盛衰学术兴废”②之学视为当时的学术新潮流。换言之,陈寅恪所阐发的“预流”论点便暗含了知识分子治学必需心系民族兴亡的旨归。关于衡量学者所治之学是否能起到维系民族兴亡的作用,陈寅恪又论述了“民族盛衰”与“学术兴废”两大标尺。
陈氏的上述论点给法律史学带来的启发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法律史学者之治学必须有维系民族兴旺与繁盛的初衷;法律史学者治学要根据时代之需选择“关系民族盛衰学术兴废”之学等。上述论点对我们解决当下法律史学界的研究范式之争———“法学的法律史学”与“史学的法律史学”、考据与法理阐发何者为胜等棘手问题均有重要意义。按照陈氏的观点,若法律史学者的治学旨趣、选题范围符合上述标准,治学路径的迥异并不能作为决定学术高下的依据。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因具有保护与宣扬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之责,当然与历史事实之叙述及阐释共具“民族盛衰”与“学术兴废”之功用,很大程度上驳斥了那些把法律古籍整理与研究等视为细致末流的荒谬论点。
其次,科学的研究视角是推进法律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陈寅恪在考证隋唐刑律制度之时,并没有运用什么新的材料,为什么能够得出大大超越同时代其他学者的“隋唐刑律源出三途”之论点,很大程度上即在于其运用了民族文化视野。陈氏此举,对法律史学者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即研究视野之更新能够从习见的材料中发现新价值,得出新结论。关于文化视角研究学术的重要性,学界多有论述。如有学者所说:“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等于向丰富的史学遗产投射去新的光束,能使我们探寻到更多的宝藏。即令对一些早已熟知的名着,我们转换一个视角,结合文化走向、社会思潮来考察,也能发现以往被掩盖的真价值。”
①还有学者认为:“在制度史与思想史研究衰落的同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日益兴旺的现象,说明寻找两者的结合点,用文化来说明法律的研究方法,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②由此看来,陈氏用文化视野研究法律史学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当前,用文化视角研究法律史学已经被广大法律史学者所重视,法律文化史的繁荣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尽管我们还不能断定陈寅恪是中国法律文化史学科的首倡者,但其对中国法律文化史学发展所做的贡献的确毋庸低估。更为关键的是,陈寅恪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在法律史学研究过程中,我们不应固守门户之见或拘囿于传统的研究范式,对新视角的尝试应是法律史学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因素。
再次,法律史学研究应“兼擅严密考证与义理阐释”③及采取跨学科研究。
陈寅恪“兼擅严密考证与义理阐释”的治学特点不仅在当时具有先进性,直至今日,这种方法仍具重要的价值。譬如,陈寅恪擅严密考证与义理阐释相结合的治学路径,就为我们解决当前中国法律史学领域的史观派与考据派所出现的问题具有启发意义。自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史学诞生以后,法律史学界就形成上述两大学派。史观派重在义理的阐发而忽略史料的考证;考据派则重在发掘史料的真伪而缺少对义理的阐发。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西学术交流的加深,一些崇尚义理阐发的学者更是以西方的新学理为标的来套用中国的法律史学研究,表现出对史料考证的不屑甚至对中国传统法学之存在产生怀疑;而考证学派则依然坚守对史料真实的发掘与考辨,尽管也有学者对义理有所阐发,但这一学派研究的主旨依然是对法律历史真实的还原与表述。陈寅恪的研究成果是在确保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对义理有所阐发,我们从中既能感知历史上的法律状况究竟如何,又能获得法律历史给我们当今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与借鉴作用。
陈寅恪的多学科知识互用的研究路径颇具特色。《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就涵盖了中国古史学、宗教学、社会学、民族学、法学、考古学、语言文字学等诸多领域。在编撰体例上,既吸收中国传统旧史之体裁的精华,“分别事类,序次先后,约略参酌唐史志及通典、唐会要诸书,而稍为增省分合”④,又对域外史学的体例有所借鉴,“微仿天竺佛教释经论之例,首章备至详悉,后章则多所阙略”⑤ ;在治学方法上,除了继承中国传统的训诂考据学方法与宋代以降的史学方法外,还对域外史学、语言学、诠释学等学科的方法有所借鉴,形成了“一种既打通汉宋,又融合中西的史学研究方法”⑥。上述种种,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成为学界传颂经典的关键所在。
从陈寅恪及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备受学界称誉这一事实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一位学者、一部学术着述甚或一门学科能否被社会所接纳与认可,首先取决于此学者、着述及该学科所关切的问题是否与时代主题密切相关,但凡能够真正提升人们认识与裨益社会发展的学术,绝不会为自己的生存及前途担忧,因受众认识拘囿而产生的误解定然不会成为永久的真理,一旦人们重新认识了它的价值,其必然重获发展的良机;在当下法律史学暂遇低谷的时期,法律史学者所做的工作并非仅局限于口头上的呼喊,尽管极力阐发法律史学社会功能以厘定大众认识非常必要,但拿出学术与时代有益的作品显得更为重要。基于此,对法律史学者而言,凸显问题意识、根据时代变迁及时调适研究内容、探索新的视野与方法,以及运用民众所容易接纳的叙事语言等,都显得十分必要与迫切,而上述努力,必须以有益于学术与社会发展为基点。与此相反,那种唯西学为上的学风与文风,尽管也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中国法律史学这门学科而言,带来更多的则是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