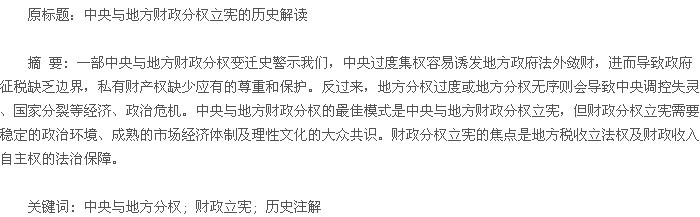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议题,它不仅决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也与权力制约、民主机制完善及公民权利保障有紧密联系。我国分税制改革基本确立了央地间财政分权的总体框架,加强了中央政府权威,催醒了地方政府利益,开启了央地财政关系的历史性嬗变,但仍存在央地间事权与财权财力、支出责任配置失衡、地方滥用举债权等诸多问题。宪法学界在着手研究财政立宪、税权及预算权控制等问题的同时,也开始从分权制衡、基本权利保障与地方自治权构建等宪法学视角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进行研讨。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宪法学界对财政分权的研究过分倚重西方学界提出的“财政联邦主义”分析范式诠释和论证我国财政分权,很少有学者从中国自身财政分权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几千年惊心动魄的中国财政史也许能够为我们目前的财政分权提供诸多启迪。
一、古代中国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更迭史
秦朝汲取夏商周封建藩国的教训,废除封国进贡的分权制,向郡县制下的统收统支转变,经过多项加强中央集权的财政措施,终于实现“利归天子”、地方“自天子以外,无尺寸之权”的财政集权。从此,开启了中央财政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交替历史运动。
两汉时期郡国并行出于对秦朝中央集权的否定;隋朝及唐朝的前期中央集权是对魏晋南北朝分权的否定; 唐朝后期出现的两税三分法是对唐朝前期中央财政过度集权的否定,唐朝最终被藩镇割据所颠覆; 宋朝又汲取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将财政大权重新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财政困难诱使地方官员在税赋法度之外收刮民财,宋朝由此走向覆灭; 元朝在汉地创造性地设立行省制度,将财政权以行省为单位进行分割,地方没有任何财权,最终王朝再次被地方官员的横征暴敛所摧毁; 明朝依然沿用中央集权体制,“侧面收受”本意是简化中央财政管理,但却导致地方政府疲于奔命; 清朝前期承袭明朝财政集权体制,但后期迫于国际国内军事、政治及经济压力,不得不推行“就地筹响”、“就地筹款”分权财政体制,最终导致两千多年君主专制体制寿终正寝。
通过考证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流变史可以发现,古代中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基本特点如下:
一是中央财政集权是主流。我国财政方面的集权形成于秦汉时期,在隋唐有所发展,至宋明清时期达到顶点,而民国时期则有所下降( P214) 。中央集权的财政关系并非呈现一种直线发展态势。相反,地方财政分权始终相伴和牵制着中央集权的发展,进而呈现一种“螺旋式”的曲折发展脉络。君主专制时代的财政严格意义上说属于“家计财政”或“官房财政”,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君主专制及少数权贵的统治利益,而不是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财政。这是历代王朝都十分关注中央财政集权、削弱地方财权及忽视民生的根本原因,也完全符合古代“所有者国家”的财政汲取品格( P53) 。
二是中央财政过度集权导致地方财政困难,地方官员在税赋制度以外横征暴敛。田赋一直占据中国古代社会税赋收入的绝对比例,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朝前期。清朝后期,厘金、洋税等新设税种的比重才有所上升。在靠天吃饭的农业文明,天赋的征收比例极其有限。这是汉朝仅仅按“什伍而税一”“三十而税一”计征的重要原因。国家对天赋的征收既然非常有限,有限的财源无奈只有优先保障中央政府。可是,这无疑导致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比如在宋朝,地方政府通过征收附加税、科敷、抑配、脏罚等非法课征汲取法外收入( P177) 。元朝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分配比例是 7∶ 3,这一分成还是以行省为单位的划分,而行省实际上属于活动的中央政府,因此剩余的 30% 实际上也被中央掌控。地方路府州县几乎没有任何财权。
明朝的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分成比例为 7∶ 3,有时高达8∶ 2。在中央政府强制改变中央与地方收入分配比例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则趁机在法令之外索财于当地居民( P138) 。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王朝的统治根基,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及朝代更迭完全印证了上述推论。
三是中央政府将税赋征收上解作为考核监控地方官员的主要指标,地方官员因此较少顾及黎民百姓的需求。秦朝建立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财政审计法律,汉朝将这一制度发展与完善,秦汉通过上计制度、设置监御史、刺史等官职加强对地方财政的监察,并将财政监察结果与考核各级官吏的政绩结合起来。此后历朝历代对地方官员的监管内容大同小异。唐朝对地方官员除了按照“四善”“二十七最”考核外,对于州县地方官员还针对土地、人口等进行考核; 宋朝除了沿袭唐制进行考核以外,还特别强调治安稳定、社会安全及劝农课桑,最大限度征税是其中重要的考核指标; 明朝对地方官员更是实行严格的“考满”或“考成”制度,税粮征收完成情况是其中重要内容; 清朝的考核也与明朝大同小异( P221 -222) 。在君主专制时代,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及品鉴机制有效保证了地方官员忠实履行中央政府的律令、政策、指示和命令等,防止地方官员的恣意妄为行为。但由于君主专制时期考核结果与官员升迁有直接关联,如同当代的 GDP 考核一样,税赋征缴、上解是考量地方官员政绩的核心指标,这无疑会导致地方治理行为的偏差、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和非法横征暴敛行为丛生。
四是法外征税税捐惯例化使私人财产权始终处于模糊状态,国家因此缺乏现代化发展的资本原始积累。
这一问题在宋朝就非常棘手。宋朝商品经济极其发达。但宋朝的财政设计却一直维持由上端统筹支配而不在下端固定私人财产权,又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以致抽税时“既以捐折钱,又以钱折卖,以捐较钱,钱倍于捐; 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 P519) 。整个古代社会缺乏诺兹和汤姆斯所说“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的社会共识,导致农业积累很难达到有序转入工商业的原始积累。由此看来,税捐制度缺乏底线思维导致私人财产权缺乏应有的尊重和保护。这应当是中国社会没有及时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嬗变的重要原因,也是传统中国财政汲取能力整体受限的根本原因。由“财政危机”到“统治合法性危机”所引起的王朝更迭也在情理之中。
五是历朝历代均采取对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采取财政扶持的政策和措施。汉朝设置大司农掌管收支使用分配权,大司农根据各地的收支情况在全国范围内调剂余缺。如《后汉书·百官志》记载: “大司农,边郡主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补足”; 宋朝设运转使一职专门负责中央财政的征收、地方财政的监管及协调所辖州县财政收支余缺的调度; 明朝财政体制中的“对拨”就是将田赋拨送其他府州县或拨送军卫所作军饷; 清朝地方之间进行的余缺调剂称为“协款”( P45、79、124、141) 。
古代社会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上述特征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原因,首先,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是君主专制国家治理的最佳体制。在多数情况下,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相互促进,趋向统一。君主专制是君主一个人的自由,这种体制要求高度中央集权的“家计财政”与其相适应。其次,在农业文明中,地主租佃制经济有利于中央集权。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长期“采用中央集权制的根本原因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制的特点”( P151) 。农业文明需要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应对江河泛滥等大型自然灾害的侵害。再次,朝廷对地方官员设立的监察制度使地方官吏的分庭抗礼和作大格局很难得逞。儒家“大一统”的思想文化及各民族的文化共融也对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形成有一定影响。总之,农业文明的经济形态、历史悠久的文化共同性及元朝以后相对固定的省级行政区划是我国古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主要成因。
二、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嬗变
在北洋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在清朝后期“洋务运动”的刺激下,单纯依靠土地和农业的社会财富创造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在此期间获得长足发展。有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探讨比较开放,争议也相当激烈。有关单一制与联邦制的选择、国税与地税的划分、财政支出责任划分、地方自治权及其地方自治事项、省级地方政府的法律地位以及如何划分省区界限等都被广泛讨论( P9) 。其中,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以县自治为核心的自治体系建设以及省级政府兼具地方自治团体和国家行政区域的双重地位等观点至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是,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制度最终都未被中国社会接纳。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立宪方面,1912 年,北洋政府公布了《国家税与地方税法草案》和《国家费目与地方费目暂行标准案》。《法案》规定国税包括天赋、盐税、关税、厘金等,地方税包括田赋附加税、商税及一些杂捐等,同时还规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等。由于这一草案将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与支出责任列入国家范围之内,而当时中央权威不足,导致上述规定并未真正实施。1923 年 10 月,北洋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又称《贿选宪法》。宪法第五章为国权章,它划分了中央与省的权限,并对双方的权力进行了列举。宪法第 12 章为地方制度,规定了省税与县税的划分由省议会决定等,但由于其政权更迭也没有实施。
1928 年,国民政府进行国税与地方税划分,将盐税、关税、内地税、常关税、厘金及国有事业收入等划归国家收入,将田赋、契税、当税、地方路政收入、电政收入等划归地方。并对新设税种及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范围进行划分。1935 年,国民政府颁布的《财政收支系统法》规定,各级政府非依法律规定,并经其立法机关议决,不得发行公债或为一年以上的长期赊欠; 省、市、县政府对于外资的借赊,应先经中央政府许可。
1947 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第 10章把中央与地方财政权限分为四类。中央财政及国税、国税与省税、县税的划分等由中央立法并执行,属于第一类; 第三类是由省立法并执行,或交由县执行的事项,省财政及省税、省债等属于第三类; 第四类是由县立法并执行的事项,县债属于第四类。第 10 章还特别规定,如果有未列举的事项发生,其事务有全国一致性质者属于中央,有全省一致性质者属于省,有一县的性质者属于县。遇有争议时,由立法院解决之。宪法第 11 章专门规定了省、县地方自治制度。这部宪法最终由于国民党的溃败而没有在大陆实施。
事实上,国民政府的其他财政法律制度在实施中也存在很大问题。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执行方面,中央财政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一直或明或暗存在。
国民政府时期每次国税与地税划分的主要动因都是加强中央财政收入,缓解财政困难。从 1937 年到 1945年,国民政府的财政均处于赤字状态,赤字占支出的比重平均高达 70% 以上( P102) 。中央的经济集权或放权都是实现其政治集权的目的,地方则采取各种举措应付中央的财政集权。地方政府截留中央专款和地方解款、公开抵制国税与地税划分、谋求财政独立以及利用国税与地税划分向中央政府转嫁支出责任等。
“民国政府虽然首开国地税划分的先河,但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各自在划分国地税的目的和行为方面的自利性,当国地税划分与自身利益相违背时,则国地税划分就不能正常实施下去。这是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一个缩影。”( P183) 。
总体来看,民国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缺乏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的政治环境。要科学、理性、均衡地界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中央政府的权威必须首先保证,否则,再先进的国家立法也仅是美丽的“装饰”。二是要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充分发育和逐步完善。《中华民国宪法》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作了较为详细的界分,但其根本就不适合当时的国情。这一例证充分说明没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充分发育,就不能清晰地凝练出适合国情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模式,更奢谈在宪法层面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作出科学而明晰界定。三是财政分权立宪必须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然而,民国时期的财政分权立宪仅仅属于当时社会精英之间的权力斗争工具而已。
三、新中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迁
新中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1978 年以前为“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 1980 年 - 1993年,国家相继推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及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管理体制;从 1994 年至今,为全面推行分税制改革时期。
“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的根本特征是高度集权,它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特有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地方政府、各企事业单位及公民个体都是这个“企业型国家”的零部件,它完全按照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优先顺位统筹安排经济和财政资源( P3)。“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虽然在短期内能够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其弊端也非常明显。其全盘用行政计划和命令管理社会经济的方式严重扼杀了广大公民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长期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社会要求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的呼声越来越高。财政管理体制也开始“放权让利”,以便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1980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决定从 1980 年起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具体内容包括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范围; 以 1979 年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数为基础,经过适当调整以后,计算确定各省地方财政收支的包干基数,一定五年不变; 民族自治地区( 包括青海、云南) 也按“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执行,但给予较多照顾。
1984 年,为了配合企业“利改税”制度,中央与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也相应地改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并继续实行一定五年不变的方式。1988年,在全国大包干思潮影响下,为了提高地方政府组织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地方实行财政包干办法的决定》,从当年开始全面推行“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包干”“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包干”“上解额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及“定额补助”等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
“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打破了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开放了地方政府的管理社会经济的积极性,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促进了地方及区域经济发展。它对中国经济的引领和促进作用也被学者形象地称为“行为联邦制”( P4) 。但“财政包干制”也有致命的弊端。首先,财力过于分散,中央财力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宏观调控能力削弱。其次,“财政包干制”助长了地方政府兴办企业的热情及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最后,财政包干制缺乏规范化治理机制,支出基数不合理等( P38) 。
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3 年又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写入根本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极大地促进了分税制改革的推进。1993 年12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并于 1994 年全面推行。分税制的原则和主要内容如下: 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政府的支出范围; 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建立中央与地方两套征税体系; 科学划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 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对于省以下财政体制,1994 年的财政改革方案没有涉及,而是授权各省、自治区以及计划单列市根据国务院决定制定所属市、县的财政管理体制。
1995 年国务院发布《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在不触动地方既得利益的情况下,通过增量改革的方式,由中央财政安排一部分资金,按照规范的办法,解决地方财政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并体现向民族地区倾斜的政策。
后来,中央政府又多次对转移支付方法、所得税分享比例及出口退税负担比例进行调整,以平衡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
1994 年分税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在提高中央财政宏观调控能力的基础上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有序促进地方政府竞争。1994 年分税制改革的历史功绩如下: 一是基本确立了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的公共财政总体框架; 二是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的设立成为中央与地方财政规范化的标志,基本明确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级财政职能,中央政府的权威得以确立和巩固,地方政府逐渐具备了责权利相统一的独立财政主体( P105 -109) 。
当然,我国的分税制改革仍有很多值得完善的空间。各级政府的职能划分尚不清晰; 支出责任层层下移导致地方财政困难; 转移支付制度尚不规范; 省以下财政分权有待推进以及财政分权的规范层面太低,缺乏宪法、法律保障等( P111、113) ; 财政分权模式不清、财政立法权、财政收益权、财政征收权及财政支出权配置不合理,地区间财政不平衡程度过高,协调与争议解决机制缺乏以及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等( P140 -154) ; 地方负债是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首要问题; 权力失衡是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主要症结; 权力失控是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主要风险等( P159 -177) 。
总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的主体地位必须充分关注、尊重和保障。国家应当在宪法、法律上规范和保障地方政府的趋利避害行为。目前,我国分税制的首要弊端是地方政府层级设立不合理。比如,“市管县”体制是否走到尽头,乡镇是继续保留还是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其次,缺乏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财权、财力及支出责任的宪法、法律界定,由此导致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投机行为和预算软约束。
这是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四、集权与分权的历史启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
通过回顾历朝历代君主专制制度、民国政府时期及新中国成立以来 60 多年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点重要历史启迪:
其一,中央财政过度集权容易诱使地方政府及地方官员在法律制度以外横征暴敛,使国家征税权及公民私有财产权都将处于模糊状态。历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前期往往呈现中央集权稳固,后期则容易出现地方势力凸显的共性,地方势力凸显成为王朝颠覆的重要原因之一。出现上述情况的根源在于中央财政过度集权,导致地方政府财权较小,不能满足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同时它也成为地方官员趁机在法律制度以外加税及横征暴敛的“口实”。加上税赋上解是古代中央对地方官吏考核的主要指标,这就进一步促使了地方官吏的法外征税行为。这一历史“顽疾”在当代中国又得以“重生”。当前地方政府对预算外资金的偏爱、在《预算法》与《担保法》等法律禁令以外的恣意举债行为以及片面依靠土地财政的行为都是上述“顽疾”的情景再现。由此看来,中央财政集权过度可能威胁中央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在金融债券市场发达的当代,地方政府的无序举债是新型“横征暴敛”行为。
其二,地方分权过度或地方分权无序也同样导致国家分裂、调控失灵等政治、经济危机。无论是农业文明还是工业文明,地方政府的主体地位都应被中央政府尊重和保护; 否则,如果无视地方政府的主体地位,极有可能被地方官员所利用,进而作为突破中央政府各种法令的借口。这种情况一旦蔓延,中央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不过,地方政府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中的地位、功能不尽相同。农业文明的地方政府更多关注的是大江大河的集中治理; 而工业文明的地方政府则更多关注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这一区分肇始于二者之间社会财富的创造方式不同。当代世界基于对地方政府市场公共服务竞争的重视,更加强调地方居民的民主自治。
地方政府的主体地位固然需要尊重和保护,但如果地方分权过度或地方分权无序,也同样可能导致政治、经济危机,甚至将国家引入灾难。在中国历史上,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清末地方的“就地筹饷”,北洋军阀时期及国民党统治时期各地通过各种方式对国税的截留以及对地方财政独立的谋求,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收支划分、分级包干”及“财政包干制”等历史阶段,都是地方分权过度的历史考证。
其三,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宪法化是根治中央过度集权或地方过度分权的唯一路径,但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入宪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及理性文化的大众共识。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虽然在宪法层面予以规范,但由于缺乏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缺乏市场经济体制的充分发育,因而出现财政分权立法超越社会现实的局面。目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并逐步完善的背景下,国内外实务界和学者从多个视角对我国分税制改革现状进行注解、研讨和评判,这是财政分权理性共识形成的必要前提,该项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周密设计、合理把握、渐进推行至关重要。
其四,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的核心———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法治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完善地方税系,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等等。这显然在传递一个信号———强化地方财政自主权是我国财政分权立宪的总向度。笔者认为,强化地方财政自主权,首先要在宪法上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在这方面我们要借鉴历史经验,国家立法应当赋予地方政府享有一定的税率调整权、税收减免权及地方税的征收权等。
其五,要在宪法上赋予地方稳定的财政收入。由于中央政府集中税收立法权,要解决事权与财权相匹配问题,必须通过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解决。即在明确中央与地方事权及支出责任划分的基础上,通过完善而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来保障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决定》提出要“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要实现这一改革蓝图,还应在宪法上明确地方政府的税收收益分配权及均等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最后,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争议解决机制应当纳入法治轨道。我国属于单一制国家,没有采取两院制,即专门为地方政府提供影响中央立法的制度平台。
由于缺乏制度性的中央与地方争议机制,目前的中央与地方争议通过各种“驻京办事处”协调中央政府官员解决,这成为腐败产生的肥沃“土壤”。为此,我国可以借鉴域外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解决机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设立专门协调及解决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机构———“地方事务委员会”或称为“政府间财政关系委员会”。由其来负责审查、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解决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争议。
参 考 文 献
[1]朱红琼.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及其变迁史[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2]葛克昌. 国家学与国家法[M]. 台北: 月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
[3]包伟民. 宋代地方财政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黄仁宇.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M]. 北京: 三联书店,2006.
[5]胡如雷. 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M]. 北京: 三联书店,1979.
[6]杨荫溥. 民国财政史[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7]周刚志. 论“财政国家”的宪法类型及其中国模式[J]. 法学评论,2012,(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