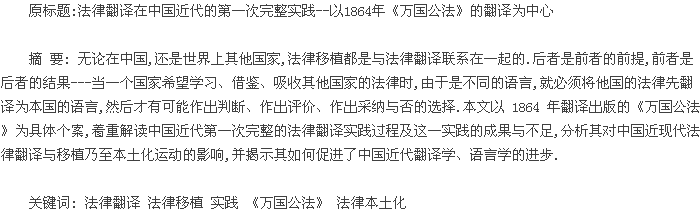
法律翻译的重要性,各个国家的学术界都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近代西方早期的莱布尼茨( Leib-niz,1646 - 1716) 、孟德斯鸠( Montesquieu,1689 - 1755) ,现代早期的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1864- 1920) 、威格摩尔 ( John H. Wigmore,1863 - 1943) ,当代比较法学家达维德 ( Rene David,1906 -1990) 、茨威格特( ( Konrad Zweigert,1911 - 1996) 、大木雅夫( 1931 - ) 等,都有深切的体会: 从事跨民族、跨文化的法律研究,首先遇到的就是另一种甚至多种语言的障碍问题.
当然,在同一个民族( 如拉丁民族) 、同一个区域( 如欧洲大陆、亚洲大陆等) 的法律交流中,这种障碍还不是太显明,如 1864 年中国翻译出版《万国公法》时,日本学术界因为有中国文化的基础和汉语的底子,所以就将《万国公法》未加翻译、原封不动地在日本翻印出版.但是,在远隔千山万水的西方和东方之间,在两种差异比较大的文化之间,上述障碍就显得非常突出了.尤其是 1840 年前后,当已经发展了 200 余年的英、法等国的法律进入有着 2000 余年专制集权政治与法律文化传统的中国,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中开始其东渐( 法律移植) 过程时,这种重要性愈发显得突出.
关于上述过程的学术探讨与研究,我国学术界近年来已经开始在做,如北京大学的李贵连,西北政法大学的王健,清华大学的高鸿钧、许章润,中国政法大学的米健、高祥、郑永流,华中科技大学的俞江以及华东政法大学的王立民、李秀清和屈文生等学者,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一批阶段性的成果.〔1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 1864 年翻译的第一本西方法学着作《万国公法》为线索,着重解读中国近代第一次完整的法律翻译实践过程及这一实践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与若干不足,分析其对中国近现代翻译事业尤其是法律翻译与法律移植乃至法律本土化运动的影响,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万国公法》翻译的知识背景
应该说,在中国,实际上早在《万国公法》之前,就开始了对外国法律的翻译和移植引进工作.〔2 〕1815 至 1823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1782 - 1834) 出版了中国近代最早的英汉字典(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三卷,六大册,中文译为"字典"、"五车韵府"、"英汉字典") ,译介了部分英文法律名词,如 a creditor( 债主) 、crime( 罪) 、power( 权) 、penal laws( 刑法) 、place of execution( 法场) 、a witness( 证人) 、punishment( 刑罚) 等.1815 年,英国传教士米怜( William Milne,1785 -1822) 在马六甲创办了已知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该刊曾连载麦都思( W. H. Medhurst,1796 -1857) 撰写的《地理便童略传》( Geographical Catechism) 文章,对英美两国政治和司法制度做介绍,从英文翻译至中文不少法律词语,保存至今的有犯罪( to com-mit a crime) 、证据( evidence) 等词.〔3 〕1833 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 K. F. A. Gutzlaff,1803 - 1851) 在广东创办了第一份内地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Eastern and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 ,在这份刊物中,办刊者通过创设一些中文法律名词"自主之理"( "法治") 、〔4 〕"国会"、"公司"、"公班衙"、"公会"、"平等"、"立法"、"内阁大学士"、"臬司"( 法官) 、"关税"、"海关"、"公会尚书"、"首领"、"律例"、"副审良民"( 陪审员) 、"批判士"( 陪审员)〔5 〕等,将英语世界中的一些专有法律名词翻译成为中文,介绍进入了中国法学界.
1840 年鸦片战争的爆发,给中国知识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大家急于了解庞大的中华文明帝国,为何给远道而来的野蛮小国打败的原因,从而涌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林则徐( 1785 -1850) 、魏源( 1794 -1857) 、冯桂芬( 1809 -1874) 等.他们或者组织属员幕僚,〔6 〕或在自己的着作中,从事着法律翻译和法律移植的工作.比如,魏源在所着的《海国图志》一书中,就将英文 Par-liament( 议会) 一词或者按照音译译为"巴厘满"、"巴厘满衙门",或者如上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作者一样,按照意译译为"国会";〔7 〕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一书中,继承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译法,将 House of Commons( 平民院、下院) 一词译为"乡绅房",将 House of Lords( 贵族院、上院) 一词译为"爵房",〔8 〕等等.〔9 〕1847、1848 年,前述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编印出版了《英汉字典》(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也将立法( legislate) 、国法( law,constitution) 、合法( legitimate,legal) 、章程( constitution) 等词引入了中国.
除此之外,在揭示西法东渐的历史及西方法律词语汉译的最早形态时,还应注意到近代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一介质.屈文生注意到,早期中英条约的各式翻译问题中,马儒翰( John Robert Morrison,1814 - 1843) 、罗伯聃( Robert Thom,1807 - 1846) 、郭实腊等译者,对一些较为重要的英文法律词语,也作了尝试性汉译,比如"身家"( persons and property,今译"人身与财产") 、consular officer/consul( 管事官/管事) 、duties and other dues( 货税、钞饷/船钞各费) 、laws and regulations( 法) 、heirs and succes-sors( 世袭主位者) 、imprison( 强留) 、demand and obtain redress( 讨求伸理) 、tariff( 则例) 、privileges orimmunities( 恩) 、criminals and offenders( 罪犯) 、be in confinement( 被禁 / 被拿监禁) 、commit crimes or of-fenses( 犯法) 、piracy( 洋盗) 、illegal traffic( 走私偷漏) 、property real or personal( 家资、产业) 、smuggling( 偷漏税饷) 、seize and confiscate( 抄取入官) 以及 trial and punishment( 按法处治) 等十数例.〔10〕所有上述前人的劳动,都为《万国公法》的翻译提供了经验,进行了学术积累,尤其是如"公司"、"国会"、"立法"和"平等"等汉字的出现,意义尤为重大.正是在此基础上,1863 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 William A. P. Matin,1827 -1916) 开始了翻译《万国公法》的艰巨劳动.该书译自美国着名国际法学家亨利·惠顿( Henry Wheaton,1785 - 1848) 1836 年出版的《国际法原理》(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丁韪良翻译此书后,于 1864 年( 同治三年) 冬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资助下,由其所创办的教会学校崇实馆刊印发行.第一版印 300 本,发给各个省,供地方使用.〔11〕从《万国公法》凡例中得知,当时参加翻译的除丁韪良之外,还有江宁何师孟、通州李大文、大兴张炜和定海曹景荣等四人.〔12〕由于《万国公法》翻译的是惠顿的整本书( 略有删节〔13〕) ,因此,其中大量的是关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尊重各国主权、国与国之间平等往来、遵守国际公约和双边条约) 、各项制度( 大使、领事、外交豁免、管辖、条约、交战、中立) 、各种观念( 如中国只是世界之一部分、自然法、民主共和、法治和三权分立等) 的释义和讲解,〔14〕但是也涉及了许多名词术语的翻译,而这些翻译,有的是成功的,为后世学界所沿用; 有的则是失败的,为后世学者所抛弃.只是《万国公法》因为有了前人劳动的铺垫,加之译者的法律翻译实践又比较用心,所以其成功的范例要更多一些.
二、《万国公法》翻译的学术成就
《万国公法》一书在法律翻译方面的成功,主要表现在它所翻译、定型成中文的名词,许多后来都得到了学界的认可.这些名词有 public law( 公法) ,international law( 万国公法,后译为"国际法")〔16〕,self - government / autonomy( 自治) ,independence / liberty( 自主) ,sovereignty( 主权) ,natural law( 性法,后译为"自然法") ,private right( 私权) ,courts/Law House/tribunals ( 法院) ,administer( 管辖) ,people( 人民) ,right( 权利) ,duty( 义务) ,dispute/conflict( 争端) ,consul( 领事) ,neutral( 中立) ,constitution( 章程) ,national law/constitution( 国法,constitution 一词后来一般译为"宪法")〔17〕,rights of the people( 人民之权利) ,election( 选举) ,politics( 政治) ,judicial( 司法) ,congress/Parliament ( 国会) ,interest( 利益) ,prize tribunals( 战利法庭,后译为"捕获法庭") ,supreme court( 上法院,后译为"最高法院") ,fullpower( 全权) ,等等.其中,性法、主权、法院、权利等词的翻译,尤为有价值.
"性法",译自惠顿的 natural law 一词.该词现在通译为"自然法".虽然,对现代中国人来说,"性法"一词的译法有点怪,但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这种译法是抓住了自然法的本质.因为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性"一词,表达的是人的本性,人的原始的最初的本原.中国古代的经典都阐述过这一点.如《论语·阳货》曰: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孟子·告子》曰: "生之为性"; 《荀子·正名》进一步展开曰: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因此,作为一种上帝赋予的、与人的出生一起产生的、管束人世间一切生灵的法律,用"性法"是一个很好的译法,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掌握了自然法的真谛.
正因为如此,当《万国公法》一书传入日本之后,"性法"一词也流传开来.包括法国巴黎大学教授保阿索那特( G. E. Boissonade,1825 -1910) 在日本的讲稿《自然法》和《法哲学》,日本人将其译成日文时,用的也都是"性法"的名称.正是在"性法"的译文基础上,日本学者进一步将其译成"自然法",这不仅对中国近代国际法,而且对中国近代法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主权",译自惠顿书中的 sovereignty 一词.它是指近代民族独立国家具有的对本国人民的统治权,对本国财产( 领土、领海与在其之上的各种资源) 的支配权,以及在对外事务中独立自主行使自己的权利、表达自己的意愿、不受他国干涉地进行各种活动的权力.
在中世纪西欧,主权主要是指封建领主对自己领地的统治权.中世纪后期,法国等国的君主合并各封建领主的权力并取而代之,形成一种独立于罗马教皇之外的最高统治权力,这被近代资产阶级学者称为"主权".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欧各国的胜利,无论是法、美等共和国,还是英、德等君主立宪国,都以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诠解国家对内对外的权力,从而形成了近代国家的主权概念.惠顿在《万国公法》一书中使用的即是这种意义上的主权概念.而作为一个美国人,丁韪良对"主权"的内涵有着透彻的理解,因此,在翻译 sovereignty 一词时,没有用"皇权",也没有用"帝权",而是用了"主权".而"主权"一词,不仅其概念对中国人来说是新鲜的,而且其内涵对中国人来说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在中国当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种种欺凌中,主权得不到伸张是一个最为痛苦的事情) .因此,"主权"一词,不仅成为中国近现代国际法中的基本概念,也传入日本,为日本国际法学界沿用至今.
"法院",译自惠顿书中的 courts,Law House,tribunals 等词.应该说,丁韪良创造出"法院"一词,其贡献是巨大的.在他之前的 20 多年前,林则徐在《各国律例》、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还将英国的Law House( 法院) 译成"律好司".这里,"律"是意译,"好司"是音译.可见,林则徐〔18〕和魏源当时尚没有找到一个与西方的 court、tribunals 和 Law House 相对应的合适的汉字用语.在翻译英文中的 thehigh court of chancery( 占色利,今译"大法官法院") 、court of common pleas( 甘文布列,今译"高等民事法院") 、court of assize and nisi prius( 阿西士庵尼西布来阿士,今译"巡回审判法院") 和 court of generalquarter session of the peace( 依尼拉尔戈达些孙阿付厘比士,今译"季度法院") 等词时,林则徐和魏源等则用相近的音译处理.〔19〕这些译法,不要说在现在几乎无人能看得懂,就是在当时,估计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而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时,他既没有选择汉语"议会"( court 的本义是指中世纪日耳曼人的民众大会) ,没有选择"委员会",也没有选择如同后来日本人选择的汉字"裁判所",而是选择了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汉文"法院".丁韪良使用"法院"一词,虽然有点突兀,因为在他之前,不仅是上述林则徐和魏源,就是马礼逊、郭实腊、麦都思、冯桂芬等人,也都没有能够创造出这个词,在翻译 court、Law House 和 tribunals 时,即使意译,一般也都以"衙门"〔20〕来对应.而"法院"一词的使用,则带有相当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即由于"法院"一词比较恰当地表达了审判官、控诉人、当事人以及证人在一起适用法律、解决纠纷、寻求公正这样一个场所的意思,比较符合中国人的将法律适用的方方面面汇集在一起的"法的庭院"这样一种逻辑思维,因而后来很快就为中国人接受,并沿用至今.
"权利"一词的使用,也是《万国公法》的重大贡献.在丁韪良翻译此书之前,如林则徐聘请美国传教士伯驾( Peter Parker) 和自己的属员袁德辉翻译瑞士国际法学家瓦特尔的《万国法》〔21〕一书时,凡是涉及 right 的地方,或者译为"例",或者译为"道理",或者译为"应当的"等.从来没有译为"权"或"权利"的.过了七年,在麦都思所编印出版的《英汉字典》中,对 right 一词的翻译,也仍然沿用了之前马礼逊、伯驾、袁德辉等人的译法,即译为"应"、"应当的"、"道理"和"正理"等.将 right 一词译为"权利",是丁韪良的伟大贡献.在《万国公法》一书中,涉及 right 一词,丁韪良译为"权"和"权利"的地方很多.如"私权"、"自护之权"、"捕鱼之权""掌物之权"、"立约之权"等,以及"人民权利"、"领事权利"、"分位权利"〔22〕等.
而且对权利的表述,与现代的法律意识没有任何不同.如在讲述主权国家对内进行统治、实施国家管理时,首要的一项职能就是对"人民"的各项"权利"进行规定.〔23〕讲到"私权"时,就是指"人民"对"植物"( 不动产) 、"动物"( 动产) 所拥有的"权利",等等.〔24〕日本有些学者认为,汉字"权利"一词,最早是由近代日本学界发明的,是日本在受荷兰文化的影响而接受"兰学"〔25〕时,从荷兰语"regt"一词翻译而来.〔26〕而我国学者李贵连、郭道晖等人认为,"权利"一词是由中国首先使用,是丁韪良在翻译《万国公法》时,创造出来以对应 right 一词的.〔27〕《万国公法》出版后,由日本学术界引入日本,予以翻刻.随后,汉字"权利"一词才开始被使用,并逐步流行,最终一直延续至今.我认为李贵连、郭道晖等人的观点值得重视.
三、《万国公法》翻译中的探索与不足
当然,《万国公法》一书中也有许多翻译不太成功的用语,比如,关于 republic,丁韪良只译为"民主之国",而不是译为"共和国",虽然"共和"的意思包括在"民主之国"里面,但毕竟没能够为后人所沿用.又如,将 president 一词译为"首领",或直接音译为"伯里玺天德"( 音译在《万国公法》中极少出现,后面将详述此点) ,〔28〕也是不成功的,后人没有接着使用.此外,丁韪良仍然将 law( 法律) 译为"律法"或"法度律例",将 judge( 法官) 译为"法师"或"公师",public jurist( 公法学家) 译为"公师",将 fed-eration( 联邦) 译为"合邦",将 diet( 议会) 和 congress( 国会) 译为"总会",将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众议院) 译为"下房",将 Senate( 参议院) 译为"上房",将 judgment( 审判、裁判) 译为"判断",将 con-stitution( 宪法) 译为"国法",将 debt( 债务) 译为"债欠",等等.这些译法,后来没有一个能够为人们所认同、采纳,也未能流传下来.
这当中,有些词的译法虽然很有创见,表达了丁韪良对英译汉之事业的探索,但未能得到后世的认可.如 judgment 和 constitution 的汉译,特别是将 constitution 译为"国法",后来《万国公法》传入日本之后,该译法还完全为日本学术界所接受,在日本宪法学者早期写作、出版的宪法( constitution) 着作中,书名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法学"、"国法学原理"等等.但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后,这种译法就被废止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当然,丁韪良对英译汉的探索,还体现在他对有些法律名词的翻译,直接借用了自然界的称呼,如将 real property( 不动产) 一词译为"植物",将 personal property( 动产) 一词译为"动物",形象是比较形象,也能把握其性质,即前者是不能搬动的财产,后者是可以搬动的财产,但毕竟不是很贴切,与中文里面自然界的"植物"和"动物"的称谓混淆了,所以未能长久,之后就不为学界所沿用.此外,丁韪良将 contract( 契约,合同) 一词,全部译为"契据",将 Supreme Court of theUnited States,Supreme Court(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一词,全部译为"上法院",虽然也不错,也看得懂,但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思维,传统的用词方法,传统的法律意识.
丁韪良的翻译受到中国文化影响,以致其部分译文出现了变异或失真.比如他将"a legislativepower / a judicial power( 立法权力机关 / 司法权力机关) "一概译为"君".而这一简单化处理,无疑使当时的读者误以为君主权力不受限制有正当化的理由,进而具备国际法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他将"law"和"positive law"一概译为"律法",则可能会使法的科学分类不易被人们察觉; 将"citizen"译为"庶民"、"obligations"译为"名分"也属这一范畴.〔29〕丁韪良对许多法律名词的翻译失败,也与当时的整个学术环境相联系.在 19 世纪 90 年代之前,西方宪政、民商法、刑法、诉讼法等领域中的一些关键用语,基本上都还没有定型,各种译法都有.如president( 总统) 一词,有翻译为"首领"的,有译为"勃列西领"的,有译为"伯理喜顿"的,也有译为"伯里玺天德"的.Senate( 参议院) 一词,有译为"上房"的,有译"西业"的,也有译为"爵房"的.Politics( 政治、政治学) 一词,有译为"衙门之事"的,有译为"国政之事"的.lawyer( 律师) 一词,有译为"法师"的,有译为"讼师"的,有译为"律士"的,也有译为"公师"的.juror ( 陪审员) 一词,有译为"副审良民"的,有译为"批判士"的.Government House( 总督官邸) 一词,有译为"内阁"的,有译为"甘文好司"的.Court( 法院) 一词,有译为"衙门"的,有译为"察院"的,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从 19 世纪初叶至 90 年代,西方法律名词的翻译,在中国已经悄然兴起,有一批中外知识分子,充满了热诚和激情在从事着这项既艰苦又神圣的事业,但绝大多数的法律翻译还处在探索阶段,还没有能够予以定型.中国近代法律翻译的大规模兴起,以及许多法律名词翻译的成熟与定型,是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中叶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戊戌变法",以及 1901 年沈家本奉命进行修律变法、大量翻译国外法律着作和法典之时,〔30〕由梁启超、严复、沈家本、伍廷芳、董康,当时一批来华的法律专家如冈田朝太郎、织田万、志田钾太郎、松冈义正,以及如熊元楷、熊元翰和熊元襄等一批早期留学日本的法科学生完成的.但无疑的是,丁韪良对《万国公法》一书的翻译,为这一法律翻译事业乃至中国整个近代翻译运动提供了经验和基础.
四、《万国公法》翻译的翻译学、语言学成果
以上,我们只是从法和法学专业( 重点是国际法) 的角度,对《万国公法》的翻译成就与不足等进行了分析和解读.下面,我们将从翻译学和语言学角度,对《万国公法》的翻译事业,再进行一番论述.
中国对外来学术文献的翻译,很早就开始了.且不说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文献对译交流,就是秦汉帝国时代,我们在对周边国家的交流过程中,也广泛翻译、吸纳了其他国家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当然,大规模地翻译外国的经典文献,是从公元 7 世纪唐代玄藏( 公元 602 -664,也称"玄奘") 在政府的支持下,全面系统地翻译西域佛教文献开始的.就法和法学领域而言,由于中华帝国的律( 后来包括了"例"等形式) 和律学,早已自成体系,且非常完备,因此直至清末,对外国法和法学的吸收、移植的动力不足,尚未出现大规模的翻译外来法和法学文献的活动.在法和法学领域,比较系统的将外来的学术文献包括法典翻译成中文,是从 19 世纪初叶开始的.
上述马礼逊、郭实腊、麦都思等西方传教士,以及中国近代第一批睁眼望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如林则徐、魏源、冯桂芬和徐继畲等,就是在翻译外国法和法学文献方面做了最初的工作.然而,如前面我们所分析的,早期的翻译,且不说其还带有零碎、分散、粗陋等特点,就是从翻译学角度,也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大量使用多音节语素来翻译西方的法律与制度、机构、职位,如用"甘文好司"来对译 House ofCommons( 平民院、下院) ,甚至用"依尼拉尔戈达些孙阿付厘比士"这样的汉字堆砌之名词来对译court of general quarter session of the peace( "季度法院") ,等等,如果不附原文、译者不逐字予以解释的话,人们基本上是无法阅读的,也根本看不懂,实际上也失去了翻译的意义和价值.
而《万国公法》在吸收前人翻译学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大胆的创新,在使译文准确、通俗、便于理解方面,作出了许多探索.一方面,《万国公法》除了人名、地名之外,基本上不再采用"多音节语素"的音译方法,已经全部采用意译的方法( 当然,还保留了个别的音译处理方法,如上述对 president 一词的处理,丁韪良时将其意译为"首领",时又直接音译为"伯里玺天德".与前人不同的是,他在个别处理这种音译名词时,一般都加上了引号) .对各项制度、法律、各种机构等的翻译,《万国公法》基本上都是通过意译方法处理的,以便将这个名词、术语的内涵尽量发掘出来,让读者一目了然.〔31〕比如,除上述主权、领事、法院、国法、权利之外,还有公法、本源、大旨、公义、天性、邦国、自治、自主、自立、自护、国、君、民、私权、外敌、盟约、国债、国土、民产、被害者、合盟、会盟、连横、制法、制律、立约、改革、变通、推让、政事、管制、妨害、立君、举官、内事、外事、外人、入籍、契据、使臣、国使、商船、民船、接待、海外、航海、征服、稽察、稽查、局外、捕拿、管辖、审案、海盗、争讼、兴讼、断案、人民、纳税、礼拜、章程、宣战、公战、交战、贸易、俘虏、停兵、禁物、敌货、封港、争端等等用语,都是丁韪良在翻译《万国公法》时创造出来,并一直流传下来的现代汉语意译术语.
另一方面,丁韪良通过偏正结构、动宾结构、联合结构、单音节词、前缀和后缀等语言学手法,使一个个单列的中文词能够组成一个词素,来对应翻译英语中的各个术语,并大体表达其内在涵义.比如丁韪良创造的"国会"一词,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的,它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名词,译者就将其用来对应翻译英国的 Parliament 和美国的 congress,这个译法为后人所吸收采纳.又如,丁韪良用前缀方法创造了"半主"一词,对译 semi - sovereign( 现译为"半主权的") ,来表达半主权的国家( 丁韪良已经将 sover-eign 一词创造性地、准确地译为"主权"了) .这里,虽然"半主"这个词后来没有传下来,被淘汰了,但其前缀"半"对后人在翻译英语前缀 semi - 时非常有参考价值.〔32〕再如,丁韪良用一批偏正结构的名词如"上房"、"下房"、"民间大会"等,后缀结构名词"总会"、"公使会"等,来对译英文 Upper House( 上议院) 、Lower House( 下议院) 、People's Assembly( 人民议会) 、congress( 国会) 等,虽然如上所述,并不十分贴切、准确,但丁韪良所作出的努力非常可贵,为后世英译汉的工作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
此外,丁韪良生活的时代,在中国还是一片文言文的世界,尚没有白话文的生存空间.但可贵的是,丁韪良在《万国公法》中不仅延续了文言文的中国士大夫( 知识) 传统,而且大量采用了白话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来对译英文法学着作的句法.如他在翻译第一卷第一章"释义明源"中第二节"出于天性"时,用了以下语言: "公法之学,创于荷兰人名虎哥( Hugo Grotius,现译为格老秀斯,1583 - 1645)者.虎哥与门人,论公法曾分为二种.世人若无国君,若无王法,天然同居,究其来往相待之理,应当如何? 此乃公法之一种,名为'性法'也.夫诸国之往来,与众人同理,将此性法所定人人相待之分,以明各国交际之义,此乃第二种也."〔33〕又如,丁韪良在翻译第二卷第二章"论制定律法之权"中第十五节"审断海盗之例"时,用的是如下语句: "犯公法之案有数种,各国刑权所能及者,如海盗等类是也.按公师所论,凡船只在海上未领自主之国所颁凭照,或于二国交战之时,兼领其凭照而私行抢掳,则为海盗也.""凡兵船领牌,既注明专攻某国,若乘机抢掳他国,则其班主、班人虽属越权而行,犹不可以海盗处之.盖赐牌者必任领牌者之责,若有托牌妄行,则审断其事专归赐牌之国.""若遇二国交战而兼领其牌照,藉以强掳者,则明为海盗无疑.……至于海盗,则为万国之仇敌,有能捕之、诛之者,自万国所同愿.故各国兵船在海上皆可捕拿,携至疆内,发交己之法院审断."〔34〕上述两段话语,虽然还有文言文的传统,如"者"、"也"、"之"等,译词也有局限,如"刑权"( 刑法) 、"公师"( 法学家) 、"班主"( 舰长、船长) 、"班人"( 船员) 等,和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法律用语还有差距,但已经是非常流畅的白话文了,稍作思考,即可领会.因此,从语言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万国公法》的翻译,译者为了要准确地对应解读近代英语( 是白话文,不是文言文) 的形式和内容,在遣词用句以及语言风格方面,比起同时代的中国人( 如魏源、徐继畲、王韬、郑观应,包括后来的谭嗣同等人) 自己写的着作,要更加容易阅读和理解.《万国公法》的翻译所取得的这一成果,是中国近代语言学发展史上文体改革的前奏,可视为晚清文体解放的先锋,它广泛吸收并再现了西方法律语言的字汇资源和文法结构,推动了近代书面语白话文的形成和发展.毕竟,20 世纪早期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之白话文改革浪潮,比《万国公法》的面世要晚几十年.而我们以前在论述中国白话文运动时,关注比较多的是文学作品,而对《万国公法》这样的法学译着,则相对较少,这是我们今后所应当重视的.当然,这是超出本文的另外一个话题,作者将会作另外的专题研究.
《万国公法》所取得的上述翻译学、语言学成就,与译者丁韪良的经历和努力是分不开的.丁韪良是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在大学( 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新阿尔巴尔神学院) 期间接受了比较系统和正规的近代教育和知识训练,对近代英语文献有很好的阅读和理解能力,获得了两个学士学位.1850 年到中国后,在宁波传教近十年,不仅精通中国官话,也学会了宁波方言; 不仅读完了四书、五经等中国古代文献,而且还参与将《圣经》译为宁波方言的工作; 不仅自己撰写中文着作如《天道溯源》等,还创办了两所私塾,每所招收 20 名左右的中国学生( 男生) .更为可贵的是,为了对法律特别是国际法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和理解,他还专程回到美国,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进修国际法.这些经历,使丁韪良能够用半文半白、以白为主的中国话,流畅、通顺地译述惠顿的《万国公法》一书,从而为中国近代翻译学、语言学和法学的发展事业,作出独特的贡献.
五、《万国公法》翻译出版的社会历史意义
《万国公法》一书的翻译出版,已经过去了 150 年,认真总结、深刻反思近代中国历史上这第一次系统、完整的法律翻译、法律移植和法律本土化的实践,我们有许多感悟和启迪.
首先,《万国公法》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本被翻译引进的西方法学着作,其翻译出版,开了中国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的先河,对中国近代以后法和法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35〕通过《万国公法》一书的翻译,中国人尤其是其先进的知识分子,不仅获得了尊重国家主权、各国平等相处、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的知识和观念,也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使长期生活在封建专制下的中国人民及其知识分子开始了解西方世界,懂得诸如民主、平等、自由、权利、法治、选举等重要政治和法律制度、观念,接触到了西方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法治的观念.它强调法律是人民公意的体现,而非仅仅是君主的意志; 主张法律必须是一种良法,必须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和人类的理性;强调每一个国民包括国君都必须遵守法律,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进行活动; 等等.而这一切,大不同于中国古代法家所倡导的"法治",对当时的国人而言,是一种全新的知识和观念.它对后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戊戌变法",以及孙中山等人发动"辛亥革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为近代中国发生的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奠定了政治法律基础.
其次,《万国公法》一书的翻译,作为中国近代法律翻译和法律移植的第一次完整的实践活动,在中国近代法律翻译史上也占据着一个重要的地位.它是 19 世纪中国法律翻译方面的一个高峰,也是中国近代法律翻译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在《万国公法》之前,外国传教士以及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法律翻译的实践活动,但都是分散的、零碎的,马礼逊、麦都思等人的活动,是在编写英汉字典的过程中,涉及到了部分法律的字、词; 郭实腊、魏源、冯桂芬等人,是在其宣传西方各个先进国家的历史、地理、经济、科技、教育、军事、政治和文化时,涉及到了法律的一些制度、原则和用语; 林则徐虽然组织了伯驾、袁德辉等人,翻译了瓦特尔的《万国法》,但没有完成,只留下了一些片断.而《万国公法》则是一次系统完整的法律翻译,它承前启后,既吸收了之前法律翻译的成果,又创造了一批汉字法律术语,从而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律翻译的基础.
再次,《万国公法》的翻译实践,是法律翻译、法律移植和法律本土化互动发展规律的一次生动体现.从历史上来看,任何跨民族、跨国家、跨区域的文化翻译活动,都会必然地带来文化移植与文化本土化的实践,上述中国唐代玄藏系统翻译印度佛教经典的活动,带来了佛教在中国的移植与本土化;明清交替时期,一些耶稣会教士如利玛窦( Matteo Ricci,1552 -1610) ,将耶稣会教义文献译为中文,传授给中国的信徒,带来了耶稣教在中国的移植与本土化的实践;〔37〕而近代中国翻译西方法律的活动,则引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法律移植和本土化的浪潮.从林则徐,到丁韪良,到沈家本,到 20 世纪 10 -20年代法治派的法律翻译活动,导致了法律移植和法律本土化的最大成果: 民国政府"六法全书"的制定颁布以及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最终形成.因此,法律翻译,必然带来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是法律发展的规律之一,法律翻译是前提,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是结果,而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又是法律翻译的目标和价值体现,这种互动关系,推动了世界各国法律的进步与发展.而《万国公法》的翻译,是法律发展规律的最经典、最辉煌的实践.
最后,学术创新、理论勇气,历来都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法律发展的原动力和灵魂.但是,我们以前的认识或论述,讲到学术创新和理论勇气,往往局限于传承与发展本国或本民族内部的经验与成果比较多,对引进国外或域外的经验和成果比较少,甚至不认为这种引进、借鉴他国之学术经验、理论成果是一种理论创新.而《万国公法》一书的翻译,使我们的认识有了很大改变,甚至可以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即法律翻译( 当然也包括了其他理论或学术的翻译) 也可以带来学术和理论的创新,给接受翻译成果的国家或民族带来翻天覆地的革命性变化.《万国公法》引进西方政治与法律观念,导致了中国近代政治与法律领域的巨大革命.将在西方诞生的政治与法律观念,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罪刑法定等引入中国,成为指导中国近代法和法学变革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更加令人鼓舞的是,这样的创新还在继续.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学者伯尔曼( Harold J. Berman,1918 - 2007) 的《法律与宗教》一书被译为中文,引入中国政治与法律界.伯尔曼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法治建设的重要命题,即"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一命题,最早只是在学术界受到追捧,为广大法科学子所认可.然而,经过 20 余年的宣传、阐释,现在这一命题已经得到了中国官方的认同.2012 年 6 月 18 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首席大法官在主题报告中曾明确要求,全国所有的法官都必须将"法治信仰"作为审判工作的准绳,以确保法律的权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信仰这一命题,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法治传统中的重要一环,传入中国知识界,经过努力,又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审判工作的准则,这中间需要强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这一事例告诉我们,法律翻译可以作为理论创新的一种模式,为中国法和法学的继续进步和完善,作出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