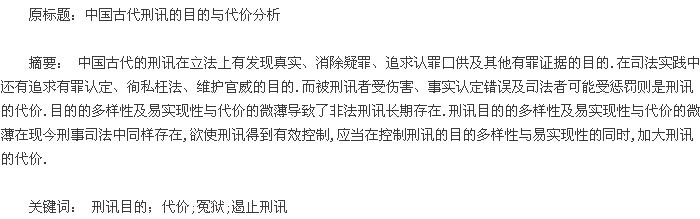
中国古代刑讯的研究成果可谓洋洋大观。其中关于刑讯合法化及常被滥用的成因是古代刑讯研究的热点之一。许多成果从不同角度探讨刑讯何以长期盛行。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侦查技术落后导致刑讯适用,如王立民指出: “中国古代的刑事侦查技术有限,如果不用刑讯,一些疑难案件的犯罪线索和证据就难于发现”.也有学者主张刑讯的存在与国家体制有关。如姜小川认为,刑讯制度缘于专制集权的国家体制……刑讯制度的废除是以专制制度的废除为前提的。由于当下人们将刑讯逼供连称,故而认为中国古代口供裁判主义模式是刑讯广泛适用的主要原因成为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如闫召华认为,中国古代司法重视以供词为核心的言词证据。在审讯时,虽然法官运用五听,也可能取得与检验供词,但趋利避害毕竟是人的本性,受审人通常情况下不会主动陈述不利于己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只能动用刑具,逼迫受审人吐供,刑讯的产生遂成为必然。
这些研究当然是有益的,但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如以刑事侦查技术落后作为古代刑讯适用的理由,但今天的刑侦技术比古代有了巨大进步,可刑讯依然存在。而主张刑讯与专制政体有关,但我国当下已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可刑讯亦未绝迹。至于重视口供是刑讯适用的理由,这一观点难以解释的问题是,无论中国古代还是现在社会,法律都有不依被告人口供定罪的规定,但刑讯在古代与现代都存在,换言之,重视口供是刑讯适用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由此可见,上述研究尚未解决刑讯存在的基本原因问题,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无论是刑讯立法还是司法,大都是理性行为。而探究理性行为,离不开对行为人心理状态的经济分析。所谓经济分析,即成本收益分析。具体到刑讯的立法与实践,刑讯的收益表现为刑讯目的的实现,而刑讯成本则表现为刑讯代价的付出。研究中国古代刑讯的立法与实践,我们应充分考虑到刑讯的目的与代价的特征。这一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刑讯的制度与实践状况。而对当下刑事司法中刑讯的目的与代价进行分析,亦有利于我们找到遏止刑讯的手段。
一、中国古代刑讯的目的
虽然刑讯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理论及司法实践,都未对刑讯的目的展开论述。但刑讯作为一项制度,必然有其目的。据笔者对古代刑讯立法的考察,刑讯目的是通过其实施条件体现出来的。实践中的刑讯目的与立法的目的既有一致的地方,亦有不同之处。
(一)立法者心目中刑讯的目的
立法者心目中刑讯的目的是指立法者在设计刑讯制度时对刑讯价值的期许,即立法者希望实施刑讯能获得的案件审理结果。在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立法者在设定刑讯制度时对其价值追求并不完全相同,大体有发现真实、消除疑罪、追求认罪口供与追求有罪证据四种。
1.发现真实
发现真实是中国古代证据法的主要目的,也是古代诉讼的重要目的之一。刑讯作为法定的取证手段之一,发现真实是其应有之义。尽管刑讯早在战国中晚期就已出现,但囿于资料,我们无法判断当时的刑讯的目的。秦律关于刑讯是这样规定的:
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治(笞)谅(掠)而得人请(情)为上; (笞)谅(掠)为下,有恐为败。
从条文内容来看, “笞掠”与“能以书从迹其言”都是“得人情”的手段。所谓得人情,即发现真实。可见秦代刑讯的目的是发现真实。汉代及魏晋时立法未见刑讯条件的规定,因此对刑讯的目的亦无从探讨。不过,汉承秦制,且汉魏时代司法实践中的刑讯确有在案件存疑时实施的,因此可以推测汉魏时期的刑讯亦以发现真实为主要目的。北魏时期,法律关于刑讯条件的规定开始详细。 《魏书·刑罚志》所载《狱官令》要求: “察狱先备五听,尽求情之意,验诸证信,事多疑似,犹不首实,加以拷掠。”北魏律中发现真实的先行手段是五听,其次是验诸证信,只有当两者皆不能发现真实时,才可以实施拷讯。可见,刑讯同样是发现真实的手段,且与秦代一样都不是发现真实的首选。唐律继承了北魏的刑讯制度,要求司法者在审理案件时应当做到:
先察其情,审其辞理,反覆案状,参验是非……事不明辨,未能断决,立案,取见在长官同判,依法拷讯。
“事不明辨,未能断决”时才可以刑讯,刑讯当然是为了明辨事实。因此,发现真实亦是唐代刑讯的主要目的。
从秦汉直到唐代法律关于刑讯的实施条件可以看出,上述时期的刑讯都以发现真实为目的,也都是各自法律规定的发现真实手段中的最后选择。
2.消除疑罪
所谓消除疑罪,是指当司法者面对疑罪,通过适用刑讯,使案件不以疑罪结案。通常情况下,消除疑罪的目的与发现真实的目的是统一的。只要案件真实发现,疑罪自然可以消除。但当真实无法发现时,通过实施刑讯亦可以使案件获得一个确定的处理结果,此即单纯的消除疑罪。消除疑罪的目的在立法与实践中均有体现,不过不体现在刑讯条件方面,而是体现在刑讯的结果方面。唐律规定对被告人拷满不承,则应取保放之;然后反拷告人,若再不承,则对原告亦取保放之。我们发现,原告指控被告犯罪,因证据不足且被告不认罪无法确定其罪。① 接着刑讯原告,但原告亦不承认是诬告。此时被告是否有罪不能确定,原告是否诬告同样不能确定,属典型疑罪。但刑讯却可以使案件有一个确定的处理结果,而不是以疑罪结案。可见法律关于刑讯的规定带有明显的投机色彩:在罪之有无不能确定时,先刑讯被告人,若被告人不能熬刑而吐实,事实即可查明;被告人若能熬过刑讯,就取保释放。然后再刑讯原告,如原告不能熬刑而承认诬告,则案件事实同样可以查明。如原告亦不认诬告,对其亦可取保释放。至于刑讯为何能成为疑罪的处理手段,笔者认为这主要同中国古代司法的对抗性结构有关。中国古代司法虽有强烈的职权主义倾向,但在形式上却表现为原告与被告的对抗。当原告指控被告之罪审理到罪之有无不能确定时,司法者若以罪疑从无为由直接释放被告,原告一般不会接受,司法者自己亦会觉得无法向原告交代,特别是原告本身就是受害人或受害人亲属时尤其如此;若持罪疑从有态度,又无法说服被告。
此时依法刑讯被告,被告若始终不承认,司法者便可向原告表明审理手段已经用尽,释放被告原告亦无话可说。但被告又会不服,觉得自己未被证明有罪,却要受到刑讯。司法者于是再刑讯原告(原告是受害人的不反拷),若原告承认自己诬告,则事实亦可查清;若原告不承认诬告,司法者对被告亦有交代。这样原被告双方都不能指责司法者袒护对方,案件便以将双方取保释放的方式解决。唐律中刑讯的两种目的之间并不冲突,而是可以兼容的。即在案件存疑时实施刑讯,若能发现真实,自然是最佳结果,疑罪也因此得以消除。若不能发现真实,但依据刑讯结果,疑罪在制度上亦可消除。这两个目的存在先后关系,发现真实是首要目的,消除疑罪是次要目的。②
3.追求认罪口供
从刑讯的条件看,在案件存疑时刑讯被告人,其目的乃是为了发现真实及消除疑罪,而在案件罪证已明时再刑讯被告人则是为了获取认罪口供。据笔者目力所及,中国古代法律中最早规定在案件明白时才可以实施刑讯的是南北朝时陈朝法律。陈律中刑讯条件是“赃验显然而不款”, ( 《隋书·刑法志》 )与同时期北魏律规定的“事多疑似”有所不同。刑讯要获得被告的“款”,即承认犯罪,而非北魏律的“首实”,即陈述实情。由此可见,陈律中刑讯的目的与北魏律的刑讯目的大异其趣。它以追求被告人认罪口供为目的,而不是发现真实。陈律中刑讯目的未能被隋唐时期的法律继承。 《宋刑统》基本上沿袭唐律,因此律文中刑讯条件与唐律相同,不过在一些诏令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出宋代刑讯条件与目的的变化。
宋太祖时诏: “令诸州获盗,非状验明白,未得掠治。” ( 《宋史·刑法一》 )而太宗时又诏令“自今系囚,如证佐明白而捍拒不伏,合讯掠者,集官属同讯问之,勿令胥吏拷决。” ( 《文献通考·刑考五》 )被告人在证佐明白的情况下还捍拒不伏,法律允许对其刑讯,刑讯的目的自然是迫使其伏罪。可见宋代的刑讯不再以发现真实为目的,而是以追求被告人的认罪口供为目的,与南朝陈的法律具有相同旨趣。元代的刑讯条件是“事情疑似,赃仗已明,而隐讳不招,依法拷问。”( 《元典章·刑部·鞫囚以理推寻》 )这一条件从逻辑上讲是冲突的, “赃仗已明”应为肯定有罪,而非“事情疑似”.元代法律的这一矛盾源于其对唐宋律与诏令不加分析的吸收。本来,唐宋律文强调的刑讯条件都是事情疑似,但宋代诏令的条件则是证佐明白。在宋代,诏令具有高于律文的效力,因此宋代刑讯的制度条件应是“证佐明白”,元代法律将两者杂糅到一起,就使得立法出现了矛盾。不过,元代刑讯要获得的是受讯人的招,而招在古代专指承认犯罪的口供,而非指吐实。总的看来,元代刑讯应是以获得被告人的认罪口供为目的。
明律继承了宋代诏令的精神,规定在被告人被控之罪审理到“赃仗证佐明白”时可以拷讯,《明会典》记载刑讯条件如下:
如各执一词,则唤原告被告干证人一同对问,观其颜色,察听情词,其词语抗厉、颜色不动者,事理必真;若转换支吾,则必理亏。略见真伪,然后用笞决勘;如又不服,然后用杖决勘。
明代刑讯是为了迫使被告人服罪,当然是司法者对案件真实已经确信,因此,刑讯的目的不是发现真实。清代律文规定:
“罪人赃仗证佐明白,不服招承。明立文案,依法拷讯。”沈之奇解释: “犯罪人赃仗证佐皆已明白,顽梗不服,不肯招承,若明立文案,依法拷讯,邂逅致死,勿论,此应勘而非故勘也。”
这是普通刑讯的实施条件,此外还有严厉刑讯的实施条件。清代条例规定:重大案件正犯,及干连有罪人犯,或证据已明,再三详究,不吐实情,或先已招认明白,后竟改供者,准夹讯外,其别项小事,概不许滥用夹棍。
总的来看,清代刑讯条件是案件事实已经清楚,但被告还不认罪。刑讯被告,自然是为了迫使其认罪。此种目的的刑讯在实践中并不罕见,蓝鼎元记载了他审理的一桩案件的刑讯使用就是如此。杜宗城之妾郭氏投水身死,验郭氏有被殴之伤,讯之杜宗城之幼女阿端,言因偷糖被宗城之妻林氏用棍殴,吏据阿端词在林氏房门后将小木棍携出,与郭氏所受伤相验符合。讯问林氏,坚不吐实。命刑之,林神色不变;拶其指:拷之二十亦不承。宗城乃谓妻曰:“事已难欺,实言可也。”林氏乃据实直言: “因郭氏偷糖四五斤,我怒以掌连批其左右颊,郭氏犹强辩,乃以木棍击其左手、右臀、两脚腕。”再问宗城及乡邻: “果非无别故,无别人殴乎?”皆曰: “并无别人殴打,林氏所言是实。”
本案司法者对林氏殴妾之死的认定既有郭氏之伤与行凶之木棍比对一致,又有林氏之女阿端的证词,可谓人证物证俱全。但林氏拒不认罪,司法者对其刑讯,林氏方承认系其所殴。本案刑讯时事实已很清楚,刑讯只不过是为了迫使林氏认罪。刑讯的条件与目的皆符合清代立法规定。
4.追求有罪证据
古代立法中刑讯的目的还有一种是获得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在中国古代,凡是法律允许对被告人刑讯,就同时允许对证人刑讯。在唐以前法律中,对被告人的刑讯是为了发现真实,对证人的刑讯同样是为了发现真实。因为在对证人刑讯时,被告之罪还未被查到赃状明白的程度。但到了宋以后的法律中,对被告人实施刑讯都必须赃状已明,那么,对证人的刑讯也应具备这一条件。宋元明的法律没有专门规定刑讯证人的条件。清律规定“犯罪人赃仗证佐皆已明白,干连之人相助匿非,则与不服招承之人俱当用刑”.沈之奇解释, “相助匿非,亦事须鞫问之一端也”.由于司法者已确信被告人有罪,那么刑讯证人无非是让其证明被告确实有罪。 《徐公谳词》记载:
刘隐贤自缢身死,其弟刘隐芳控是因与蒋又恒争坟界而于蒋家门口自缢,蒋则反诉刘隐贤死于自家,刘隐芳扛尸图赖,并引查尔顺为证。县审定刘隐芳图赖之罪。招解到府后,徐士林认为刘蒋两家相距二十余里,抬尸远行,岂无他人看见,而独一异乡之查尔顺于恰好撞遇?即其悬梁室内,扛移出门,妻子宁不悲号,邻佑何无知觉,现隐贤既无沉疴之疾,又无横逆之加,何至家中自缢。扛尸图赖之说诞而不经。刑讯查尔顺,始则茹刑狡展,及加严讯,则以昏夜错看为词,游移混供。遂否定了县审事实。
本案审理过程中,徐士林已经认定刘隐芳不可能扛尸图赖,但证人查尔顺称自己目睹刘隐芳扛尸在途。徐士林刑讯查尔顺,目的非常明确,意在迫使查尔顺承认自己系作伪证,亦即为了获得对被告人蒋又恒不利的证词。这与清律规定的干连之人相助匿非情形相符。
(二)实践中刑讯的目的
实践中的刑讯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与立法规定是一致的,但也有与立法冲突之处。与立法一致的部分不再赘述,与立法冲突的刑讯目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追求有罪认定
中国古代立法关于刑讯的目的虽有不同规定,但都没有将追求有罪认定作为刑讯的目的。虽说明清时期的刑讯有追求被告人认罪口供以及迫使证人作出有罪证词的目的,不过此时的刑讯只是为了完善有罪案件的证据体系,而不是将疑罪审理成有罪。但司法实践中的部分刑讯却具有这一目的。司法者在实施刑讯时,被告之罪还只属于疑罪状态,但司法者希望通过刑讯迫使被告人认罪并且收集到证明被告有罪的证据,此时刑讯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发现真实,而是为了对被告人作出有罪认定。 《后汉书·寒朗传》载,东汉寒朗在奏折中曾言:
臣见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恶大敌,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无后责。是以考一连十,考十连百。
这份奏折不仅表明拷讯追求有罪认定的目的广泛存在,而且还透露了司法者追求这一目的的原因---可无后责。司法者为何会觉得案件有罪认定可以免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即对于一件疑罪,认定无罪或认定有罪皆有可能出错。但认定有罪出错,充其量会被认定为办案失误;而认定无罪出错,复审者往往会认为原审者收受贿赂而纵放犯罪者,故司法者宁可失入亦不愿失出。这种观念在很早就成为司法者的保身哲学。西汉时期的治狱吏“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 《汉书·路温舒传》 ) 《旧唐书·刑法志》载,唐初实践中也出现“今失入则无辜,失出则便获大罪,所由吏皆深文”.另外,司法者倾向于将疑罪认定为有罪,还有邀功的考虑。对于疑难案件,查下去的结果可能出现无罪、有罪及依然未查清三种情形。未查清当然无功可言;查明被告无罪,功亦有限。因为在犯罪事实确已发生的情况下,查明被告无罪则表明真犯另有其人,案件还须继续审查。为此,司法者倾向于认定疑罪为有罪并且将这一目的贯穿于刑讯过程就是自然的选择。这种意识对司法者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内化为司法者实施刑讯时的潜意识,他们自己亦不觉得有何不妥。清人张自堂记载了他本人审理的一则案件,情形如下:
一僧控乡民占其坟地,呈白契一纸。余疑其契为伪,随令招出造契之人。僧不招,即令掌责,唤审别件。完一件,问一回,仍不招,又掌责一回,一连问完四宗,共计掌责五十,始则混认自造。令其照写不对,复谕动刑,急呼曰: “情愿退还不要!”
本案中司法者仅因契约为白契就疑其为伪,这是典型的有罪认定思路。沿着这一思路,当僧人不承认是伪契时,司法者便对其刑讯。刑讯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希望僧人承认契约是伪造的。
2.徇私枉法
所谓徇私枉法的目的,是指司法者在实施刑讯时的目的不仅与立法中刑讯目的不符合,而且与司法者本人内心自发的有罪认定倾向亦不符合。关于实践中刑讯的徇私枉法性, 《魏书·刑罚志》记载:
理官鞫囚,杖限五十。而有司欲免之则以细捶,欲陷之则先大杖。民多不胜而诬引,或绝命于杖下。
有司讯囚时有“欲免之”及“欲陷之”两种目的,这两种目的都与发现真实目的冲突,且司法者是明知而故犯,属典型的徇私枉法。以徇私枉法为目的的刑讯在历史上很早即已出现。 《史记·李斯列传》载:“赵高治斯、榜掠千余,斯不胜痛,自诬服。”李斯并无谋反之事,但赵高必欲迫其自诬有罪,又虑轻刑不能遂愿,故而榜掠千余。本案的刑讯完全是出于徇私枉法的目的。徇私是实施非法刑讯的目的,但其背后的动机则多种多样。司法者与受讯者的关系是重要因素:两者亲近,则会欲出其罪;两者有仇嫌,则可能陷其入罪。 《汉书·陈咸传》载:
咸为御史中丞,时中书令石显用事,咸颇言显短,显等恨之。时有朱云残杀不辜,有司举奏,未下。咸素善云,教令上书自讼。显知之,奏咸漏泄省中书,下狱掠治,髡为城旦。
本案中的陈咸受刑讯,是由于当权者石显因泄私忿而施报复。当然,司法者与当事人有亲仇关并不常见,因此亲疏恩仇很少成为司法者徇私的动机。大部分徇私枉法刑讯的动机在于图财,图财已得则会对行贿者轻刑纵放,而对他方当事人则可能重刑逼诬;图财不得则可能对被索财对象进行严刑拷打,以泄怒火。这种因图财而滥用刑讯的做法不仅在刑事诉讼中存在,在民事诉讼中亦较为常见, 《皇明条法事类纂》载:
刁民假证争产,贪赂无为者不辨真假,一概准受,往往提人问理,暗受财嘱,非法拷打,朦胧逼退,增追价银。
相比较因亲仇关系而实施的刑讯而言,以图财为目的的刑讯的实施主体更多是各级衙门的吏役。清人潘月山《未信篇》卷三《刑名上》载:
皂隶用刑,只讲银钱。得钱则散打平铺,声响而轻,皮破血出。虽至淋漓,易于平复,以伤不入骨气行血散故也。若不遂欲,使性乱打。不论臀腿,必至糜烂日久,或成废疾。也更有仇家贿官买责,又与行杖皂隶讲明,或令断筋或令殒命,讲过谢银多少。则板用缩头,加力毒打。只打一块,肉死血淤,动至立死。
相对于正式官员而言,这些直接实施刑讯的吏役合法收入极低,不足以养家糊口。他们更会利用诉讼来自肥,而在刑讯上予取予夺则是其徇私自肥的重要手段。
3.维护官威
在古代诉讼中,司法判决的权威性是与官员本身的权威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为了在诉讼当事人面前展现司法者的权威,对于一些不够驯服的当事人实施刑讯就成了重要手段。在清代山东孔府的诉讼档案中,有一起是孔府与周围农民的土地纠纷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司法官员曾四次对属于原告一方的不同当事人实施掌责,且并不是因为证据确实而当事人不肯承认而掌责,而是仅仅因为司法官认为当事人在法庭上出言不逊。值得注意的是,司法者还表明该案是上司发下来的案件,所以不便上来就施打骂。他本人审案从来就没有这么宽的。① 可见在一般案件中,通过刑讯体现官威应当是比较普遍的做法。
(三)刑讯目的多样且容易实现
前文研究标明,刑讯的目的共有七种之多,司法者审理案件的绝大部分目的都可以通过刑讯来实现。目的多样导致刑讯会受到司法者的青睐。但我们还应关注刑讯目的实现的难易程度。如适用刑讯很容易达到目的,则司法者适用刑讯的动机就较为强烈,如刑讯很难实现目的,那么,司法者也不会积极实施刑讯。
关于刑讯的目的实现的难易程度,胡兴东认为刑讯制度是人类司法制度中公认最不能达到目的的制度之一。笔者的疑问是,倘若刑讯达不到目的已是古今公认,何以古代社会刑讯的合法性从未间断,现代中国刑讯亦难以根绝?以笔者的理解,胡兴东仅是从发现真实的角度来判断刑讯目的不能达到。关于刑讯的这一目的,古人也认为刑讯确实不是良法,郑克就认为“恃拷掠者,乃无术也”.不过,就发现真实而言,刑讯也并非一无是处,司法实践中以刑讯发现真实的案例还是存在的。 《折狱龟鉴》载:
宋李南公尚书提点河北刑狱时,有班行犯罪下狱,按之不服,闭口不食百余日。狱吏不敢考讯,甚以为患,诉于宪使。南公曰: “吾能立使之食。”引出,问曰: “吾欲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终不食乎?”其人惧,即食,且服罪。盖彼善服气,以物塞鼻,则气结,故惧。
本案中李南公仅以非刑相威胁,刑讯尚未实施,被告人即认罪,事实得以发现。有罪之人因畏刑而认罪,亦是人情之一种,这是刑讯有可能发现真实的机理。古人之所以认为刑讯可发现真实,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机理。 《三国志·魏书·孙礼传》载孙礼之言代表了这一观点。
礼迁冀州牧。太傅司马宣王谓礼曰: “今清河、平原争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决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礼曰: “听者以先老为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如今所闻,虽皋陶犹将为难。若欲使必也无讼,当以烈祖初封平原时图决之。”
孙礼之所以认为听讼者以老者为正不可靠,原因就是老者不可加以榎楚。文中所指的老者仅是证人,而非当事人。连证人若不加刑讯,司法者都认为他们的证言不可信,那么对当事人更须用刑讯才可以迫使其吐真情。孙礼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实践中的司法者也觉得若受讯人的陈述若在刑讯前作出的,便不太可信。面对受讯人在刑讯后的陈述,即使内容与当初陈述一样,司法者也会觉得后者更可信。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的一则案例颇能说明这一现象:
高祖戏而伤婴,人有告高祖。高祖时为亭长,重坐伤人,告故不伤婴,婴证之。后狱覆,婴坐高祖系岁余,掠笞数百,终以是脱高祖。
本案在初审中夏侯婴证明刘邦没有故意伤害他,与被告人刘邦的陈述相符。复审时司法官员不信夏侯婴证言,关押证人一年有余,刑讯数百,但最终还是采信了同样的证言。
既然司法者普遍认为刑讯后的证人与当事人陈述更可信,说明他们倾向于相信刑讯能够发现真实。至于那些批评刑讯不利于发现真实的人,其观点并非否定刑讯本身,而是否定刑讯的滥用。
消除疑罪、追求被告人认罪口供等目的亦是不同时期诉讼中刑讯的追求。在中国古代的诉讼中,通过发现真实来消除疑罪是最理想的方式,但当真实无法发现时,依证据及依刑讯亦可消除疑罪。如《唐律·老幼不拷讯》条规定对特殊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以众证定罪,若证明被告有罪的证人不足三人,皆认定无罪。显然此时的无罪并非是查清无罪,而是将疑罪视为无罪。不过,以众证来消除疑罪,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当众证被分别贿赂而作出相反证言时,则无法消除疑罪。而众证的这一不足恰是刑讯的优势。被告人受刑讯后,或者承认犯罪指控,或者始终不认罪,对前者可认定其有罪,对后者则可认定无罪。实践中这两种情形都有案可稽,前者如秦代李斯被控谋反,审理时受“榜掠千余,自诬服”,被定有罪。后者如汉“故太尉杨彪被诬谋反,宠考讯如法,杨彪无他辞。满宠言于曹操,称彪罪不明,若施刑恐失人望,操遂释彪”. ( 《三国志·魏书·满宠传》 )我们认为,刑讯也许会使无罪者被认定有罪,亦会使有罪者逃脱法网,但一般不会有案件继续存疑的状况。
从消除疑罪的角度,刑讯比众证定罪更有优势。至于追求被告人的认罪口供,通常亦须通过刑讯获得。明清时期法律强调刑讯必须在证佐明白的情况下方可实施,这表明即使在赃仗证佐明白时有的被告人依然不愿意认罪。被告人不认罪,一方面是可能真的无罪,即证佐明白有可能不可靠。① 另一方面可能是被告人虽心中认罪,但口头不服,以图逃避制裁。对于被告不认罪,仅凭说服教育效果是很微弱的,为此刑讯便能派上用场。而且刑讯只要足够严厉,获得被告人认罪口供的可能性就非常大。至于刑讯证人以追求有罪证据,对案件作出有罪认定,甚至徇私枉法及体现官威,刑讯都能很容易达到目的。
二、中国古代刑讯的代价
(一)被刑讯人受到的伤害
刑讯无论是非法还是合法,都会给被刑讯人带来伤害,差别只在于非法刑讯伤害的程度可能更严重。有史可载出现严重伤害后果的刑讯大都属非法刑讯。如《后汉书·戴就列传》载,会稽人戴就作为证人“被幽囚考掠,烧鋘斧,使就挟于肘腋。以大针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堕落”.《新唐书·来俊臣传》载,酷吏来俊臣等“鞫囚不问轻重皆注醯于鼻,掘地为牢,或寝以匽溺,或绝其粮,囚至啮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终不得出”.汉代法律允许的刑讯方式只有“榜笞立”三种,而唐代的法定刑讯方式只有笞杖,因此戴就受到的刑讯与来俊臣实施的刑讯都是非法刑讯。相反,合法实施的刑讯一般没有刑讯后果的记载。如前述杨彪一案,史书明言对杨彪“拷讯如法”,可见该案刑讯是依法实施的,但未有刑讯伤害程度的记载。南北朝时期亦有合法刑讯实践的记载。梁时官员何远被控犯赃,他虽依惯例可不受测立刑讯却自愿放弃这一权利,因此刑讯的实施并不违法,而测立三七日亦与当时法定的刑讯方式与数量相符。两案中实施的合法刑讯都没有伤害情况的记载。没有伤害记载并不意味着没有伤害,只不过在史家眼中,合法的刑讯即使造成伤害,也是无可厚非的。因此,人们在观念上一般不会将合法刑讯造成的伤害视为刑讯的代价。
(二)造成错案
刑讯既可能导致受讯人如实陈述,亦可能导致虚假陈述。虚假陈述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若受讯人不能承受刑讯之苦,无罪者可能自诬有罪;若其能熬过刑讯之苦,有罪者亦可能坚称无罪。刑讯若太过严厉,无罪者自诬有罪的情况较易发生;若刑讯过轻,则有罪者不认罪的情形更易出现。对刑讯的这一不足,西方人做出了较为客观的论述。古罗马修词学书引语称: “严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实,而不能忍痛者吐不实”;法国人蒙田也说: “刑讯不足考察真实,只可测验堪忍”.② 所谓不能忍痛者吐不实即自诬有罪,能忍痛者不吐实则是有罪者不认罪。中国古代对于刑讯会迫使无罪者自诬有罪这一方面有较多关注。 《汉书·路温舒传》载,路温舒批评刑讯说:
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词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
这一观点批评了过重的刑讯会使受讯人生不如死,故而会自诬或诬陷他人。这种重刑会致人自诬的观点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 《金史·刑法志》载,金世宗在批评法司滥用刑讯时称: “棰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鞫狱者不以情求之乎?”
面对被刑讯人的不实陈述,司法者若予以采信,事实认定就可能出现错误。因此,事实认定错误亦是刑讯的代价之一。司法实践中因刑讯而导致的错案从秦代到清代屡见不鲜。前引李斯谋反案中。李斯本无罪,因严刑而自诬,并因而被定罪处罚。清代案狱笔记记载:麻城涂如松妻失踪,妻弟控涂杀妻。官拷涂甚急,遂自诬服。无证据,不能结案。续拷之,涂不堪忍受,唯求一死。其姐割破手指染成血衣,交于官。县案遂定。
本案中,涂如松被控杀妻,官府连其妻生死都未查明,但通过刑讯不仅迫使其认罪,而且迫使其家人提供了所谓的物证,从而形成错案。
(三)司法者受到制裁
适用刑讯的第三个代价是司法者因实施刑讯而受到法律制裁。由于在中国古代绝大部分时期,刑讯都具有合法地位。司法者依法实施刑讯,不管其认定事实是否正确,造成的后果有多么严重,都不会受到制裁。① 因此,司法者的刑讯成本主要出现在非法刑讯领域。中国古代法对于刑讯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刑讯主体方面:包括施刑主体和受刑主体合法,二是刑讯严厉程度方面:包括刑讯方式与数量合法;三是刑讯条件合法,包括案件事实查明程度及程序上符合法定要求。上述条件有一个不符合皆为非法刑讯。对于非法刑讯,法律有明确的处罚措施。以唐律为例,对于刑讯不符合案件查清程度要求及程序要求的,杖六十;对于拷讯数量及方式违法的,杖一百。历代法律对于违法刑讯也大都有惩罚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亦有司法者因实施违法刑讯而受到追责的情形。唐代以前因资料所限,尚未见到单纯因非法刑讯而受到制裁的司法官员。宋代时开始有相关记载。 《宋会要》载: “感德军司理杨若愚不申长吏,考决无罪人骆宪等,加石械上。若愚特追一官,典押、狱卒各刺配。”到了清代,违法刑讯受到制裁的记载也明显增多。 《比照案件》记载了几则非法刑讯受制裁的案例。
广西司钦差奏:临桂县知县田晼承审抚署窃案,并不虚心研鞫,辄将毫无指证之郭升等刑逼多伤,复押毙一命。若仅依非法殴打致死律,拟在杖徒,尚觉轻纵,请旨发新疆效力赎罪。
四川司川督咨:宁备杨英将贼犯杨贵捉拿跴压殴打之死。将杨英比照监临官因公事于人虚怯外非法殴打致死律,杖一百,徒三年。
奉天司盛京刑部奏:易图厅通判金福将案内牵连人证任绍业传案审讯,因其顶撞,拴吊逼供,致任绍业受刑平复,越三十九日因病身死,将金福照滥用非刑例,革职。
上述案例表明,中国古代立法规定的对非法刑讯者制裁规定曾并非具文,亦曾实施。
(四)刑讯代价较小且不易付出
刑讯代价只有三种,仅就数量而言,已远远小于刑讯的目的。问题在于,刑讯的代价不仅种类较少,而且代价值实际付出的可能性亦很低,我们知道,作为一种行为的代价究竟有多大,在很大程度上与代价付出者的认识有很大关系。若代价付出者认为该代价无关紧要,则该代价就应视为较小的代价。古代刑讯代价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前文指出,刑讯的代价在有三个方面。一是刑讯对被刑讯人的人身伤害。但将这一伤害视为代价主要是依据现代人的观点,其理论依据是无罪推定的观念。嫌疑人在未经生效判决前不得被认定为有罪,因而不得通过刑讯伤害嫌疑人。但在中国古代,并未形成无罪推定理念,嫌疑人被刑讯在立法者与司法者看来并无不妥,否则刑讯也不会合法。既然如此,合法刑讯造成的伤害在人们的观念上就没有被视为刑讯的代价。即使是非法刑讯造成的伤害,也并非全部被视为代价。通常情况下只在刑讯非法、受刑讯者无辜且刑讯伤害极端严重的时候,人们才认为刑讯的伤害是不能接受的。南宋人吴雨岩曾言: “诸郡狱案,有妄捉平人吊打致死者,斯民何辜,而罹此吏卒之毒。被追之人,非必皆有所犯,见吏卒或捆或踢,继以百端苦楚,苟有仁心,宁不为之痛心疾首。”在论者观念中,对“非必皆有所犯”之人实施刑讯而吊打致死才视为刑讯造成了恶劣的后果。这表明刑讯的客观伤害结果要变成人们观念上的伤害结果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中尤其是“被刑讯者无辜”在司法者决定实施刑讯的时候很难具备,因为大部分司法者在实施刑讯时都相信被刑讯者有过错的。因此这三个条件很难同时具备。退而言之,刑讯即使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刑讯给受刑讯人带来伤害也大都不是刑讯实施者的感受,而是旁观者的认识。而被旁观者视为是刑讯代价的伤害很难成为阻碍司法者实施刑讯的因素。
刑讯的第二个代价是刑讯可能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此类案例在古代社会不胜枚举。前文已述,此处不赘。可能造成错案这一代价对于刑讯实施的阻止作用究竟如何,我们可作如下分析。我们知道,刑讯的目的有七种,发现真实只是其中一种。也就是说司法者只有在认为刑讯是为了发现真实时,才可能想到到刑讯也许发现不了真实。如果刑讯本来就不是为了发现真实,那么,可能造成错案就不会成为阻碍因素。比如刑讯是为了消除疑罪、追求认罪口供、收集有罪证据,获得有罪认定结果,或维护体现官威,事实认定是否正确原本就不是司法者特别关注的。更有甚者,有的司法者实施刑讯就是为了认定错误事实,如司法者有意制造冤案时即是如此。即使刑讯的目的是为了发现真实,事实认定错误这一成本对刑讯的阻碍作亦很有限的。由于中国古代审判中强调五听听讼,司法者通过察辞观色已认为受讯人有罪,并进而对其刑讯。此时司法者先入为主,不会担心刑讯会致被刑讯人自诬,自然也很少有刑讯会致使事实认定错误这样的担忧。
刑讯的第三个代价是实施刑讯受到制裁。前述研究表明,古代社会制裁非法刑讯的制度与实践都存在。但非法刑讯可能受到的处罚不足以成为非法刑讯实施的阻碍因素,这与中国古代非法刑讯的实施者被追究责任情形的特点有关;具体而言,中国古代非法刑讯被处罚的实践有几个特点:一是处罚轻,二是条件严,三是发生少。
就非法刑讯的处罚程度而言,目前尚未看到因实施非法刑讯而被定死罪的情形,通常都是免官或革职、稍重的杖徒。清代出现的一例将非法刑讯者流至新疆效力已经是很极端的情形。相比较非法刑讯动辄致人死亡,上述处罚显得过于轻纵,不足以对非法刑讯实施者形成威慑。
就非法刑讯行为人的制裁条件而言,司法实践中的条件相当严格,非法刑讯的实施必须满足多种情形才可以构成非法刑讯的惩罚条件。一般而言,非法刑讯者欲受到制裁,必须具备非法刑讯致人死亡,受刑讯者无辜及刑讯主体、刑讯方式非法等条件。上述条件也许不要求同时具备,但被刑讯人死亡及刑讯方式非法是基本条件。但被刑讯人死亡在非法刑实施时司法者很难预见,即司法者在实施刑讯一般不会想到被刑讯人会被刑讯致死,因而这一因素很难成为非法刑讯实施的阻碍。就非法刑法受到制裁的发生概率而言,也是非常低的。见诸史册的非法刑讯实施者大都没有受到制裁,唐代以前则未见相关记载。
如前述汉代戴就案的审理者及唐代的来俊臣,都没有因为非法刑讯而受到惩罚。非法刑讯受制裁的实践条件严格是其概率低的主要原因。另外,中国古代司法官员之间官官相卫的传统及各级司法官员本身对刑讯的认可亦是导致非法刑讯者难以受到制裁的原因。非法刑讯制裁的低概率导致它很难成为非法刑讯适用时司法者要考虑的要素。
对于非法刑讯的三个代价,前两种在司法理论上经常会受到关注。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的司法理论经常有批评刑讯的内容,而批评刑讯的一个重要理由即为由无辜者受到刑讯及被迫自诬。但到了具体案件的审理中,能够被司法者视为是刑讯代价的主要是后一种。前两种代价对司法者而言只具有道义上的不正当性,而道义上的坚守在面对破案的巨大压力时很容易被击败。因此能否有效阻止司法者实施非法刑讯,主要就在于法律对于非法刑讯实施者的处罚是否严厉及是否能真正实现。恰恰在这一方面,中国古代法律做得非常不到位。
三、中国古代刑讯目的与代价的特征对现今司法的影响
(一)刑讯依然能实现诉讼目的
刑讯目的多样且易实现,而代价较少又难以真正付出,这导致中国了中国古代非法刑讯的长期存在。当下中国的刑事司法过程中,刑讯现象亦难以根绝。与中国古代司法者一样,发现案件真实依然是诉讼的主要目的。但诚如前文所言,司法者在案件侦破的压力下,常会将发现真实的目的异化为对被告人进行有罪认定的目的。中国当下的司法者与他们的古代先辈一样存在着很大的案件侦破压力,具体表现为案件的破案率与破案期限的压力。特别是一些重大案件,更强调破案率,很多侦查机关就强调命案必破。倾向于有罪认定的审讯目的导致司法者会追求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而嫌疑人无论是有罪还是无罪,都很难主动作出有罪供述。因此,通过刑讯来迫使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就很容易被侦查机关采用。而且刑讯可能获得的证据还不只是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侦查人员还有可以通过嫌疑人的供述再发现其他嫌疑人有罪的证据。刑讯的这一功能会使得被我国诉讼法中“仅有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有罪”这一规定遏止刑讯的功能被化解。因为司法者可以通过刑讯获得嫌疑人口供,再通过口供获得事实认定的其他证据。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司法者面临的案件侦破压力与刑讯逼供的实施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相关调查结果也验证这一关系的存在。有针对警察的调查表明,有86. 4%的受访警察认为“法律规定的办案期限,实践中的限期破案、破案率”等要求会给办案人员带来很大压力,从而导致刑讯逼供。可见,就刑事案件侦查的目的而言,刑讯是较容易实现目的的重要手段。
(二)刑讯代价不易付出及原因
1.刑讯代价不易付出
再从刑讯实施代价来看,亦不利于有效遏止刑讯。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刑讯的代价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刑讯实施者受到的实体处罚;二是刑讯获得的证据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
对于非法刑讯实施者的制裁,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 “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适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结合《刑法》第234条、第232条内容,司法者在刑讯逼供过程中致人伤残、死亡的,按照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处罚,法定刑最高可能是死刑,比古代对非法刑讯的处罚要重得多。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者因刑讯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难得一见。许多以刑讯逼供抗辩的刑事案件,多被以证据不足而不予采纳,或简单认定刑讯逼供“与客观事实不符”,这一比例占刑讯抗辩案件的绝大多数。因而刑讯实施者受到制裁的可能性亦远低于刑讯的实际发生数。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我国法律亦有规定。 “两高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主要是刑讯或其他非法方式取得的言辞证据,物证和书证等实物证据不在内。如果侦查人员通过刑讯获得了相关案件信息,再顺藤摸瓜,获得其他重要的实物证据,案件移送起诉时只将实物证据移送,被告人一方就无法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上述证据排除。可见刑讯取证虽属非法,但其获得的证据依然能够实现司法者的办案目的。由此来看,非法证据排除的不全面在很大程度上会激励司法者刑讯取证。那些可以排除的非法言词证据在实践中被排除的可能性亦非常低。据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发布的“新刑诉法实施状况年度调研报告”显示: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有42. 1%受访律师表示“在审查起诉环节中虽提出过申请,但公诉机关没有回应”. 2014年3月3日《京华时报》载,陈光中教授也指出,从过去一年(2013)看,非法证据排除有成绩,但是阻力比较大、难度比较大,并没有严格执行,成功的案例比较少。
从理论上讲,司法人员非法取证会受到很严厉的制裁,而且该证据还不能被用来认定事实,即司法人员承担很大风险获得的是无用证据,司法者应当没有必要再进行刑讯逼供。但事实上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刑讯逼供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并且还在不断地制造冤假错案。盘点近年来的冤假错案,如浙江张高平、张辉强奸杀人案,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湖北佘祥林杀妻案,云南杜培武杀人案等,背后都有刑讯逼供的影子。
2.刑讯代价难以付出的原因
制裁刑讯实施者与非法证据排除都是刑讯的代价。这两个代价要真正付出需要同一个前提,即刑讯逼供行为被确认。但依我国法律规定,确认刑讯存在两个障碍:一是刑讯存在的证明机制。依目前的机制,刑讯的存在需由被告人或其辩护人证明。在案件进入审判阶段之前,由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对侦查机关实施的刑讯向检察机关提出,由检察机关来认定刑讯是否存在。但刑事案件的侦查基本上处于秘密状态,侦查人员是否适用了刑讯需要嫌疑人来证明,而嫌疑人被侦查机关控制,很难证明自己受到了刑讯。而且有些案件的侦查就是由检察机关实施的,如对国家公职人员的贪污受贿案件的侦查即是如此。在此情况下,若犯罪嫌疑人指控侦查人员实施刑讯,就会出现嫌疑人控告检察机关,但仍由检察机关来审查的情形。这种体制下的审查很难确认刑讯存在。在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如被告人主张受到刑讯,则由法院来审理。此时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成了被审理对象,法院居中裁判,从审理架构来看无可厚非。
问题在于若法院经审查认定了控方提供的证据是刑讯取得,就应排除该证据;而该证据往往是关键证据,一旦被排除,对被告人犯罪事实就无法认定,案件就应当作疑罪从无处理。但在实践中这一结果很难被审判方接受,我国法院还没有做好做出罪疑从无判决的心理准备。特别是现行体制下检察院与法院地位平等,法院在制度设计上并不能居高临下审理检察院的事务。立法强调司法机关之间的制衡与配合,但实践中更重视配合而非制衡。从司法机制来看,刑讯很难被认定。
二是刑讯方式的变化。当下的法律全面禁止刑讯,因此司法者在实施刑讯时自然知道其后果。为此,司法者在实施刑讯时往往不会选择可能给受刑讯人留下痕迹的刑讯方式,而是采用不让受刑讯人休息、用强灯泡照射眼睛等变相刑讯,这些变相刑讯与普通刑讯一样会给受刑讯人带来很大痛苦,一样能够迫使受刑讯人作出违背自己意愿的陈述。如受刑讯人后来主张自己曾受到刑讯,即使审查机关予以审查,若侦查机关不承认实施刑讯,受刑讯人也无法证明刑讯曾经发生。
(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同中国古代控制非法刑讯效果甚微一样,当下法律遏止刑讯的效用亦不明显。根本问题在于两者都没有能够控制刑讯目的数量与易实现性,也没有使刑讯代价的付出落到实处。要使刑讯能够被切实控制,必须解决好这两个问题。现行刑讯认定机制存在的缺陷及变相刑讯方式的广泛采用导致刑讯很难被认定。刑讯如不能被认定,则视为没有刑讯。即使偶尔有一些审理中的刑讯获得的认定,也是因为后来出现特别有力的新证据导致了案件被重审。但这种机会出现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司法者在实施刑讯时一般也不认为其认定的事实可能被推翻。那么,司法者就不会担心因实施非法刑讯而受到制裁。这样在追求追求破案立功、避免不能破案受责的目的影响之下,实施刑讯就难以完全避免。笔者认为,欲要控制刑讯的发生,应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就非法证据排除而言,相关立法可以考虑适用“毒树之果”规则,将刑讯逼供获得的实物证据亦予以排除。同时,考虑到犯罪嫌疑人对刑讯适用举证困难的情形,可以兼采两种举证模式:一是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当嫌疑人或被告人主张受到刑讯时,由侦查机关证明刑讯不存在,如果侦查机关无法证明不存在刑讯逼供,可以推定发生过刑讯。推定发生刑讯的法律后果应设定为排除刑讯获得的证据。① 二是适用正常的举证模式,即由嫌疑人或被告方证明刑讯存在,如他们能够证明有刑讯存在,则不仅对非法刑讯获得的证据应予排除,还应当追究刑讯实施者的法律责任。两种举证模式的选择权由嫌疑人或被告人行使。若嫌疑人与被告人能够享有这一权利,对于真正发生刑讯逼供的案件而言,轻则否定非法证据,重则惩罚刑讯实施者,前者可以使刑讯的目的难以实现,后者则使刑讯代价落到实处。如此可以有效的遏止刑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