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保辜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极具特色的法律制度,在唐代臻于成熟。保辜制度的目的在于确定伤害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具有对受害人进行保护、对加害人赋予悔改机会以平稳修复社会关系的深层内涵,从某种意义上其与当代的刑事和解制度的目的有着一定的相通性,对于完善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具有积极意义。借鉴唐代保辜制度理念,可以从扩大适用范围、增加审查起诉阶段观察期、加大司法机关参与力度、实行执行阶段保证人制度等方面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
关键词: 保辜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 唐代; 法律文化;
Abstract: The system of Baogu was a very distinctive legal system in ancient China,which reached maturity in the Tang Dynasty.The purpose of Baoguo system is to determin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armful behavior and the result.It has the deep connotation of protecting the victim and giving the victim an opportunity to repent to restore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smoothly.In a sense,it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commonality compared to the purpose of the contemporary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system,which has positive meaning for improving the current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system.Referring to the concept of Baogu system of Tang Dynasty,we can improve China's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system in terms of expanding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adding observation period to the review prosecution stage,increas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judicial organs,implementing the guarantor system in the implementation stage and so on.
Keyword: Baogu system;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system; Tang Dynasty; legal culture;
保辜制度作为我国古代一项极具特色的法律制度,自产生之日起,经过历代的不断发展,到唐代发展完善。唐代保辜制度正式入律,对其后该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元明清时期的保辜制度基本沿袭了唐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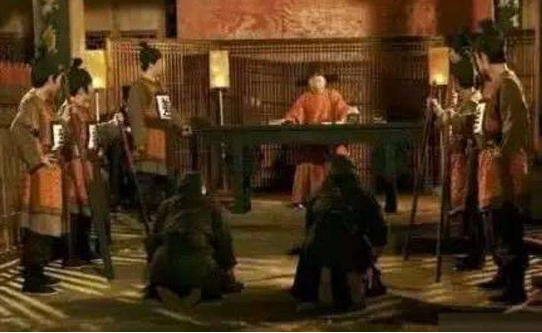
目前学者对唐代保辜制度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其制度设计、因果关系等方面,对于“保辜”制度的内涵,学者多引述《说文解字》或《大清律辑注》中的语句简单带过,没有作进一步解释。同时,对“保辜”两字学界也没有统一界定,不少学者对保辜制度甚至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持怀疑态度,认为“传统”与“当代”是不相融洽的,或者说互不相通的。但是传统法律体系的瓦解并不代表“法传统”也不再延续,相反,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以及由其影响而形成的“法传统”内在理念有着巨大惯性,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审视思考。有学者对古今刑事和解制度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其完全是“殊途异归”[1],但笔者认为,要想更好地理解保辜制度与当代的刑事和解制度,仅仅从表面分析对比是远远不够的,应该从其内涵开始,通过探究其内在理念,挖掘其背后的价值。因此,本文探究唐代保辜制度的内涵,并以此为视角分析我国当代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缺陷,进而提出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构想,以期为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参考。
一、唐代保辜制度
保辜制度自产生之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直到唐代被写入《唐律疏议》才正式入律。《唐律疏议》对保辜制度的详细规定和严密注疏,使古代的保辜制度臻于成熟。
(一)唐代保辜制度的基本内容
保辜制度是指在发生伤害案件后,加害人在法定的期限内积极救助被害人,期限届满时,根据受害人的具体伤情对加害人定罪量刑的法律制度。戴炎辉先生在解读唐律时认为:“故保辜之‘保’,若欲求三种保辜之共同内容,应解为系‘保留’之意,非‘保护’之谓。”1因为唐律中并没有强制加害人对被害人进行救治,只规定“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2]1482而且“保辜”一般由加害人向官府提出,加害人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虽然法律并没有让其施加救治的要求,但加害人如果想求轻判,则要悉心照料被害人使其符合法条规定。可见保辜制度是在给予加害人一定利益的基础上,使被害人获得更大的利益。加害人是否救治被害人,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是否诚心认罪、悔改,是否真诚弥补被害人的损失。因主动性在加害人自身,官府在此期间处于观察状态,如何定罪尚且“待定”,为了突出这种“罪名待定”的状态,故此处“保”做“保留”来解释更加合理,而“保辜”,则可以理解为“保留罪名”。
1. 保辜制度的适用范围
《唐律疏议》列出了关于保辜制度的具体条文。《斗讼律》第307条:“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支体及破骨者五十日。殴、伤不相须。余条殴伤及杀伤,各准此。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因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他故,谓别增余患而死者。”[2]1482并佐之以相应注疏。对条文内容进行解释的同时,对保辜适用的案件范围作了说明:“议曰:凡是殴人,皆立辜限。手足殴人,限十日;若以他物殴伤者,限二十日;若折骨跌体及破骨,无问手足、他物,皆限五十日。……谓诸条殴人,或伤人,故、斗、谋杀,强盗,应有罪者,保辜并准此。”[2]1482另外,涉及到保辜制度的条文还有第302条“斗殴以手足他物伤”[2]1468、第303条“斗殴折齿毁耳鼻”[2]1470、第304条“兵刃斫射人”[2]1472、第305条“殴人折跌支体瞎目”[2]1475、第308条“同谋不同谋殴伤人”[2]1485等。在《斗讼律》之外,保辜的规定也可见于其他各律,涉及到的内容广泛,如《贼盗律》中第286条“以他故殴人因而夺物”[2]1400和第289条“因盗过失杀伤人”[2]1411等,保辜期限大多比照斗殴杀伤罪来确定。
由此可以看出,唐代保辜制度主要适用于以斗殴为典型特征的杀伤类案件,但具有伤害性质的其他案件也包括在内。凡是可以考虑到的范围之内的案件,皆可保辜。例如吐鲁番出土文献中记载的一个类似交通肇事的案例“唐宝应元年(公元七六二年)六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一个叫康失芬的人因为不熟悉借来牛车的性能,力有不及,拽挽不住,牛车失控,碾伤了路边门前坐着的男孩金儿、女孩想子,导致金儿“腰以下骨并破碎,恐性命不存”,想子“腰胯折”的严重后果。康失芬对自己的罪行如实供述,“愿保辜,将医药看待,如不差身死,请求准法科断”,因为他实属过失,官府“放出,勒保辜”。依照唐律规定,虽不属斗殴,但此案件依然属于“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保辜期限为五十日[3]。
2. 保辜期限的确立标准
唐代保辜期限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不允许双方当事人自行约定。由《唐律疏议》中关于保辜的相关规定来看,“辜限”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第一,用手、脚等身体部位致人受伤的保辜期限为十日;第二,用手脚以外的其他器物致人受伤的保辜期限为二十日;第三,用兵刃、热水或火致人受伤的保辜期限为三十日,此处相比前一级别,所用器物的危险性增加;第四,不论用何手段致伤,只要造成被害人折跌肢体、破骨的,保辜期限均为五十日。由此四个级别可以看出,唐代保辜期限的确立,根据加害人所用器物或手段的危险程度以及被害人受伤的轻重程度来定。保辜期限的长短与加害人所用器物的危险性大小有直接关系,所用器物之危险性愈大,保辜期限则愈长。
(二)保辜制度的内涵
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实施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也同时体现出一定的价值倾向,因此,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解读唐代的保辜制度。第一层面,保辜制度是一种因古代医疗设备以及技术的局限性,而采用的确认加害行为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方法;第二层面,保辜制度包含着因儒家“非讼”“和合”文化的影响,给予加害人改过自新、真诚悔罪的机会,以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的价值取向。在唐代,保辜制度的第一层面处于更加突出的地位,“保辜本质上,系对结果犯限定其因果关系者”2,基于当时医疗诊断水平的限制,为确定案件具体的因果关系固然要使用较为朴素又略显复杂的一套方法;但在保辜制度的发展及实践过程中,其无意中达到了国家让渡一定的司法权力给加害者,使受害人获取更大的利益,从而达到社会和谐的效果,即保辜制度第二个层面的涵义,也正是从这一层面上来看,保辜制度蕴含着深层次的超越时代价值的法理念。
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保辜制度必然有其时代局限性,可以说是统治者为了平息社会斗争、保证稳定、坐稳江山而施行的。但是,保辜制度具有通过对被害人进行救助而达到修复社会关系、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从而维护社会和谐的深层含义,因此仍然值得关注。
首先,从远古社会开始,施行仁政、慎用刑罚就已经为大多数统治者(首领)所践行。为了效仿三皇,西周时期周公提出“明德慎罚”,后儒家思想将其再次发展弘扬,主张“先教后刑”“德主刑辅”。虽然历史上不乏滥施刑罚的统治者,但总有忠孝臣子对其进行劝谏。陈子昂在上书武则天反对其严于用刑时说:“臣闻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义也;霸者威之,任权智也;强国胁之,务刑罚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后威之,威之不足,然后刑之。”[4]保辜制度的目的虽然是为了确定案件的因果关系,但也反映了统治者慎刑慎罚的思想。同时,保辜制度给予加害人一定的选择权仅仅是国家赋予其主观悔罪、补救的机会。换句话说,保辜是为加害人设定特定时间的“不确定状态”,这段时间里加害者自身并不是自由的,仅是多了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也使国家多了一个少施刑罚的机会。
其次,在统治者“仁政”及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生发了社会对“和谐”的追求。孔子称“和为贵”,提倡“无讼”“息讼”,要求人与人和睦相处,提倡用和解的方式化解矛盾和纠纷,尽量不要诉诸公堂。梁治平先生说:“……强调绝对的和谐,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乃至整个宇宙之间的洽和无间。于是,争讼成了绝对的坏事,法律亦被认为是‘必要的邪恶’。”[5]此时维持和谐社会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6]。对当事人劝说或感化,使其自我反思,从本质上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性质,达到对行为人改造、温和修复社会关系的效果。
因此,笔者认为,在对比研究古今法律制度时不能将已经落后,或已经被更先进的技术所取代的具体的法律条文纳入比较范围。从第一个层面来讲,伴随着发达的医学技术,保辜制度已经被当今刑法因果关系体系所替代,其具体形式和内容与当今时代并不相适应。但是,就第二个层面来说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传统并不是凝固的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传统不仅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而且对现实具有巨大的影响力[7]50。从这个角度分析,唐代保辜制度与当代刑事和解制度内在的法理念有着一定的相通性,其在对被害人救助、修复破损的社会关系、消除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等方面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对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仍然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二、我国当代刑事和解制度及存在问题
(一)刑事和解制度基本内容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及其亲属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与协议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8]。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将刑事和解作为特殊程序予以规定,在此之前也多有实践。2018年修订后的刑诉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
刑事和解制度通过让渡一部分利益给加害人,让加害人更好地配合,实现被害人损失弥补的最大化以及社会关系修复的平稳化。加害人与被害人和解,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解决纠纷,节约司法资源,另一方面可以弥补常规刑事案件忽视被害人与被告人意愿的不足,更加有效地化解双方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修复社会关系。
我国刑事和解的兴起,与西方辩诉交易、恢复性司法有一定的关系,其本质在于鼓励人际关系的修复,让彼此恢复原来的状态,较好地兼顾受害人、侵害人和社会多方利益[9]。由此看来,刑事和解制度与唐代保辜制度所追求的效果是一致的,是对我国固有的“和谐”的法律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继承与发扬。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缺陷
第一,“花钱买刑”问题。我国现行刑事和解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最突出问题“花钱买刑”。在刑事诉讼法中“真诚悔罪”“赔礼道歉”的程度和方式没有明确界定,实际执行过程中没有鉴定标准,正是这种构建在加害人给予被害人简单物质补偿基础上的和解,使人们质疑它是富人“花钱买刑”的工具。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往往只关注和解的结果,忽视和解的过程。刑事和解过程中双方都在尽力追求自己权益最大化,加害人希望通过物质金钱补偿被害人,以减轻罪行,被害人希望获得大额赔偿来弥补自己的损失,只有关注刑事和解的过程,才能更好地平衡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利益。如果只关注刑事和解结果,由于和解之后往往不会对加害人造成其他方面的损失,会使人认为可以用一定的物质和金钱来弥补犯罪,降低犯罪成本。同时,对于被害人是否因为急需钱物而被迫达成和解,是否被加害方要挟利诱,司法机关均不好评判,更难以取证,从而加剧了“花钱买刑”,甚至“花钱犯罪”的问题。
第二,刑事和解适用范围较窄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我国刑事和解仅适用于“三年以下”轻微刑事案件和“七年以下”过失犯罪的初犯人员。这类案件社会危害性小,或者多为邻里、亲朋之间的矛盾纠纷,犯罪人往往并无恶劣行径,本身可以加以良好改造。但是个案情况均不相同,造成某些虽超出此范围但同样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被排除在外的情况。例如下面案例:一个女孩为了躲避男友,从楼上摔下,高位截瘫,每天治疗需要巨额医疗费,全家人花费全部积蓄仍差十几万元[10]。其男友其实也并非故意,只是理解有误,并且在事后真诚悔过,表示如果女方可以谅解他,虽积蓄不多,但他愿意凑足所需医疗费,并且希望自己可以娶女孩为妻,照顾其后半生。女方很感动,愿意和解,但是法院拒绝了和解请求,判处男方八年有期徒刑。导致男方既无心凑钱,也无法兑现诺言,女孩绝望哀求父亲杀死自己,父亲只得痛下杀手,又酿成另一个悲剧。虽然这个案例发生时我国并没有刑事和解制度,但是根据现行法律,目前也仍不适用刑事和解。
第三,刑事和解监督机制不完善问题。虽然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要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并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进行刑事和解。但是在实践中,公检法机关自身事务众多,为了节约司法成本,提高案件审理的效率,会急于促成刑事和解,致使刑事和解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缺乏有效监督,刑事和解制度无法真正发挥平衡案件双方当事人利益之作用。
三、唐代保辜制度之于当代刑事和解制度的启示
保辜制度与当代刑事和解的内在法理念有着一定的相通性,也正因为如此,其对于我国当代尚不完善的刑事和解制度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笔者以为唐代的保辜制度为刑事和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
(一)唐代保辜制度的积极意义
第一,保辜制度给予加害人弥补过错,诚心悔过的机会。加害人在一定的期限内是否对被害人进行救助直接影响定罪量刑,使得加害人在此阶段不得不对自己的伤害行为进行反思,在与被害人更多的接触交流后,体会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包括对被害人以及对自己造成的后果,从而在道德层面反省自己的过错。保辜制度将惩罚与教化相结合,提高了法律的信服度,也符合我国刑法宽严相济的价值目标。
第二,保辜制度体现了对被害人给予更多关注,提供积极救助的理念。虽然唐代保辜制度有确认加害行为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作用,但其主要目的仍然是保护被害人的权益,以被害人的受伤程度和加害人的补救程度作为处罚标准,同时设立了适用不同伤情的考察期限[11]。为了减轻处罚,在保辜期限内加害人会积极为被害人医治伤病,特别是在受害人因经济状况有限而不能得到很好的医治情况下,加害人若提供及时的救助,会大大提高被害人治愈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保辜不但是对于加害人的救助,更是对被害人的救助。
第三,保辜制度中“和谐”理念在当代具有重大价值。中国社会向来倡导“和为贵”“和合”“与人为善”的思想,追求社会和谐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加害人主动为被害人提供救助,悉心照料、探望、安慰、赔礼道歉,这样往往能够得到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减少精神层面的二次伤害,使受损的社会关系得到平稳修复,防止矛盾激化,稳定社会秩序,而这一点与我国当代刑事和解制度是一脉相承的。
第四,唐代保辜制度体现了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的理念。加害人主动提出保辜请求的案件,一般案情较为明晰,经过官府审核批准后,加害人被释放,即可立即投入到对被害人的积极救助中,所需时间短,极大减少了复杂的诉讼程序,节约了司法资源,使得有限的司法资源转向更复杂的案件,大大提高司法办案效率。
(二)完善刑事和解制度之构想
1. 扩大刑事和解适用范围
如前文所述,唐律中保辜制度的适用范围比较广泛,不仅适用于伤害罪,还规定了过失杀伤等案件,因斗殴而间接引起的伤害,如被恐吓摔倒致伤等情况,亦适用保辜制度。一些非斗殴的伤害案件,同样适用保辜制度。同时,殴打伤人、杀人的,都依此条文行事,不论是殴打伤人、故意伤人、打架斗殴使人受伤、谋杀、抢劫,伤害别人、致人损伤的,都按照该条文施行。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只有轻罪案件才适用刑事和解,重罪案件均不在刑事和解的范围之内。纵然也有观点认为有关重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并不会在我国传统(并延续至今)的法律文化土壤上顺利地生根发芽,进而提出这一范围(重罪)内的“刑事和解”完全没有存在的可能性[12]。但笔者以为,这种限制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有一定的局限性,重罪案件也分多种情况,应该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双方意愿、具体情况来判断是否适用刑事和解。如果案件双方当事人都希望刑事和解,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死亡赔偿金并不多的情况下,应允许适用刑事和解,被害人家属则有可能获得更高的补偿,避免失去亲人又失去赔偿的情况发生,避免如前述案件父亲痛下杀手的更大悲剧。但同时刑事和解制度并不具有强制性,受害方具有更多自主权,如果受害方不希望和解,那么和解的基础就不存在,则刑事和解完全不应适用,所以扩大刑事和解范围并不意味着扩大和解的必然性,而是给予更大范围案件刑事和解的可能性。
2. 增加审查起诉阶段观察期
唐律根据加害人使用的器具和被害人的受伤程度,规定了不同的保辜期限,在保辜期限内,加害人可以通过为受害人提供积极救助而减轻处罚,同时也使被害人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如果被害人在保辜期限内恢复,加害人就会得到减轻刑罚的待遇;如果被害人在保辜期限内死亡,则加害人就会被按斗殴杀人罪处以死刑。
借鉴唐代保辜做法,当今的刑事和解制度可以在审查起诉阶段增加观察期,根据案件的轻重程度设立不同的观察期限。由加害人提出,经被害人以及司法机关的同意后,对被害人做初步伤情鉴定,然后在加害人在提供担保的情况下,为其设定一定的观察期限,在观察期内,由加害人对被害人进行医疗救助,待观察期限届满后对被害人进行第二次伤情鉴定,以第一次鉴定与第二次鉴定分别定罪量刑,并且综合考虑加害人在这一期限内的悔罪表现以及被害人的恢复程度,再确定具体的民事赔偿数额。这样既给了加害人积极悔罪的机会,也使得被害人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
观察期的实行,能够防止刑事和解“花钱买刑”的产生,因为加害人不能给钱了事,而是要对被害人进行切实的救助;观察期间加害人与被害人不可避免地多次接触,也使他们有更多交流机会,从而促成矛盾的缓和。另外,因为适合于刑事和解制度的仅限于轻伤害案件,而在轻伤案件中加害者往往是非故意的,造成的后果也不是很严重,但在刑事和解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被害人漫天要价、小病大养等情况,无形中加重加害人的刑事责任,而在观察期内,加害人是根据受害人病情治疗情况提供费用的,因此能够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因此,观察期的设立可以更好地协调被害人与加害者之间的利益平衡,达到刑事和解制度的目的。
3. 加大司法机关参与力度
唐代保辜制度是由加害人向官府提出的,并且保辜的决定也全在官府,可以避免加害人以不正当手段达成与被害人和解的情况。在当今的刑事和解制度中,司法机关的作用不可或缺,虽然刑事和解是由当事人提出的,是否和解决定权在于当事人双方,司法机关不应过多干预,但司法机关也不能放任不管。同时刑事和解过程中的诸多事宜,包括对加害人的请求进行审查、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磋商以及最后进行评估等等,都离不开司法机关的参与。但是如前所述,司法机关事务众多,不能把主要精力用于刑事和解,从而无法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在刑事和解中的监督作用。为此,要加大司法机关的参与力度,可以在司法机关设立刑事和解部门,专门负责可以进行刑事调节案件的具体事宜,从而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的监督职能。
4. 实行执行阶段保证人制度
在和解后的执行阶段,为了防止加害人报复被害人或者拖延不执行等情况出现,有必要增加保证人或者监督人,由保证人提供担保,监督加害人的执行情况。在公检法工作繁重的情况下,也可以增加“刑事和解执行工会”,由专门人员来进行和解评定和监督工作。
四、结语
唐代保辜制度诸多具体规定已经不适合于当代,但其所蕴含的内在理念对当今的刑事和解制度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有学者认为将保辜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比较是“似是而非”“形同实异”的比附[12]。但是笔者认为,两者“形异而内同”。如果“实异”是指两个制度所生存的制度背景,或者其经济基础,那么古今对比则毫无必要。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已经在西方强大的外力下解体,但是其生长的中国本土文化环境完全没有断代,中国五千年传承的法传统仍具有巨大的惯性,以各种方式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果在刑事诉讼法中适当借鉴保辜制度,则首先应剥离其具体适用规则,而深入批判继承其内在的法传统,法传统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凭着历史的发展惯性影响着现实,而现实中的许多问题也正产生于这“不自觉”的“惯性”。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传统的重要,并有意识地“激活”传统中有益于现实、有利于发展的成分,传统才能成为发展的动力而不是阻力[7]65。对于刑事和解制度,其本身就带有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也应在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加以完善改造,以更好地适应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卫红.殊途异归:古今刑事和解[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2):115-119.
[2]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6.
[3]刘海年,杨一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四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190-194.
[4]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144.
[5] 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M].修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393.
[6]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78.
[7]马小红.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陈光中.刑事和解再探[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2):3-9.
[9]狄小华,李志刚.刑事司法前沿问题:恢复性司法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6-15.
[10] 女孩躲避强奸摔成高位截瘫,苦求下老父将其掐死[EB/OL].(2006-02-22)[2020-01-25].http://news.sohu.com/20060222/n241956772.shtml.
[11]傅承鸿.唐代保辜制度研究[D].泉州:华侨大学,2017.
[12]赵晶.刑事和解与中国古代法文化的若干断想[J].保定学院学报,2011(5):65-68,87.
注释
1参见戴炎辉《唐律通论》。
2(1)参见戴炎辉《唐律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