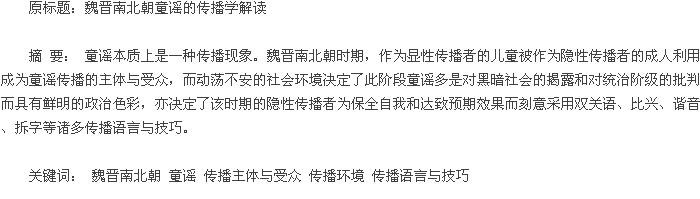
所谓童谣,乃是童子所歌之谣,是民间歌谣的组成部分。清人杜文澜在《古谣谚·凡例》中将儿谣、女谣、小儿谣、婴儿谣等一并归入童谣,或者也可称为“孺子歌”、“儿童谣”、“小儿语”等。古代童谣不同于现代童谣,古代童谣的内容或是对人物的褒贬,或是对政治事件的评论,多是与政治接轨的,可以说是营造政治舆论的一种传播手段,故其存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拟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童谣作为解读对象,分别从童谣的传播主体与受众、传播环境与内容、传播语言与技巧三个层面进行阐释,以求管中窥豹,一探童谣的传播本质。
一、传播主体与受众
童谣作为一种传播活动,主要借助口头传播,一方面能使信息得到快速传播,另一方面能使传播者及时获得反馈信息。古代童谣的传播主体有两个: 一是隐性传播者即成人,二是显性传播者即儿童。众所周知,大多数童谣的作者无从考察,只能从侧面加以揣测,“其歌皆咏当时事实,寄兴他物,隐晦其词,后世之人,鲜能会解。故童谣云者,殆当时有心人之作,流行于世,驯至为童子所歌者耳”,即古之童谣,皆是大人所作而儿童歌之者。[1]
“童谣中的不少预言之所以常验,就在于它是有远见的成年人所作,或是早已设下了圈套的政治家、阴谋家所作。”[2]处在第一位的隐性传播者,之所以隐而不见,盖主要出于“慎言”的考虑,《周易·系辞传》云: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 ‘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3]
如果语言不慎,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祸患。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传播者和受众的身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相互交替的; 换言之,一个人在发出信息时是传播者,而在接受信息时则又在扮演着受众的角色,所以作为一个小群体的儿童,既是童谣的传播者又是其受众。他们先是接受隐性传播者所编写的童谣,然后充当传播者的角色将其传唱给大众。而隐性传播者之所以选择儿童作为传播童谣的对象,大致有如下原因: 一是就受众层次来说,儿童算是层次较低的受传者,他们没有丰富的阅历和经验,不懂政治,也不关心政治,但恰恰是儿童这种天真烂漫的本性,使得隐性传播者选择他们进行传播,这样可以使没有心机的儿童( 受众) 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中接受传播者的意图,产生与传播信息相一致的心理,进而使传播活动得以顺利进行。二是利用儿童传唱童谣体现了西方“魔弹论”的受众思想。“魔弹论”是早期受众理论的代表,认为传播者发出的信息就像出膛的子弹,威力无比,而受众就像是射击场上的靶子,只要被魔弹射中,就会发生预想的效应。儿童就像是中弹的靶子,可以随时被隐性传播者加以利用。三是中国古人有“儿童是荧惑一星的化身”之说,荧惑乃是执法之星,认为儿童所传唱的童谣是上天的旨意,《三国志·陆凯传》云: “臣闻翼星为变,荧惑作妖,童谣之言,生于天心。”《晋书·天文志》云: “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岁星降为贵臣; 荧惑降为童兑,歌谣嬉戏,……吉凶之应,随其象告。”所以,尽管儿童所传唱的童谣都是一些敏感性的政治评论,但那些被谴责的对象也不会对他们兴师问罪。这应是隐性传播者的高明之处,利用儿童是神的化身和没有心机的特点,一方面保护了自己,另一方面也易于达到传播的目的。
二、传播环境与内容
传播活动必然要依赖一定的环境来进行,换言之,它必然要以某种形式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因此,要探究某种传播活动,首先应先了解其传播环境。环境既是媒介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也是人类进行传播活动的基础。其中,社会环境是指由人类主体聚集、汇合后所形成的社会状况和条件,其构成因素也是复杂多样的。单就对传播活动的影响来说,社会环境主要包括四个因素: 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讯息因素。而古代童谣作为一种传播活动,离不开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可以说,它们是对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表达了对时政和统治阶级的认可与否。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战乱和分裂成为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先是三国纷争,统一不久的西晋又发生“八王之乱”,随后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称为“五胡十六国”的混乱时代,而南方东晋王敦、桓玄等人也伺机作乱; 接着南方宋、齐、梁、陈几个朝代更迭,其中梁末发生较大的侯景之乱; 北方十六国中脱颖而出的北魏,以及后来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朝代的更替,再加上南北方之间的争斗,在这三百多年里,几乎随时都弥漫着战争的硝烟。随着朝代的起伏跌宕,童谣也随之应运而生,故该时期的童谣多是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和对统治阶级的批判。童谣作为政治的传播工具之一,可以说就是这个时代的一面镜子。
大多数童谣之所以能够应验,这不是巧合,应是有谋略、有眼光人士对政治的远见。同时,这些童谣也不是抽象的、纯粹的猜测,而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所决定的。在动荡不安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童谣或抨击、嘲讽君王,或揭露祸国殃民的权臣,或反映人民疾苦等。可以说,该时期的童谣具有不同朝代更替的政治舆论宣传作用,因而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例如以君王为打击对象的童谣《陆凯引童谣》: “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黄龙元年( 229 年) ,孙权将国都从武昌迁到建业。到了末帝孙皓甘露元年( 265 年) 九月,西陵都督步阐上表要求迁到武昌,得到孙皓的赞同,不久开始迁都,搞得人民苦不堪言。陆凯上书孙皓,引用了这则童谣,说明迁都对人民带来的危害,希望孙皓不要违背人民的意愿,但孙皓以“建业宫不利,故避之; 西宫室宇摧朽”等为由,坚持迁都。后来孙皓又将国都从武昌重新迁回建业,这样反反复复的迁都,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又如《三国志·吴书·孙皓传》所载童谣言: “吴天子当上。”据《江表传》记载,刁玄出使蜀国,听说了司马微与刘廙谈论命运历劫之事。刁玄回国后蒙骗其国家的人说: “黄色的旗帜,紫色顶盖的车骑将会从东南方出现,而最终拥有天下的人,应该是荆州、扬州的君主。”后又抓获从中原投降的人,说寿春郡乡下有童谣唱“吴天子当上”.于是,孙皓就携带其母亲、妻子和子女还有后宫数千人,从牛诸走旱路向西出发,奔向洛阳,以顺应天命。路上遇到大雪,道路泥泞,马车陷入泥潭而坏,士兵们身穿铠甲带着武器,上百人共同拉着一辆车才能行走,冻得就要死了,士兵们不堪忍受,说“如果遇到敌人就放下武器投降”,孙浩听了,方不得已下令返回。
以权臣为嘲讽对象的童谣很多,如《襄阳童儿为山简歌》: “山公出何许? 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时时能骑马,倒着白接离。举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儿。”永嘉三年,四方叛乱,天下分崩离析,王威不振,而作为征南将军的山简却每天无所事事,只知喝酒游园,享受生活。这首童谣就描写了山简沉溺于游乐,以及醉酒后的丑态。魏晋时,重门阀不重才气,很多达官贵人没有真才实学,而有才之人却无用武之地,可以说,这首童谣既是对当时统治阶级生活腐败状态的一个缩影,又揭露了晋王朝不合理的用人制度。又如《北州童谣》: “府中赫赫,朱邱伯。十囊五囊,入枣郎。”这首童谣主要揭露了官吏贪赃枉法、大饱私囊的丑恶行径。“北州”指豳州,“府中”指豳州太守王浚的官府,“朱邱伯”指王浚豢养的权臣朱硕,他是一个苛刻贪婪的小人,“枣郎”指王浚的女婿和部下枣嵩。据《晋书·王浚传》记载,王浚掌管豳州的军政要务,其人相当飞扬跋扈,纵情于犬马声色中,其任用的官吏更是一些阿谀奉承、贪赃枉法之人,其中尤以朱硕、枣嵩最为猖獗。“府中赫赫”、“十囊五囊”分别点出了两人的本性,朱硕在王浚的庇佑下,权倾朝堂,不可一世; 而枣嵩对金钱极其看重,因而大量收刮钱财。一个小小豳州军政长官下的小吏就可以这样任意恣肆,其上司不言而明。又如《张敬儿自造童谣》: “天子在何处? 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谁? 非猪如是狗。”据《南史·张敬儿传》记载,张敬儿本名张苟( 狗儿) ,宋明帝因其名低俗,改为张敬儿,后来,其哥哥( 猪儿) 改名为张恭儿。张敬儿喜欢占卜术,尤其相信梦。“自云贵不可言。由是不自测量,无知。又使于乡里为谣言,使小儿歌曰: ‘天子在何处? 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谁? 非猪如是狗。’敬儿家在冠军,宅前有地名赤谷。”[4]
由于张敬儿贪恋权力,密谋叛乱,被宋武帝所杀。再如《齐武平元年童谣》: “狐截尾,你欲除我我除你。”这首童谣揭露了宫廷复杂的权力斗争。北齐武成帝高湛昏庸荒淫,宠信大臣和士开,并听信和士开谗言,终日沉湎酒色,不理朝政,不到一年就死了,临终还将后事嘱托给和士开,而和士开早已篡夺大权,并私通皇后胡氏。高湛死后,武成皇后胡氏的哥哥胡长仁依仗皇亲国戚的身份胡作非为、干预朝政,为此和士开将他踢出京师,贬为齐州刺史。胡长仁怀恨在心,于武平元年( 570) 四月,暗中谋划刺杀和士开,后来因走漏风声,最终借小皇帝之手被“赐死”.齐后主的弟弟高俨也对和士开不满,暗下联络一些大臣,假传圣旨要和士开到南台遣兵,和士开没有留意,去后即被擒住,由冯永洛一刀刺死。这时,冯子琮等人劝高俨趁机谋反,自立为王,被斛律光用计化解,冯子琮等人被后主亲自射杀,高俨也在打猎活动中被杀。
还有反映人民疾苦的童谣如《王恭既诛时童谣》: “昔年食麦屑,今年食鹿豆。鹿豆不可食,使我枯咙喉。”这首童谣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王恭被诛时,晋王朝内部战争不断,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人民叫苦不迭。“昔年食麦屑,今年食鹿豆”,过去还能吃上麦麸,现在连麦麸都吃不上了,只能吃野生的鹿豆了。“鹿豆不可食,使我枯咙喉”两句进一步指出生活的艰辛。
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童谣不同于其它时期的童谣就在于它多是对统治阶级或者是政治事件的评判,而很少有直接反应人民疾苦的童谣,究其根源,我们认为,这还是由当时严峻的政治环境决定的。尽管童谣在儿童的嬉戏中传唱,但传播的内容却是敏感的政治话题,而且当时有法律明文规定禁止妖言的传播,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童谣近似妖言,因而当时的童谣也深受其害,《魏书·高祖孝文帝纪上》: “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密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着以大辟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