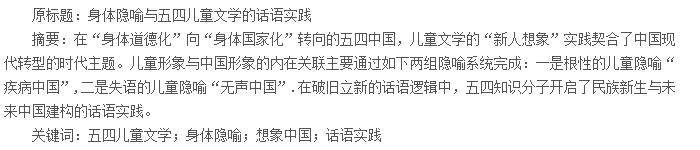
在传统中国,道德对身体的规训使人无法承受“身体道德化”之重。严苛的“修身”过程主要集中在身体的“洁化”问题上,而对于身体之外的民族、国家等问题则付之阙如。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将身体理解为一种想象民族国家的象征性符码。身体的意义来源于其与精神的复杂关联,没有脱离精神而在的身体,也没有离弃身体而在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身体”表征着主体,身体铭刻着历史主体性文化锻造的印记,所有的精神、情感状态最终回归着相应的身体状态。“所有的身体状态都存在着一种精神要素,而同样,所有的精神状态都存在着身体因素”.
可以说,身体不是精神之外的世俗化的肉体,而是生命的本体;不是被动的利用对象,而是可以视为隐喻历史和现实存在的话语载体,并在话语实践的场域中不断被赋予精神化的意义。在五四儿童文学的现代性框架内,儿童作为一个要被解放的群体,成为知识分子“新人想象”的载体,这是晚清以来“救国救种”意识的延续和突破。对儿童身体的审视,集中体现了他们想象未来民族国家的话语实践。
一、“根性的儿童”:疾病中国的隐喻
在五四中国,“身”与“心”紧密相联,一脉相通。先觉者所倡导的“人的解放”包含着以上两个方面的维度。身体成为他们进行言说“人”个性解放、主体精神的重要载体。尽管“身”与“心”之于人的个性解放来说有着相同的诉求,然而,很多知识分子还是更为强调“心”(“精神”),更加重视从思想革命的角度来改造国民性。即如周作人所说:“儿童的身体还没有安全保障,哪里说得到精神?”
对于儿童“身体”的关注和思考也自觉纳入了知识分子“身体政治化”、“身体国家化”的话语体系之中。与妇女相似的是,儿童长期被忽略的身份和价值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范畴改变了中国新文学中性别、伦理、社会及政治想象。
到五四时期,当一些作家自觉将儿童与社会使命或未来国家进行关联时,“新儿童”与“旧儿童”身体的区别就很明显了。叶圣陶的童话《小白船》将儿童书写成为纯洁至美的精灵,“小白船”与儿童是彼此匹配的:“小溪的右岸停着一条小小的船。这是一条很可爱的小船,船身是白的,它的舵和桨,它的帆,也都是白的,形状像一支梭子,又狭又长。胖子是不配乘这条船的。胖子一跨上船,船身一侧,就掉进水里去了。老人也不配乘这条船。老人脸色黝黑,额角上布满了皱纹,坐在小船上,被美丽的白色一衬托,老人会羞得没处躲藏了。这条小船只配给活泼美丽的小孩儿乘。”
“小白船”只是一个隐喻美丽小孩儿的载体。“胖子”和“老人”的身体与“小白船”不协调,因为它只属于活泼美丽的小孩儿。在这里,“小白船”这个意象所隐喻的希望是叶圣陶早期童话的重要精神象征,这艘美丽的船更可寓意为建设“中国童话家园”的介质,它“运载一批人文知识分子行动在营建这篇美丽家园的劳作中”.
叶圣陶将儿童与成人(“胖子”和“老人”)的身体进行了比照,两者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而儿童与“小白船”却非常地契合协调,它们似乎是一个整体,天然亲近,“小白船稳稳地载着他们两个,略微摆了两下,好像有点骄傲”.
尽管冰心、丰子恺、郑振铎等人均有对儿童身体的赞美篇章,但是,更多的知识分子却将其描绘得并非完美和康健,沾染了“老中国”的病态。沿用“民族寓言”的解读策略,这种病态的儿童身体实际上为五四知识分子的启蒙实践拓展了“用武之地”.在这方面,鲁迅的儿童书写最具代表性,值得深入探究。鲁迅意识到儿童之于未来的重要性,然而,他对于生活于“黑色染缸”土壤中的儿童怀着深深的警惕和担忧。他的“救救孩子”是基于“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因此,还没有深受环境污染,有着优良的种性的孩子才是鲁迅的希望所在。然而,这样的孩子几乎很难找到。在他笔下,我们能看到很多病态儿童,他们与外国儿童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一到大路上,映进眼帘来的却只是轩昂活泼地玩着走着的外国孩子,中国的儿童儿乎看不见了。但也并非没有,只因为衣裤郎当,精神萎靡,被别人压得像影子一样,不能醒目了。”
“公园里面,外国孩子聚沙成为圆堆,横插上两条短树干,这明明是在创造铁甲炮车了,而中国孩子是青白的,瘦瘦的脸,躲在大人的背后,羞怯的,惊异的看着,身上穿着一件斯文之极的长衫。”
德里达认为:“不存在中性的二元对立组,二元中的一极通常处于支配地位,是把另一极纳入自己操作领域中的一极,二元对立的各极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
在鲁迅呈示的中日儿童的差异对照中,人们能根据差异建构起自我认同和对这种文化差异的强大震撼感。显然,那种精神萎靡,躲在大人背后的中国儿童是五四现实中国的写照,鲁迅用一种“挞丑”的方式将儿童的身体及精神构图生动地书写出来,成为其反思社会和人的重要途径。
在五四儿童作家笔下,由于贫困、饥饿,儿童的身体呈现出病态的形态,没有生机,缺乏生命力,为当时的中国现状作了很形象的脚注:“她面色是洁白的,而看去却像带有病色,因为她并不像其他的女孩子有红润的腮颊”(王统照《纪梦》);“那女人怀中抱着一个病势十分沉重的五岁来大的小孩……仿佛一只小鸟中了弹子将要毙命时那种最后的哀鸣”(孙俍工《隔绝的世界》);“有几个小孩子,中间有一个,也不过十来岁大,穿身黑衣衫,而面貌愁苦,看去好像很明白世故的老年妇女,她整天忙着,早晨很早,就可以见着她,凡孩子们的勾当,都没有她”(徐玉诺《认清我们的敌人》);“我愈是不想看,那双手便愈加明显地呈在我的眼前。它们很黝黑,好像是从炭堆里掘出来。
平常人的手都是很平坦的,但它们却浮肿得好似两座小坟墓”(赵景深:《红肿的手》)。无论是面目憔悴、眼神无光,还是少年老成的儿童,都是特殊语境中的产物,作家书写了各类形形色色的儿童形象,对其病相的文学表达体现了他们对“旧中国”儿童群体的伦理关怀及独特的社会批判立场,其精神指向则是儿童所栖身的文化土壤和中国情境。
死亡意味着身体的退场。由于长期的父权思想及中国现实环境的重压,儿童成为成人世界的牺牲品,被无情地吞噬:“狂人”的小妹被吃(鲁迅《狂人日记》);华小栓得了肺痨未痊愈死去(鲁迅《药》);单四嫂子的宝儿被庸医稀里糊涂误死(鲁迅《明天》);祥林嫂的儿子被狼吃掉(鲁迅《祝福》);桂儿得了白喉医治无效(吴立模《猫鸣声中》);雨冲倒后墙压死的弟弟(杨振声《渔家》);被婆婆狠打而死的翠儿(冰心《最后的安息》);不幸中弹而亡的三儿(冰心《三儿》);旧历除夕晚上得病而死的马夫的儿子(孙俍工《隔绝的世界》);受惊吓而死的小学生怡萱(冰心《是谁断送了你》);被疯狗咬死的阿成哥(王鲁彦《童年的悲哀》)。
“死亡”是五四儿童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事情,如饿死、冻死、病死等场景俯拾皆是,这与中国近代的危机有着极大的关联,面对着创痛巨深的中国,成人作家用失败、屈辱和可能注定灭顶之灾命运的身体化意象来隐喻中国的现实遭遇。于是,在五四儿童文学作品中,高频率出现的“死亡身体”就不是偶然的了。与此同时,它与中国历史一贯的“吃人”行为还构成了互文性印证。鲁迅将中国的文明比作“人肉的筵席”,“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女人和小孩”.更为残忍的是,在这个“人肉筵席”中存活的儿童也有与成人相似的国民“劣根性”.对孩子“劣根性”的反思体现了鲁迅思想启蒙的深刻性。在他的小说中,孩子不仅继续充当着麻木的“看客”,拼命挤进人群“欣赏”革命先驱被残忍杀害的过程,他们像“用力掷在墙上而又拨过来的皮球一般”飞奔到热闹的围观者中间,在人群中钻来钻去,与成人一起构成庞大的看客群体(《示众》)。更为可悲的是,为了生存,他们无意识地站到了“吃人者”的行列中。
《药》中,已病入膏肓的少年华小栓,为了“治病”竟然不自觉中成了“吃人”的人,“他撮起这黑东西(人血馒头),看了一会,似乎拿了自己的性命一般,心里说不出的奇怪”,他是一个被动的“吃人者”,本能和父母的安排让他无法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正确与否,“不多功夫,已经全在肚子里了,却全忘了什么味”.这种劣根性维护了中国“铁屋子”秩序的稳定、恒久,也是其无法撼动“主-奴”社会的内在缘由。这些儿童与病态成人无异,他们没有个体意识,也不需要个体意识,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用肉食者的意识来处理自己面临的现实问题。
身体作为生命的本体,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理现实。它从外在与内在两个向度参与了社会对人的规定。联系这些儿童的存在境域不难发现他们的病相多是外在社会的重压所致。作家们对这类儿童身体的叙述,主要通过社会、家庭的人际关系来达到社会反思及儿童生命意识书写的符号指意功能。
二、“失语的儿童”:无声中国的隐喻
五四知识分子基于启蒙所发出的呐喊是有方向的,欲其“声出而天下昭苏”、“震人间世,使之瞿然”.“会说”、“能说”是表征一个人存在的途径之一,“沉默”和“失语”则意味着一个人失去了话语权,只能被动地为他人牵着鼻子,亦步亦趋地按他人意志行事。依此逻辑,五四强调彰显“人”的意识也就要求他们拥有自己的“说话”的权利,并且这种声音能表情达意地显示自我的存在及意义,否则“人”的解放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因此,对于儿童而言,他们必须在与成人的对话过程中将自己的意愿及思想传达出来,同时,通过这种言说呈示个人的精神内涵。
可以说,启蒙者的发声是希望有聆听者,有接受者的。他们希望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能发出自己的心音。如果只有朝向群体的附和之声,那么人的“个人性”将在群体的同声中受到遮蔽和湮没。然而,在五四儿童文学作品中,很多儿童丧失了语言表达的自主意愿,要么沉默,要么以一种近乎无效的话语存在。即使有意言说和参与讨论,也被一种强大力量所压制,而成为被动的倾听者。
显然,这种失语意味着主体丧失了表达自我的能力,其主体价值也就无从谈起。具体而论,儿童的失语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基于精神世界的不健全,儿童不愿说。“儿童不愿说”是基于人的精神品格而言的,儿童作为人的精神品格基本具备,由于长时期历史的惰力,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进化而消失,而是始终停留在占大多数的愚昧民众(包括儿童)的潜意识中,所以一旦要他们表达有异于既定习惯和范式的个人愿望时,他们的困境就可想而知了。
王统照的《纪梦》书写了一个被称为“活哑巴”的小女孩,“她寡于言语,又似懒于言语。她每天来到教室,安闲从容,绝不似他人的忙乱,有时连上四班的功课,她可以一次也不离开座位。可是她的功课却不见得答得完全”.她很少和其他同学交流,“在一群欢乐的女孩子中她是孤寂的、落寞的,如同从远处跑来的一个陌生人”.为了彰显她的孤僻和沉默,王统照刻意书写了一群欢声笑语的女孩子与之对照,“她们都如春日园林中的小鸟,一切都是随意的,自然的,没有拘束也没有恐怖”.与此同时,作家意味深长地为她们的作文课设计了一个可以自由想象的题目---“纪梦”,于是,学生们的思维被打开,丰富的联想和连绵的回忆由此展开。“活哑巴”和其他同学的区别也因此被放大。经过一番酝酿后,很多孩子用语言描绘了他们游历梦境的过程。上述心理是正常儿童该有的情思反应,是激活儿童梦想及记忆的重要途径。然而,就是这个寡言少语的“活哑巴”却陷入了无从下手的复杂情绪之中:“她自见出题之后,望了望黑板上的大字,仍然将脸左向,侧望着绿色的墙壁。先生如何解释题目,她是一个字也没听清的。乃至她的同学们都在执笔构思的当儿,她又回头望了那”纪梦“两个字,便伏在案子上不动了。墨盒儿没有开,毛笔还是安闲地方在一边,她的肩背却时时耸动。”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呢?原来她沉默的背后有着特殊的个人隐忧和痛苦,因为环境的威迫,她被父母当质押品做了陌生老太太的童养媳。老太太每见到她就会骂她“不长进的畜类……不是我养的”这类话。
因此,老师出的作文题目,使她想起了自己经过的艰难岁月。然而,对于这种深深嵌入其脑海的回忆,“总难有抒写出来的机会,而且她又哪里有勇气来写;她想自己的苦梦,不知哪天才做得完,又如何写得出”.作者的话意味深长,道出了社会空间和时代语境给予儿童身心造成的痛苦烙印,儿童不愿也不能反抗的心路历程。
在这方面,叶圣陶笔下的几个失语的儿童形象也很有代表性。在《阿凤》中,阿凤是个童养媳,对于婆婆给予的一切诅咒和打骂,她的态度是“牙一咬紧,眼睛一紧闭---再张开时泪如泉涌了”.待到婆婆转身,她的“红润的面庞又现出笑容了”.这种随遇而安的处事姿态道出了她缺乏反抗意识,默默接受别人给予人生安排的命运。《小铜匠》中的根元生活于单亲家庭,母亲依靠劈竹做扫帚维持生活,经历无钱上学到母亲病逝的磨难后,根元的脸面慢慢变得没有表情,也没有了语言,什么事都只能“愚蠢地摇着头”说不知道,终日以“懦怯的心”过活,当他的母亲去世时,“他还是绝不伤心”.
叶圣陶以一种悲悯的同情观照这样一个病态儿童的心理状况,将批判的对象指向了当时特殊的社会语境及人际关系。在另一篇小说《阿菊》中,叶氏更是将失语的儿童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阿菊生活在一个破败的家庭里,为了生存,父母艰难地劳作着,没有任何时间余暇来关注阿菊的成长。八岁的阿菊“除了一间屋子和门前的一段街道,他没有境遇;除了行人的歌声,他没有听闻;除了母亲,他没有伴侣,---父亲只伴他睡眠;他只有个很狭窄的世界”.正是这种狭小而单调的生活空间制约了阿菊生理和心理的发展,他的一举一动中呈示出愚呆、寡言、怯懦的形象。入学后,当女教师问他的名字,他竟“全然无法应付”,一言不发后“不绝地涌出泪来”.在嬉闹的操场上,他觉得这里不是安稳的地方,于是“两脚尽往后退,直到背心靠住了墙才止,他回转身来,抚摩那淡青色的墙壁,额角也抵住在上边,像要将小身躯钻进去”.
这种无声的表达体现了阿菊无法适应社会,艰难地徘徊于个人狭小世界的痛苦境地。
有感于国民沉默的精神弊病,鲁迅呼吁知识分子应发出“雄声”、“至诚之声”,以培养善美刚健的国民。鲁迅笔下的儿童常以沉默者的形象出现:《药》中的小栓是几乎没有言语的,留给读者的印象只是他不住咳嗽的样子。《明天》中的宝儿也是没有活泼的生命气象的,没有言语,悄悄地死去。这些儿童之所以让人同情,是因为生命之花还没绽放就已凋零。《示众》中卖包子的胖孩子和戴雪白小布帽的小学生,他们没有语言,在其麻木的灵魂下只剩下光秃秃的躯体,他们一看到示众者就“像用力掷在墙上而反拨过来的皮球一般”飞奔上前,他们的冷漠与麻木同样成为“被示众”的对象,与周围拥有国民劣根性的成年看客形象毫无二致。在鲁迅的意识中,这些失语的儿童只是一些可怜的生物,他们没有自我意识,没有生存的希望,其无言的行为确证了人性的悲凉。徐兰君将鲁迅笔下那些没有成长的希望,从来没有自己的声音的儿童形象定义为“鬼魅儿童”.她提出了一个问题:“虽然鲁迅一再赞美儿童的力量,强调儿童/成人的价值秩序,然而,儿童的解放却似乎端赖成人的行动,那么究竟儿童是救国的主体,还是无力的待救者?”这一反问颇有深意,切中了鲁迅对于儿童问题思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但是,在鲁迅复杂体验里潮涌发酵的,依然是未来中国的忧思以及强民救国的凝眸。儿童可以成为救国的主体,是鲁迅“内的努力”和进化观念的体现。但是,儿童身上有着对成人无法割舍的依赖性,这也限制了其力量的施展。一旦他们被“酱”
入成人的“黑色染缸”而无力自救时,他们也就成为了待救者。儿童的这种状态使鲁迅“救救孩子”的启蒙工程陷入了困境之中,也预示了五四知识分子“儿童救国”方案的艰难历程。
二是基于强势话语的压制,儿童不能说。“儿童不能说”主要是基于人的生存境域而言的,当儿童具备言说能力却遭遇外界强大的重压时,其言说功能散失。在五四的情境里,儿童对自己的人格价值和社会角色还缺乏稳定的评定原则,还未具备廓清自主与自发、主动与被动的能力。当无力冲破文化他者制造的障碍和控制时,他们只能承受无从获致自我价值的精神危机。选择沉默,也许是最好的办法。儿童不愿意将个人的诉求和欲望公之于众,体现了他们面对外界压力的妥协状态,一边是自我社会角色意识的丧失和分裂,一边是情理的两难与纠葛。在不断滋生、蔓延的虚弱无力的自我体认下,夹在被动的现实选择和不自主的情思反应之间,儿童言说能力的丧失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杨振声的《渔家》中,王茂的女儿看到警察来抓她的父亲时,“原是哭着的,后来看见那警察来了,她便吓得跑到她母亲的背后,一声也不敢哭了”.对于一个孩子而言,无声的“哭”是其面对恐惧的最为直观及真实的反应,这种沉默表征了小女孩的无助与无奈。他的《风筝》刻画了一个多病、瘦得不堪的“我的小兄弟”,他是喜欢风筝的,但作为兄长的“我”向来不爱放风筝,认为是没有出息孩子所做的玩意儿,当“我”发现他尘封的什物堆中装饰和糊着风筝时,我伸手折断了风筝的一支翅骨,将风轮掷在地上踏扁时,他“只能绝望地站在小屋里”,一句话不敢说。造成他失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论长幼,论力气,他是敌不过我的”.
那么,如果主体有“语言”的产生(“发声”)就能完成“言语”的实践吗?显然没有这么简单,五四儿童作家似乎有意设置了“言”与“意”的距离和隔膜。儿童即使有言说行为的产生,但成人话语的遏制使其无法自由、真实地传达自我的思想及想法,因此也就变成无效的语言,同样归于失语。
可以说,当现存的语言无法表达他自己正在生成的体验,儿童言说功能的缺失表征其失去了提供存在状态信息的能力,成为无所知的存在境遇中没有身份指向、没有价值取向的人。在程生的《白旗子》中,当二儿告知母亲日本人占领中国的青岛,中国要亡了时,母亲自觉地将儿童从政治时局的参与中析离出来,她说:“蠢孩子,那与你有什么相干哩”,“哪儿来的话,你不要听他们野扯”.其父亲回来更是大骂,“我看这班学生,真是无法无天,现任的总长---公使---总裁---都敢如此地骂,还成世界吗”.在他看来,儿童根本不懂得国家大事,在他的打骂下,两个儿子只能“撅着张小嘴,一声儿不响”,等待他们的是不准上学堂,掷在家里念书的命运。在这场对话中,父母的声音占了上风,他们用强势的话语扼杀了儿子从学堂获得的现代话语的权利。由此,他们生活在同一的逻辑经验世界里,自以为身处和谐、澄明之中,但存在之真的多样性已被遮蔽。同样,在《两个小学生》中,庐隐书写了一个母亲对于学生参加请愿这件事的看法,她认为:“这么点小孩子,也学管那些事;请什么愿?倘若闯出祸来,岂不是白吃亏吗?没的吓得爹娘的心都碎了。”旁人也认为:“哎,这些孩子们,永远不肯听话!他们的任性,只是苦了无数做母亲的心!”
在成人的意识中,儿童是未成年人,他们没必要和一个未成年人谈论他们意定的事情,由此以来,儿童的话变得不可理解也不可理喻,变成无效的语言。成人不再愿意与儿童进行交流。基于此,共同语言根本不存在,或者说不再有共同语言。在这些篇什中,儿童作为成人眼中异己的力量,使得成人在压制儿童的过程中,运用了祛除声音的强制手段,目的是“不让周围的人同他交流,让周围的人对谵妄病人的自由呼喊、高亢表演无动于衷,保持沉默”,其结果导致言说主体与倾听客体之间的关系被斩断,因此,儿童微弱的自我认知在强大的他者的话语权威下只能通过“独白”、退回内心的方式来表现。
正如德里达所言,人的行为取向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沉默一言不发;要么跟着疯子跑到他的流亡之路上去。”
可以这样理解,人要么保持沉默,与常人所在的习惯、秩序保持一致;反之,如果人站在常人的对立面,就一定要表达和言说自我,哪怕他的言说在常人看来和疯子所说无异。
在成人的眼中,儿童的“越轨”及“反抗”无异于疯子所为,是不符合日常习惯,甚至是不孝或不道德的。这即是说,儿童所发出的声音如果与成人所期待和允许的一致,就是合法的、可以通行的语言;反之,则是违背常规且非法的,是不允许流通的。这样一来,儿童如果和成人的话语保持一致,就丧失和遮蔽了自我的话语;如果和成人的话语相冲突,就会遭致成人的剿杀和包围,最终失去自己的声音。因此,只有打破沉默,并且言说个人的声音才能彰显儿童主体的存在。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其道理是一致的。这也成为五四儿童文学想象中国的理论根源。
三、民族新生与“未来中国”的建构
“未来中国”的儿童形象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负重-超越”的心境下的产物,作为一种集体的想象物,它被视为“民族隐喻”机制,发挥着汇聚民族气度的话语功能。郑振铎于1919年11月1日创作的儿歌《我是少年》延续了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那种将少年儿童与未来国家比照的传统。这首诗颂扬了少年儿童所具有的现代品格:“我有如炬的眼,我有思想的泉。我有牺牲的精神,我有自由不可损,”他们强大的主体意识来自于不可泯灭的“人”的自由意志及打破成规旧俗的勇气,“我过不惯偶像似地流年,我过不惯奴隶的苟安。我起!
我起!我欲打破一切的威权”.在这里,“我”拥有着不愿重复过去的心智,这种心智催生出充沛的生命强力支撑着主体勇敢向前:“我有沸腾的热血和活泼进去的气象。我欲进前!进前!进前!”正是基于这种“进前”的冲动和伟力,“我”能抵挡住“浊浪排空,狂飙肆虐”,才能“看见前面的光明”.
可以说,这首儿歌所体现的精神和五四的时代精神是非常契合的,那种打破偶像及确立自我价值的精神在儿童身上十分贴切地呈示出来。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由于古典型国家的权利效能对社会空间统治的有限性,在社会生活中道德与习俗是起着决定力量的控制体系,因而“在古典型国家向现代性民族国家的权利转型中,道德问题总是被突出出来”.
这即是说,某个社会生活中道德状况的变动是与国家类型的转换“表征”密切相关的。郭沫若的童话剧《黎明》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之作,该剧的开篇呈现的是一个浑浊不明、苍莽原始的背景:“海影朦胧。呈现出一种凄惨可怕的颜色。海涛狂暴依然。大海中恍惚有座孤岛”.
这是预设自明的一个文化背景,暗示着一个秩序混乱、中心颠覆的“多语”格局和隐隐新生的胎动,是转型和创世的文化先兆。换言之,这种天地相含混、晦冥萧瑟的背景隐喻了社会变动的文化信息。与此同时,黎明曙光、初生太阳出现了,“曙光渐渐浓厚,颜色渐渐转青”,“太阳出海,如火烧天壁,万道光霞齐射”.一对先觉儿女在此情境中出场了,他们是作家憧憬中国未来和新生的符号:“脱了壳的蝉虫”、“出了笼的飞鸟”、“才出胎的羚羊”、“才发芽的春草”.他们唱歌、跳舞,是天宇中的精灵,他们“好像这黎明时候的太阳!”“好像这黎明时候的海洋!”在这里,旧时代为新生力量取代也不可避免,这对儿女有“涤荡去一些尘垢秕糠”,破除旧时代的使命感,他们也有创造一个新世界的自豪感,他们诅咒一切桎梏人自由发展的“囚笼”、“幽宫”,决定与宇宙中的一切生灵去“制造出一些明耀辉光”、“从新制造出一个大洋”.共同欢庆“天地的新生”、“海日的新造”.在他们的召唤下,藏禁于“幽宫”和“囚笼”的弟兄、姊妹被唤醒了,“加入了这一场黎明到来的节日仪式之中”.
这对先觉儿女用一种狂欢的方式迎接着新太阳的出现(“加冕仪式”):在曙光初现的孤岛,一群儿女放声高唱,他们尽情舞蹈,“跪向太阳祷告,跪向太阳祈祷”.与此同时,旧体制、旧时代在他们的狂欢里黯然地谢幕(“脱冕”)了,“我们唱着凯歌,来给你们送终”.儿女们在高涨的“更生”、“新生”中达至了生命酩酊状态,得到的是一种狂欢的新生快感,“我们将永远同你断线。我们唱着凯歌凯旋”.
在“道德中国”里,父亲借助传统文化的力量树立其权威者的地位,儿童要从这种压制性的权威或僵化的权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必须有对个体生命自觉的认识以及对生命资源有理性的自知。权威者合法性的获得来自于服膺者的认同,“主人只有当奴隶允许他做主人的时候,才是一个主人”.换言之,人的身份确认往往和人与人之间的权力话语同源同构。林毓生在讨论五四1威“与”压制性的权威“之别,在他看来,前者是真权威,而后者是假权威。人的自由精神的确立源自人对于”压制性的权威“的批判,然后培育与建立外在自由与内在自由所需要的”心安理得的权威“.
运用在父与子的对峙过程中,父亲有使儿女服膺的力量,这种服膺是出自服膺者心甘情愿的意愿,否则他们服膺的便不是真的权威。
一旦儿女不认同父亲的权威,父亲的权威身份就会遭致质疑与挑战。这种质疑与挑战体现了儿女自由意识的生成,有助于培养儿女建构新的真正权威的话语实践。可见,子女的自由、进步等意识的生成本源于有形的或无形的父辈权威的威胁与压迫,他们新质的体现也来自于对父辈批判与蜕变过程,为”道德中国“向”未来中国“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精神保障。
总而言之,儿童是未来的隐喻,儿童的发现开启了中国儿童文学对于未来中国及民族”新生“的思考。借助儿童视角来建构中国形象,将儿童这一主体与现代民族国家的设想紧密联系在一起。
构建中国形象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内在诉求,不是中国儿童文学的”越位“或自我消解,而是它的”本位“和拓展。借助儿童视角来建构中国形象,体现了一种”经验世界“的情感和想象空间的精神化呈现,其性质是对现代中国的一种价值重建与意义重构。正是在批判”以长者为本位“思想的基础上,五四知识分子开启了对”以幼者为本位“思想的探寻和反思。当然,他们没有简化人性的复杂性、深刻性,也没有将儿童神化为”未来中国“的能指符码,既发掘其身上的现代品质,又鞭挞其与成人一致的根性,在”破“与”立“的逻辑框架中,开启儿童想象中国的话语实践。
参考文献:
[1]安德鲁·斯特拉桑。身体思想[M].王业伟,赵国新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2]周作人。关于儿童的书[M]∥周作人论儿童文学。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
[3]浦漫汀。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童话(一)[C].太原:希望出版社,2009.
[4]陈桃兰。从”忽视儿童“到”儿童为本“---现代小说里中国儿童教育观念的变革[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5]鲁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徐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