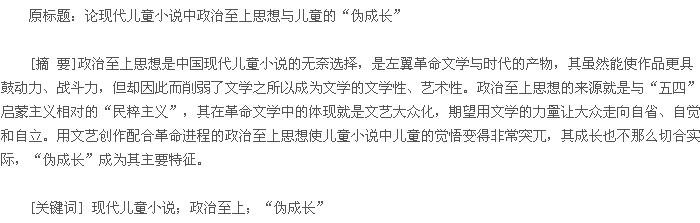
“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后,启蒙的任务已经结束,至于启蒙的结果是否达到了这些思想先行者们所预想的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中国儿童文学一直与时代发展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当历史进入到下一个发展阶段后,中国儿童文学即使没有完成启蒙任务,也会跟随时代的脚步匆忙前行。1925年开始的大革命最终还是因在国民革命中势力壮大起来并背叛革命的蒋介石以及随着革命形势发展转而走向反动的汪精卫两人而以失败告终,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使得1927年后的中国社会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而紧密跟随时代发展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儿童文学也随之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格局。
一、政治至上思想的形成与来源
王泉根曾明确指出中国儿童文学在这一时期所出现的两种倾向:“一是倒退的倾向,一是激进的倾向。……1930年前后的中国儿童文学在对自身价值功能的选择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性时刻。
这一选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右翼势力试图让儿童文学‘羽翼传经’重开历史倒车的逆流遭到了批判,儿童文学的文学地位、现代精神与艺术个性进一步得到了巩固与加强;另一方面,左翼文坛则从阶级斗争、民族振兴的角度出发,要求儿童文学与整个左翼文学一样注入‘革命范式’的理想主义激情,强化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革命的关系。”的确是这样的,这两种倾向在大革命失败后直接交锋,引发了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着名的“鸟言兽语之争”。大致的经过是这样的:1931 年 3 月 5日,上海《申报》发表了湖南省主席何键的《咨请教育部改良学校课程》一文,认为:“民八以前,各学校国文课本,犹有文理;近日课本,每每‘狗说’、‘猪说’、‘鸭子说’,以及‘猫小姐’、‘狗大哥’、‘牛公公’之词,充溢行间,禽兽能作人言,尊称加诸兽类,鄙俚怪诞,莫可言状。
尤有一种荒谬之说,如‘爸爸,你天天帮人造屋,自己没有屋住。’又如‘我的拳头大,臂膀粗’等语。不啻鼓吹共产,引诱暴行,青年性根未能坚定,往往被其蛊惑。
此种书籍,若其散布学校,列为课程,是一面铲除有形之共党,一方面仍制造大多数无形之共党。虽日言铲共,又奚益耶?”并说此类儿童读物与教科书“不切实用,切宜焚毁”,认为“查改良课本,为现时切要之图”。
随后,支持何键观点的初等教育专家尚仲衣的《选择儿童读物的标准》与反对何键观点的吴研因的《致儿童教育社社员讨论儿童读物的一封信———应否用鸟言兽语的故事》两文针锋相对并以二人为主要辩手引发大规模论争。陈鹤琴、魏冰心、张匡等教育家和作家也参加了讨论,其中鲁迅在 1931 年 4 月 1 日写的《〈勇敢的约翰〉校后记》中,批判何键的“高见”是“杞人之虑”,指出童话的作用对儿童是“有益无害”的。可以说,这场论争席卷了整个中国教育界和儿童文学界,最终的结果是有力地反击了儿童文学领域的复辟倒退现象。但正如王泉根教授所言,中国儿童文学在这个时候要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巩固和加强儿童文学的文学地位、现代精神与艺术个性,使得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更加符合文学的本质;另一个则是配合左翼文学,使文学成为时代与革命的宣传手段。
很显然,在左翼文学渐成主流的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儿童文学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左翼文学的政治至上思想左右了当时的整个文坛,儿童文学也无法置身事外,令人无奈的是,选择了后者虽然能使作品更具鼓动力、战斗力,但却因此而削弱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文学性、艺术性。
其实,这种政治至上思想的来源就是与“五四”启蒙主义相对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或民粹派源于俄语HapogHuIOcmto,英语为 Populism,也可译为“人民主义”、“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 Elitism 相对。这个概念起源于法国,命名却在俄国,19 世纪中期以后,别林斯基、杜勃罗留夫、克鲁鲍特金等人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主张知识分子走向乡村,发动农民以反抗俄国的资本主义化;有人则提出平民主义要求,主张知识分子向农民学习,走“身份同化”的道路,这与马克思主义启蒙鼓动劳动者的价值取向正好相反,当然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反驳。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对 19 世纪俄国受民粹主义影响的“平民知识分子的民主文学”的描述是非常准确的,他认为“这派作家都有一种无力感,都感觉到自身力量的渺小”,“这种对自己的社会脆弱性的感觉,激发了俄国作家注意到人民,感到他们必须唤起人民的潜在力量,并且把这力量化为夺取政权的积极的思想武器。也正是这种无力感,使得绝大多数俄国作家成为激烈的政治煽动者,他们千方百计阿谀人民,时而讨好农民,时而奉承工人”。
这种“无力感”正是民粹主义出现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源。中国的五四运动之初,民粹主义就即时登上了历史舞台。1918年 11 月 16 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致辞中说道:“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做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随后,李大钊在一次集会演讲中说道:“我们要先在世界上当一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工人,诸位呀!快去做工啊!”
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视为劳工的胜利和庶民的胜利。从此,民粹主义同启蒙主义一样,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潮。政治上的“平民政治”、教育上的“平民教育”、文学上的“平民文学”等等都是民粹主义的直接体现,如“平民文学……是在讲究全体的生活,如何能够改进到正当的方向”,“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换句话说,民粹主义的阶级观就是把劳工或平民的问题都归咎于统治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上,而“平民主义”就是一种冲破统治阶级强权的解放行为。毛泽东曾评价过这种解放式平民观,他认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谟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上的强权,文学上的强权,政治上的强权,社会上的强权,教育上的强权,经济上的强权,思想上的强权,国际上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们打倒。”
的确是这样的,在打倒强权上,民粹主义与启蒙主义又交合在了一起,二者既矛盾又有统一,相互纠缠,深深地影响着那一代思想家和作家们。
二、政治至上思想下的儿童“伪成长”
说到政治至上思想就不得不提鲁迅,因为他也是这种思想的接受者和践行者。鲁迅正是感到了自身力量的渺小和当时中国社会的脆弱性,使他的内心无比愤懑与寂寞,“那在寂寞中奔驰的勇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他才用一生去呐喊,既想喊醒那些沉睡的民众,又想成为民众的一员,启蒙与民粹的矛盾纠结,其最终目的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获得大众(平民)的巨大力量,打倒强权以建设一个全新的世界。
虽然鲁迅在种种惨烈的社会实践与革命斗争中,对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和中国革命的进程越来越不抱有希望,甚至是绝望,但鲁迅毕竟是中国新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他与其弟周作人对“平民主义”的接受和传承还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后,“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就从未停止过,直到革命文学兴起时终于达到了一个高潮。
民粹主义在革命文学中的体现就是文艺大众化,期望用文学的力量让大众走向自省、自觉和自立。但让人想象不到的是随着革命进程的深入,革命文学开始出现功利性、口语性、概念化、程式化的倾向并愈演愈烈,本来是文学描写对象的大众从客体摇身一变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体,要求文学迎合大众并由大众自己来创作,原本的创作主体知识分子则被客体化了。
在之后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中,郭沫若甚至指出大众文艺“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你不要丢开大众,你不要丢开无产大众”,这种偏颇的观点实际上已经将文学推向了政治、革命的附属物了,政治至上、革命至上的思想由此而来。刚刚“独立”的儿童文学也无法幸免。
1930 年 3 月底,左联成立不久后,《大众文艺》便组织了一次关于如何办好《少年大众》的讨论会,与会的沈起予、华汉、田汉、钱杏邨、洪灵菲、冯乃超、蒋光慈、白薇等18 位左翼作家参与了讨论并指出:儿童文学应“给少年们以阶级的认识,帮助并鼓动他们,使他们了解并参加斗争之必要,组织之必要”;在“题材方面应该容纳讽刺,暴露,鼓动,教育等几种”“,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富于宣传性和鼓动性的文字、插图等样式,来形成他们先入的观念,……竭力和一切革命的斗争配合起来。”(这次座谈会的全文发表于 1930 年 5 月《大众文艺》第 2 卷第 4 期)“鼓动”几乎成为了这次讨论会的关键词,可见这些左翼作家对儿童文学的政治功能性的看重是空前的。并且,这些作家在实际创作中也以此为准则,尽全力配合革命进程。
就儿童小说而言有冯铿的《小阿强》、胡也频的《黑骨头》、张天翼的《小彼得》、陈伯吹的《华家的儿子》、洪灵菲的《女孩》、草明的《小玲妹》、沙汀的《码头上》、鲁彦的《童年的悲哀》、茅盾的《大鼻子的故事》、叶圣陶的《一个练习生》、戴平万的《小丰》、阿英的《小林禽》、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艾芜的《爸爸》、宋之的的《忌日》等,其中,尤以茅盾和叶圣陶的儿童小说最具代表性,在政治至上思想的影响下,小说中儿童的觉悟变得非常突兀,其成长也不那么切合实际,给人一种虚假的感觉,我将之称为“伪成长”。
对于这样的“伪成长”,鲁迅不但深知其思想根源,更是对其危害有着极为直观且惨痛的认识。1927 年,鲁迅在广州亲历“四一五”政变,让其深深地感受到了真正的“恐怖”,“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在这种严酷的阶级斗争的现实中,鲁迅敏感地觉察到中国青年的成长出了问题。
由于受到进化论的深刻影响,鲁迅把国家的未来完全寄希望于正在茁壮成长的青年一代,“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现在,青年必胜于老人”,他认为,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熏陶和教育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必然会为新世界的建立而奋起抗争、殚精竭虑,“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
当鲁迅看到那些在他看来本应已经具备了强烈革命意识和坚定革命信仰的青年们在威逼、利诱下竟然背叛了革命,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这让鲁迅痛心疾首,直到此时,他才真正意识到中国青年的成长一直都是病态的,其中的某些人表面上看来因新文化运动的刺激而意气风发、蓬勃向上,但内里却因为老一辈革命先驱们的拔苗助长、自以为是而糟朽不堪,稍经考验就原形毕露。鲁迅的亲身经历使他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为此极力奔走呼号,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也能够正视这种不健康的“伪成长”。
三、现代儿童小说中儿童“伪成长”的个案分析茅盾的
《儿子开会去了》(原载于《光明》半月刊第1 卷第 1 号,1936 年 6 月 10 日。原题为《儿子去开会去了》,解放后收入《茅盾文集》第 8 卷,改为现名),这篇小说很显然是为了纪念五卅运动的,小说以一个13 岁的小学生阿向去参加五卅运动纪念游行为主线,借阿向父母之口穿插表达了作家对革命的认识,“11年前血染南京路的第二天晚上,母亲同她的两个女朋友从‘包围总商会’立逼‘宣布罢市’的群众大示威回到家里时,一把抱住这两岁的孩子,……我那时就想到我们的阿向。可是,阿向大了时,世界总该不是现在那样的世界罢?”可事实并非如此,在十一年间,大大小小的示威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直到现在,连自己的孩子阿向都开始参加此类游行了,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依然是混乱、黑暗、亟待打破和重建的世界。整篇小说仍然是以配合革命为主,鼓动宣传少年儿童走出家门,为新世界的建立贡献自己的力量,“他要跟群众走,怎么肯跟你母亲呢!”,“到群众中去”的平民主义思想十分明显。但很显然,在政治至上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儿童的成长是脱离了正确轨道的“伪成长”,例如一个小学生竟然可以在游行中来回走“二十里路”以及阿向在与父母对答中所表现出的冷静、沉着和成熟是他那个年龄的孩子所不可能具有的,这些情节完全是作家为了配合革命宣传而牵强附会上的,其中的儿童是被“拔苗助长”的,是一种虚假的“伪成长”。再如《大鼻子的故事》(原载于《文学》第 7 卷第 1 号,1936 年 7 月1日),小说描写了一个上海小瘪三“大鼻子”的故事,他也只有十二三岁,但却习得了上海滩小流氓的各种恶习,能偷会骗,但一次意外把他卷进了进步学生的游行中,在游行队伍中他起初仍扮演着一个不折不扣的小瘪三的形象,他把鼻涕抹在说洋话的学生身上和头发上,在看到学生的钱夹时仍会忍不住要偷来,但后来他发现,那些游行的学生竟然和自己一样被巡捕打,“他脑筋里立刻排出一个公式来:他自己常常被巡捕打,现在那学生和那女子也被打;他自己是好人,所以那二人也是好人;好人要帮好人!”于是,大鼻子成长了,他开始加入游行的队伍,看到有学生钱夹掉了,他会捡起来再神不知鬼不觉的放回原处,并且跟着学生一起喊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这里当然有儿童的纯真和质朴,但大鼻子的转变还是有些突然了,可以试想,一个经常饿肚子的小瘪三怎么会突然良心发现,将已经到手的钱夹再送回去,可见,为了配合革命形势,作家往往会忽视生活的客观真实性,在今天看来,大鼻子的成长也是不现实的,是一种“伪成长”。
茅盾的儿童小说如此,另一位儿童文学大家叶圣陶的儿童小说也是如此。例如《儿童节》(原载于《永生周刊》第 1 卷第 5 期,1936 年 4 月 4 日),小说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情节———提灯会,提灯会是一种集工艺、美术、书法、剪纸、音乐之大成的综合性民间艺术,在中秋、元宵、端午等中国传统节日中比较流行。1923年2 月 7 日,直系军阀吴佩孚发动了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流血事件“二七”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等团体为推动声讨军阀与援助工人运动的发展,联合决定于旧历元宵节时举行提灯示威游行。
后来,提灯会成为一种习俗,经常出现在各种示威游行活动中。小说《儿童节》中的提灯会显然也非传统节日的纪念活动,而是为了配合当时的革命形势,为儿童谋幸福。
王大春和李诚并不知道提灯会有什么意义,他们只是在先生的鼓动下才要去参加的,而他们参加提灯会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最大的快活”,可以说,这些孩子是懵懂和天真的,他们的成长被那些成人扭曲了,难道提着灯,嘴里喊着先生教给他们的口号“增———进———全———国———儿———童———的———幸———福!”,他们就真能“得到最大的快活”吗?当然不会,这些孩子只能在那些别有用心的成人的蛊惑下畸形成长。再如《一个练习生》,主人公“我”是一个初中读了两年就被迫辍学的少年,爸爸被辞退,妈妈靠糊自来火盒填补家用,生活十分拮据,为了能填饱肚子,“我”在张伯伯的帮助下,考进了书局做了练习生,但却因此付出了自家祖传十几代的字画。经过千难万难终于进了书局,“我”却因为一次无意间的卷入学生示威游行而被书局解雇,竹篮打水一场空,“得到它是这样难,失掉它却很容易,唉,简直太容易了!”小说最后留给读者的仍然是妈妈打结的眉心和爸爸的叹气声。小说表现了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百姓生活的艰难困苦,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黑暗、百业凋零的事实。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儿童,其当然得不到健康的成长,“我”的未来在哪?这是个沉重的话题。
由上可知,茅盾和叶圣陶儿童小说中的“政治至上”思想及其对儿童成长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虽然二者都是“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为人生”的艺术思想都要求他们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但茅盾的革命情绪更为浓烈和直接。
作为革命文艺的奠基人之一,茅盾对儿童文学的鼓动教训作用是相当看重的,“一部‘儿童文学’必须有明晰的故事(结构),使得儿童们能够清清楚楚知道怎样的人是好的,怎样的人是坏的”,“我是主张儿童文学应该有教训意味。儿童文学不但要满足儿童的求智欲,满足儿童的好奇好活动的心情,不但要启发儿童的想象力,思考力,并且应当助长儿童本性上的美质:———天真纯洁,爱护动物,憎恨强暴与同情弱小,爱美爱真……等等。所谓教训的作用就是指这样地‘助长’和‘满足’和‘启发’而言的。”
因此,茅盾在他的儿童小说中,会让儿童主人公十分迅速的成长为小革命者,不懂事的孩童、恶习满身的小瘪三几乎都在瞬间完成了成长,可以想见,这种成长是经过了作家革命情绪的催化而产生的,并不真实。
这些作品也是茅盾、郭沫若等革命文学先驱为配合政治形势和革命进程而创作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却因此而丢掉了艺术的客观真实性和文学的本性,很难成为文学经典。
而叶圣陶的“政治至上”思想则有所不同,他也同样是为了配合革命进程而创作的,但他更多的是描写革命前和革命过程中,作为革命对立面的黑暗社会、混乱政治和帝国主义等对儿童成长的扭曲,从文学特征上来看,则比茅盾的同时期儿童小说要稍胜一筹。
二者一个是鼓动,一个是控诉,都在“政治至上”思想的影响下描写了儿童的“伪成长”,目的相似而手段相异。茅盾和叶圣陶仅仅是民粹主义、平民主义和“政治至上”思想的代表作家,其身后是一大批追随者。在这之后,抗战时期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运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民族形式”大讨论,1942 年的延安整风运动,甚至十年文革的到来应该都是这种革命情绪积淀的历史必然,中国文学的主流话语也由此诞生。
[参考文献]
[1]王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60- 61.
[2]何键.咨请教育部改良学校课程[N].申报,1931- 03- 05.
[3]高尔基.俄国文学史[M].缪灵珠,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7.
[4]蔡元培.劳工神圣[M]//蔡元培全集.上海:中华书局,1981:219.
[5]李大钊.庶民的胜利[M]//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96.
[6]周作人.平民文学[N].每周评论,1919- 1,第5号.[7]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N].湘江评论,1919- 7- 14(1).
[8]鲁迅.鲁迅杂文全集[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4.130.
[9]鲁迅.答有恒先生[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62.
[10]鲁迅.三闲集·序言[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1]茅盾.茅盾和儿童文学[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