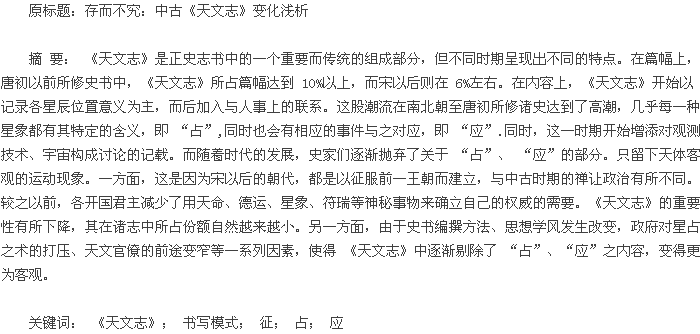
天体运动作为人类可以直观看到的一种自然现象,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人类也对其进行不断的观察和探索,这从历代政权都设有专门的天文机构就可以看出。①天文技术官员们通过长期观测星象运行,留下了大量的记录,成为历代正史 《天文志》中的重要素材。然而,由于古代技术水准的限制,人们还无法完全客观地解释天体的运行规律,故而其中夹杂着大量附会时事的记载。星体的运转,也因此成为天道对人事的反映和警示。
正因为 《天文志》中存在着大量不符合现代科学理论的记载,今人多视其为迷信而缺乏足够的关注; 而其中关于星象名物及其推算的记载又往往繁复难解,也成为深入研究的障碍。故而 《天文志》在过去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随着学术视野的拓宽,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天文对于古人的意义,进而从天文入手探讨背后的政治动态。在这方面,目前已经积累了不少成果。学界已有的研究,从最初的简单星象考订,逐步转向星象与当时政治生活的结合,然对 《天文志》本身的讨论并不多。①其实,《天文志》本身就是正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 《史记》到《清史稿》的 “二十五史”中,十八史有志 ( 或相当于志的书、考等) ,其中十七史就有 《天文志》( 《辽史》无 《天文志》) .北宋欧阳修撰 《新五代史》时,虽然认为 “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但仍编有 《司天考》二卷,足见其对天文之重视,也充分反映了 《天文志》在正史中的地位。仅就入选次数而言,《天文志》和 《礼志》持平 ( 《新五代史》没有 《礼考》) ,更在 《食货志》之上( 《后汉书》、《宋书》、《南齐书》、 《新五代史》无 《食货志 ( 考) 》) ,这一现象也颇值玩味。此外,历代 《天文志》在具体内容和书写模式上有无变化? 其背后反映了古人什么样的思想观念? 等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选取中古 《天文志》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前后时期的变化,提出自己的若干浅见,希望能得到方家的批评指正。
一、历代 《天文志》的差异
我们知道,史书在传记位置的安排上是有所讲究的。在大体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基础上,将哪些人放入到一个列传之中,又将这些列传按照何种次序编排,都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也就是所谓的 “体例”.但具体到某些传记的编排上,则会引起争论。如在摆放 “开国群雄传”位次的问题上,就有着不同的态度。②而这些争论,往往就是不同思想风潮碰撞的表现。与之同理,《天文志》在正史中的排列以及内容所占比例,也反映了时人对其重要程度的认识。
比对诸正史,我们发现,汉到唐初,《天文志》在正史中的比例一直保持在 10% 以上,有时甚至达到 20%.而从唐代开始,《天文志》的份额呈下降趋势,通常在 6% 左右,几乎比上一个时段少了一半 ( 《新五代史》是特例,姑且不算在内) .
但 《天文志》在各正史中所处的位置,一开始显得有些杂乱无章,没有固定顺序,直至元修三史时才稳定地排在诸志之首。发生这种变化,可能是因为唐以后的正史书写由于是官修史书,越来越模式化。到了元人所修的宋、辽、金三史之时,这种情况就变得十分明显。③尽管各书之间存在着些许差异,但大致是按照天、地、人三才的顺序排列的,也即 《天文志》一般居于诸志之首。
《天文志》卷次编排上的变化是一方面,而更令我们关注的还是内容上的差异。由于此前少有专著来讨论天文星象,那么作为第一部正史天文志的 《史记·天官书》就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即具体介绍何谓 “天官”.《史记·天官书》一开篇,首先介绍各星名称、内涵以及所在方位。在此基础之上,司马迁又介绍了种种异象所代表的含义,也即可称为“征”、“占”的部分,但作为 “应”的史实却并不算多,④而且内容也多局限于兵灾,属于当时王朝兴废的大事。
但 《汉书·天文志》则有所不同,其记录 “应”的部分,大大超出了 《史记》的记载。以与《史记》年代重合的部分为例,《汉书》就多出了秦二世 “残骨肉,戮将相”; 汉高祖击匈奴; 汉高祖驾崩; 汉文帝时匈奴入侵; 诛反者周殷; 汉文帝驾崩; 汉景帝时梁王入关谢罪; 梁王、城阳王、济阴王、成阳公主去世; 大疫; 汉武帝除济东、胶西、江都、淮阳、衡山诸王; 废陈皇后; 窦太后去世等事件。①这些材料说明 《汉书》比 《史记》更重视星象的应验程度,而且星象预警的内容也变得更为详细,同时也表明在当时利用星象来为某些政治活动造势,已经逐渐变得普遍起来。
然而这种书写方式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天体的位置及运行规律并没有变化,从而使得关于星象定位这部分显得很累赘。班固因循司马迁,在 《汉书》中继续记录这一部分,就受到了后世的批评,刘知几 《史通》卷三 《内篇·书志》云:
但 《史记》包括所及,区域绵长,故书有 《天官》,读者竟忘其误,榷而为论,未见其宜。班固因循,复以天文作志,志无汉事而隶入 《汉书》,寻篇考限,睹其乖越者矣。……若乃体分蒙氵项,色著青苍,丹曦、素魄之躔次,黄道、紫宫之分野,既不预于人事,辄编之于策书,故曰刊之国史,施于何代不可也。②应该说,刘知几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正因如此,班固之后,唐初之前,诸史 《天文志》都删去了这部分内容,故而受到刘知几的称赞。③但刘知几没有注意到的是,在删去星象定义的同时,《宋书》补入了关于天体三说的讨论以及天文观测仪器的大体形制及使用方法,这也使得 《天文志》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脱离完全讲述天人感应的状况。但遗憾的是,只有 《宋书》如此, 《后汉书》、 《南齐书》、《魏书》对此并无涉及。
这也造成了一个现象,南北朝时 《天文志》中既没有关于星象的定义,也没有对于天文学说的讨论,更没有观测仪器的记录,剩下的只是枯燥的星象记录。从而使得几乎每一个政治事件都可能与天象扯上关系,星象示警次数也因此变得频繁起来,相关内容也日趋细密。
而在唐初所编 《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中,史家们不仅在保留 《宋书》有关天体三说讨论的基础上,大大增补其内容,还将 《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中所舍弃掉的关于天官方位的内容又重新补入其中,同样也较 《史记》、 《汉书》等有所增补。这样一来,就显得篇幅臃肿,体例不当,与 《汉书》一样受到刘知几的批评。之所以这样编写,是因为唐政府集中力量编写多部前朝史书,带有认识和总结前朝历史的意蕴,尤其在 《五代史志》中承载众说,加以评述,更是有整合长期分裂的南北文化之功效,故而时人盛赞李淳风 《天文志》。④这与其后刘知几的评价,可谓大相径庭,其原因恐在于立场不同而已。
《旧唐书》较之以往史书,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在大量增加观测技术内容的同时,相应削减了“征”、“占”、“应”的记载。尤其是唐前期的天人感应记载就相对较少,甚至连唐高祖受禅也没有什么星象表示,这在南北朝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仅有的几条记载也多为有某天象、皇帝询问是何灾异、臣下回答等。而在 《新唐书》中甚至连这些内容也都删去了。《新唐书》在罗列各种天文现象时,记载相应的 “占”,然对应验状况却只字不提。其实欧阳修在 《新五代史·司天考》就表明了自己对待天人感应的态度:
自尧、舜、三代以来,莫不称天以举事,孔子删 《诗》、《书》不去也。盖圣人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绝天于人则天道废,以天参人则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⑤不 “绝天于人”,就需要将星象记录下来; 不 “以天参人”,就要抛弃掉天象与人事的对应。两者综合,就形成了 “存而不究”的 《新唐书》、《新五代史》的 《天文志》、《司天考》了。
然而,抛弃了 “应”的部分,一面使得 《天文志》整体变得更为客观,另一面也使得 “占”的内容变得鸡肋起来。没有了 “应”,“占”也就变得没有意义,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故而元修 《宋史》、《金史》等,“今合累朝史臣所录为一志,而取欧阳修 《新唐书》、《五代史记》为法,凡征验之说有涉于傅会,咸削而不书,归于传信而已矣”.①之后的 《元史》、《明史》等也遵循了这个原则。只保留天象变化的事实,那么剩下的内容就再也很难和实际政治联系起来了。其实非止 《天文志》如此,《五行志》亦是同样去掉了那些牵强附会的东西,一定程度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轨迹。
要之,历朝 《天文志》在次序安排上逐渐由杂乱无章走向系统化、模式化,《天文志》在 《宋史》以后诸史都占据了首篇的位置; 在志书所占比例上,却由唐以前的10%以上,下降到了唐以后的 6%左右。在内容上,由充满谶纬占应变为较为客观单纯的星象记载。那么,为何会产生这一重要变化呢? 下面对此试作分析。
二、政权更迭模式与 《天文志》地位的升降
中古 《天文志》地位的凸显,与当时政权更迭模式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知道,汉唐间朝代更迭,多采取禅让模式。新君多为旧臣,以臣谋君,本就不合道义,唯有强调受禅者得到天命的眷顾,才能在政治上取得相应的合法地位。从汉献帝的退位诏书开始,“天之历数,实在尔躬”这句话几乎成了禅让文中的必备语句。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许多天文现象就被附会上了天命的色彩。
如汉献帝时,“( 建安) 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东井舆鬼,入轩辕太微。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贯紫宫,及北辰。占曰: ‘彗星扫太微宫,人主易位。’其后魏文帝受禅”.②这里就有值得玩味之处。魏得天命的种种天文异象,其实并不在汉魏之交的延康元年 ( 220) ,而是追溯到了建安九年 ( 204) .这恰恰说明了时人对天象的重视,即使当年并没有特别的星象,还是要通过更为牵强的附会来确立自己禅代的合法性。到了南北朝时期,情况依旧如此。譬如按照 《南齐书》设计的体例,《天文志》中不应该出现占应的记载。③然而萧子显还是要对齐高帝受命时的天象大书特书。④这清楚地说明天象对于南齐受禅的意义。
又如,东西魏分立之时,有关正统性的问题变得十分重要。北齐魏收借着自己编 《魏书》之际,就把北齐政权兴起的天象记录其中。⑤《周书》由于没有志,在这点上就存在缺憾。即便后来北周隋唐一系编写的 《五代史志》,仍不见关于此事的记载,可见缺少本朝的 《天文志》,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迨至唐代,有关唐高祖受天命的记载却均被史书忽略了。新、旧 《唐书》的 《高祖纪》、 《天文志》都没有相关的记载。《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记载了大量裴寂等人为李渊登基做的准备,但其中大多都是谣谶,而没有天象的记录。⑥这种星象上的缺失,在于李唐与魏晋南北朝诸政权存在一个较大区别。当时的隋政权处于一种土崩瓦解状态,并非一个安定完整的整体。李渊的竞争对手,是各地拥有精兵强将的实力派军阀,而非朝堂上的政治对手。口口相传的谣谶在底层民众中还能发挥一下作用,玄奥虚渺的天象在一般百姓中很难传播。而对于拥有知识精英的竞争对手而言,这些东西又实在是太空洞了些。在这种情况下,天象的价值就显得可有可无。因此,李渊将其排除在禅让征兆中,也就能够理解了。
这种情况到了五代时更甚。朱温建梁,要取代的是已经立国近三百年、有二十余位天子的唐朝,其所承受的历史压力可想而知,故而不得不选择异常天象来表示自己为天命所归。《旧五代史》卷三 《梁书·太祖纪三》云:
唐乾符中,木星入南斗,数夕不退,诸道都统晋国公王铎观之,问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 “金火土犯斗即为灾,唯木当为福耳。”或亦然之。时有术士边冈者,洞晓天文,博通阴阳历数之妙,穷天下之奇秘,有先见之明,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铎召而质之,冈曰: “惟木为福神,当以帝王占之。然则非福于今,必当有验于后,未敢言之,请他日证其所验。”一日,又密召冈,因坚请语其详,至于三四,冈辞不获。铎乃屏去左右,冈曰: “木星入斗,帝王之兆也。木在斗中,‘朱’字也。以此观之,将来当有朱氏为君者也,天戒之矣。且木之数三,其祯也应在三纪之内乎。”铎闻之,不复有言。①细绎史料即可发现,所谓 “金火土犯斗为灾,唯木当为福”,并不符合中古以来的传统天文学观念。木星,在星书多称为岁星。《魏书·天象志》云: “是岁六月,岁星昼见于南斗。斗为天禄,吴分也。
天象若曰: 或以诸侯干君而代夺之。”②《新唐书·天文志》对 “岁星犯斗”的 “占”有两条,一条预示着 “大臣有诛”,一条预示着 “有反臣”,都不是什么福兆。③而号称 “洞晓天文”、“博通阴阳历术之妙”的边冈所谓 “朱氏为君”云云,居然使用的是拆字法,与传统天文星占术迥然不同。这条材料说明时人在对星象解释中,不仅加入了新的说辞,更在原理上采用了更为简便易行的拆字法。然而这种新方法显然只能是针对具体事例偶一为之,很难构建一个相对完整自洽的体系。换言之,原有占星术已逐渐萎靡,新生的拆字法却又难以长久流传。天象示警的体系不可避免地衰弱下去了。
此后的后唐,本就与后梁是敌对政权,不存在禅让问题。后晋是契丹所立,被契丹所灭,与后唐、后汉都不存在禅让关系。真正较为典型的禅让,只有后汉与后周、后周与宋。而且这些禅让在战乱之中,亦不过是虚应故事而已,远不如魏晋南北朝时隆重。这一点从新、旧 《五代史》和 《宋史》上对禅让事宜书写的简略即可看出。宋以后各朝都是以武力征服的方式建立新的政权,根本无需禅让,也就更谈不上与之相关的天象了。
因此 《天文志》就失去了原有的一个重要功能,即为政权的正统性提供依据,也随之失去了其重要地位。其实不仅 《天文志》如此,其他诸如德运、祥瑞、五行灾异的地位都受到冲击。比如中古时期激烈讨论的德运问题,在宋以后就很少提及。④宋以后的历代 《五行志》,虽也在序中往往提到一些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⑤之类的说法,但更多的还是记录客观存在的种种灾异,并不将其与时局政治联系起来。或者说,联系的远远没有宋以前的史书那么紧密。
三、“占”与 “应”的消失
与 《天文志》在篇幅上的减少相对应的是,在内容上也逐渐抛弃了 “占”、 “应”的记载。此种变化,不仅仅是因为政权的取得由 “天命”转变为 “逐鹿”,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
首先是和 《天文志》的编撰方式有关。我们知道,各朝都有自己的天文机构,会将观测到的结果记录下来,以作为以后编写史书的数据。如唐代,就有如下规定:( 太史局) 每季录所见灾祥送门下、中书省入起居注,岁终总录,封送史馆。①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通常来说,应该是先有天象示警,再有结果发生。但是由于天文机构只能记录下他们所观察到的结果,顶多附上占语,但无法记录之后发生的应验状况。其实五代时,司天台的旧例就是 “祇依申星耀事件,不载占言”了。②史馆记下之后发生的历史事件,却未必会将之与星象记录对应起来。而且唐代以前,多为私家修史。这些史家都是博学多才之士,修史时胸中自有丘壑,有着自己的谋篇布局。因而能将分开的星象记录与历史事件串联起来,写成 《天文志》。有时即使牵强附会也要将两者扯上关系,比如上举 《后汉书》记录曹魏得天命的记载,即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文中当然就是征、占、应三者俱全。
而唐代开始官修史书制度,书成众手,总揽全局的角色又常常由宰相挂名充任,不能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著述中。但具体参与撰写的史臣,却又未必能顺利的获得规定上应该拿到的材料。如刘知几修国史时,就向萧至忠抱怨: “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编录,唯自询采。而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台阁,簿籍难见。”③而志书,尤其是 《天文志》这种专业性较强的书,往往是请专业人士来写。如 《晋书·天文志》、五代史志的 《天文志》,即出自李淳风之手。编写 《新唐书·天文志》的刘羲叟,亦是 “尤长于星历、术数”.④这种纪传与志书的分离,更会造成内容上的不协调。若要将条目繁多的星象记录,逐条与正史纪传相对应,恐怕一般天文学者也难胜其任。在这种情况下,“应”的消失也就能够理解了。
其次,利用天象星占,亦渐渐受到怀疑。西汉开始流行谶纬之学,在东汉达到顶峰,南北朝亦颇为盛行。但当时亦有人对星占之术提出质疑。比如谈到浑仪时,刘宋徐爰即称: “浑仪,羲和氏之旧器,历代相传,谓之机衡,其所由来,有原统矣。而斯器设在候台,史官禁密,学者寡得闻见,穿凿之徒,不解机衡之意,见有七政之言,因以为北斗七星,构造虚文,托之谶纬,史迁、班固,犹尚惑之。”⑤唐代一些有识之士对天象星占之书嗤之以鼻,却希望对此加以利用,以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
孔颖达即是其中代表。他说:
天道深远,有时而验,或亦人之祸衅,偶相逢,故圣人得因其变常,假为劝戒。知达之士,识先圣之幽情; 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惧。但神道可以助教,不可专以为教。神之则惑众,去之则害宜。故其言若有若无,其事若信若不信,期于大通而已。世之学者,宜知其趣焉。⑥孔颖达正是要借助天象来约束人君行为,使得人君时刻保持警惕的状态,不至肆意妄为。至于他自己对于天象星占之说,只是 “若信若不信”而已。⑦五代时,抨击天人感应的思潮变得更为猛烈。《旧五代史》卷四三 《明宗纪九》云:( 长兴三年十月) 壬申,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 “是知国家有不足惧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阴阳不调不足惧,三辰失行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涸不足惧,蟊贼伤稼不足惧,此不足惧者五也。”……澄言可畏六事,实中当时之病,识者许之。⑧康澄将阴阳不调、三辰失行看作 “不足惧”之事,而且被 “识者许之”,颇见时人对天变的态度。
在五代乱世,逐鹿比之天命更为现实。“尽人事”也取代 “安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其实较之理论上的质疑,更为现实的是,星占术的实际效果更是难以言说。据黄一农先生利用现代天文手法回推,星占学中一大凶象---荧惑守心,在史籍上的记载有二十三次,但其中十七次都为虚构,附会牵强之处可见一斑。实际上,这种天文现象约五十年即发生一次,亦即是说,有大量的此种星象未被记录下来。①用这样的数据记录来进行星占,自然很难得到满意的结果。或者说由于有大量的伪造情况存在,被识破的可能性也是极高的。
到了宋代,关于天人感应之类的感应说、天谴说的争论就更是激烈。日本学者小岛毅先生在讨论有关争论后,作出如下结论: “在政治领域中,事应说依然发挥着效力。但是仅依此并不能说他们从内心里相信 ‘事应’理论。……不只如此,甚至可以说批判事应说才是宋代的主流。”②应当说这个结论是中肯的。在这种思想氛围下,赵宋以后的历代 《天文志》中抛弃掉事应的部分也就能够理解了。
此外,天文官员地位的变化,也是值得关注的。虽然司马迁称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③但实际上,太史令一类的天文官员并无升迁上的障碍。如曹魏重臣高堂隆,“王即尊位,是为明帝。以隆为给事中、博士、驸马都尉。……迁侍中,犹领太史令。……迁光禄勋”.④又如北魏晁崇, “太祖爱其伎术,甚见亲待。从平中原,拜太史令,诏崇造浑仪,历象日月星辰。迁中书侍郎,令如故”.⑤可见太史令一职不仅可由侍中、中书侍郎来兼领,之后也不妨碍迁为他官。
但到了唐代,具体负责天文观测、星象占卜的官员,被称为伎术官。而伎术官只能在本司内迁转,极难进入主流官场。《唐六典》卷二 《尚书吏部》吏部侍郎条云:
凡伎术之官,皆本司铨注讫,吏部承以附甲焉。 ( 谓秘书、殿中、太仆寺等伎术之官,唯得本司迁转,不得外叙。) ⑥观测天象是由太史局负责的,正好隶属于秘书省。其实,《唐会要》里说得更清楚:
神功元年十月三日敕: “自今以后,本色出身,解天文者,进官不得过太史令。”⑦也就是说如果是伎术官出身,即便业务能力再强,也只能在太史局内工作,最多升到太史令、丞。
这是一个浊官职位,前途暗淡,绝非士人所乐为。既然无上进之途径,工作中也难免缺少动力。无参与之积极性,自然也难去鼓吹风险较高的星占活动。
还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隋唐时期,科举兴起,除了专门去考明算的士人之外,明经、进士科都无需太多的天文知识。而官方严厉禁绝的措施,又使得底层不容易接收到这些星占之书 ( 当然,并非完全没有) .如此循环,星占学在官僚士大夫中的知识体系中地位逐渐下降,最后被排除在正史之外也就能够理解了。
综上所述,在由私家修史向官方修史的转变过程中,由于书成众手,提高了将天象与时事串联在一起的难度。而思想学风上的转变,预测不能达到满意结果的尴尬,也使不少人对星占之术产生了怀疑。同时政府对星占术的禁止日趋严苛,天文官僚的出路日趋狭窄,打消了其对星占的热情。这一系列的原因,最终导致了谶纬星占之学在正史中出现的比例越来越少,以至于无。
结 语
《天文志》是正史志书中的一个重要而传统的组成部分。诸史几乎是有志必有 《天文志》。然而,其在内容和篇幅上却发生了变化。在唐初以前所修史书中,《天文志》所占篇幅达到了 10% 以上,而宋以后则在 6%左右。在内容上,《天文志》开始以记录各星辰位置意义为主,而后加入了与人事上的联系。这股潮流在南北朝至唐初所修诸史达到了高潮,几乎每一种星象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即 “占”,同时也会有相应的事件与之对应,即 “应”.同时,这一时期开始增添对观测技术、宇宙构成讨论的记载。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史家们逐渐抛弃了关于 “占”、 “应”的部分,只留下了天体客观的运动现象。一方面,这是因为宋以后的朝代,都是以征服前一王朝而建立,与中古时期的禅让政治有所不同。各开国君主不需要以天命、德运、星象、符瑞等神秘事物来确立自己的权威,《天文志》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其在诸志中所占份额自然越来越小。另一方面,由于史书编撰方法、思想学风发生改变,政府对星占之术的打压、天文官僚的前途变窄等一系列因素,使得 《天文志》中逐渐剔除了 “占”、“应”之内容,变得更为客观。这说明尽管人们未必是主观的、有意识地剔除固有观念中迷信蒙昧的成分,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还是不自觉地走上了更为理性的道路。这种历史趋势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