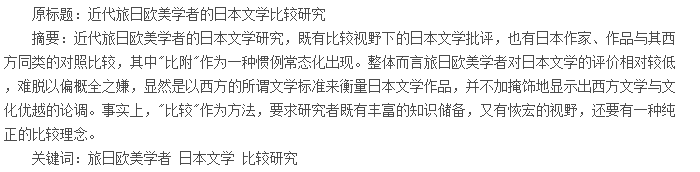
1853年之后日本幕府解除了锁国禁令,明治维新接踵而至,短时期内欧美人大量涌入日本。地处 亚洲 东隅 的日本在思想、政治与社会诸层面的变化,引起了欧美人的广泛关注。曾经一度代表日本与外部世界交流主渠道的中日文化往还,让位于欧美诸国与日本的接触、体认和交流。随着人员往来的增多趋繁,思想文化方面的交流必然走向细化与深入,而最能体现日本思想文化特征的日本文学很快进入了旅日欧美学者的视野。
旅日欧美学者较 早开始译介日本和歌、俳句与物语中的经典佳作,同时积极开展研究。他们以相异于日本人的视野与旨趣为出发点,在历史上第一次将日本本土的学问与近代西方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将自己长期身在日本获得的文化体验与扎实的学术训练相结合,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开展日本文学批评。
由近代旅日欧美学者创办、在日本出版发行、最早完全专注于日本研究的英文刊物《日本亚洲学会学刊》(Transactions of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刊载了一些研究日本文学的文章,将日本民间文学与西方的民间故事加以对照比较,也进行过汇通日本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尝试,将日本作家、作品与其西方 同类进行平行比较。
本文拟从载于该刊的部分此类文章入手,探讨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文学比较研究方法和宗旨,研判其类比的合理性,探究在跨文化理解与传通的过程中"比较"的方法问题。东西方民间故事对照民间故事是指在历史上由民众集体创作、依靠口头流传并一直留存下来的虚构性非韵文口头文学作品。民间故事题材广泛,往往与古老的神话有某种关联,常常借助奇异的语言和象征的形式展开情节,大都表现人们的美好愿望。
1875年古德温(C.W.Goodwin)在《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第三卷发表的《日本传说数种》,概述了一些日本民间故事,并与《格林童话》、爱尔兰民间传说等进行了对比。
《鬼取瘤事》及其西方比照古德温从日本古典故事集《宇治拾遗物语》中一个名为《鬼取瘤事》("The Story of the Man withthe Wen")的日本故事谈起,大意是:一个斫柴翁因风雨大作无法回家,不得不在山上过夜,因无处容身而钻进树洞,遇见群鬼饮酒跳舞,受感染而加入到他们的歌舞行列。群鬼很开心,临别时要他日后再来,并取下他右颊上的瘤以为质。邻翁左颊上也有个瘤,想让群鬼帮他拿掉,于是也进山过夜。但因他舞跳得太拙劣,群鬼很生气,就把上次那个瘤掷还到邻翁颊上,翁饮恨而归。故事结尾点明寓意:不应嫉妒他人。
古德温将《鬼取瘤事》与爱尔兰民间故事《诺克格拉夫顿传说》("The Legend ofKnockgrafton")进行对比。后者讲的是在一个名为诺克格拉夫顿的村庄,一个善良的驼背小个子一个夏日的夜晚在护城河边听到水下精灵唱歌,因不满对方歌声单调,在歌声间隙插入自己的吟唱,被对方捉到水下,与他一起唱歌跳舞。之后为答谢他,精灵用黄油做的锯把他的驼背锯掉,他直起腰来,变得很高大。村中另一个驼背在母亲怂恿下做同样的尝试,却急不可耐地用毫无韵律的吼叫一次次打断精灵的歌唱。被激怒的精灵为了惩罚他,将上次取下的驼背加到他身上。故事结尾揭示:这就是嫉妒和不好的品味造成的后果。
古德温评述道:"毫无疑问这两个故事是同一的。难道我们能够认为同样的主旨会'独立地'进入两个不同的讲故事人的头脑?说其中一方的故事不是从另一方借鉴的可信吗?"(58)他相信近代日本与爱尔兰两国间不可能存在直接交往,也没有办法追查该故事的迁徙流播情况,很可能同一个故事几乎走遍了全世界。他猜测一种可能是日本人在相对晚近的时候通过中国,或通过阿拉伯或印度的商人接受了外来故事;另一种可能是这类故事属于都兰语族圈最古老的传说,远在信史黎明阶段以前就广泛存在于整个亚洲与欧洲。
(69)按照古德温的前一种猜测,故事系从西方传到东方的;若后一种猜测属实,则该故事当是从东方传到西方的。仔细推敲,古德温的推测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至少迟至13世纪初叶日本与爱尔兰之间不存在人员往来的通道,也没有足够证据表明中间有一个过渡或中转,所以很难断定一方的故事是从另一方那里借鉴的。古德温确信《诺克格拉夫顿传说》"在爱尔兰以外的欧洲其他地方不为人知",(54)因而该故事向外流传的可能性非常小,无论哪个方向上的传播都不可能不着痕迹。
古德温没有言及的另一个关键点,是《鬼取瘤事》蕴含着明显的佛教因果报应因素。自中世以来,日本文学、尤其是小说中一直贯穿着浓厚的佛教思想,如轮回、无常及因果报应等。这类题材在近世得到延续,小说中对地狱冥府、妖魔鬼怪等的描写颇为常见。《宇治拾遗物语》中除《鬼取瘤事》外,《鼻长僧事》、《雀报恩事》等许多故事都包含类似的佛教思想,其中 《雀报恩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文学比较研究事》宣扬善恶有报、否弃嫉妒的论调与《鬼取瘤事》如出一辙。
《日本采石工》之东西方对照《日本采石工》("The Japanese Stone-cutter")说的是一位采石工工作非常辛苦但收入微薄,有一次他仰天长叹,天使现身帮他实现愿望。他先是希望变得富有;变富有后又想成为国王;继而又想成为力量更强大的太阳;后太阳被云遮住,又想成为云;云被岩石挡住,又想成为岩石;一旦变为岩石,见一个采石工从岩石上采下许多石块,心生羡慕,最终又变回到采石工。他继续辛苦劳作,收入一如既往地微薄,却心满意足了。古德温称自己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时即联想到格林童话中 《渔夫和妻子的故事》,其寓意是"满足于你现在的状态".
古德温指出,《日本采石工》出现于一部荷兰小说《麦克斯·哈夫纳》(Max Havelaar)中,并且明确指出该故事取自一篇名为《荷属印度》("Dutch India")的期刊论文,显然其中包含若干非日本因素。考虑到日本在江户时代,包括锁国的1641-1853年,与荷兰关系甚好,并且荷兰人是当时唯一能够出入日本的欧洲人,或可以推测该故事系由荷兰赴日人士传入日本的。古德温调查后却发现,当时在任何日本书籍中都找不到类似故事,很难想象荷兰人会直接向日本人口头传播并在民众中迅速流传开来。
但是有一个正在日本民众中口头流传的《野心老鼠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Am-bitious Mice"),主要情节与此十分相似。
野心勃勃的老鼠要把女儿嫁给世界上最强大者,最初选择了太阳;发现太阳可以被云遮住,于是改选云;云可以被风吹走,又改选风;风可以被墙挡住,再改选墙;最终发现墙可以被老鼠穿透,确信还是老鼠最强大,于是把女儿嫁给了老鼠。古德温指出,尽管采石工的故事与野心老鼠的故事有明显的共同基础,但又在若干重要之处存在着差异。
他解释可能荷兰作家在整理时头脑中早已存在的德国传说在起作用,又说德国的《渔夫和妻子的故事》与日本《野心老鼠的故事》虽存在一般的相似性,但它们是否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却相当令人怀疑。因为日本采石工的故事出现在荷兰小说中,从而在两者之间构筑了某种联系,然而这三个传说一起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即一种想法可能会有多种表现形式。
东西方作家比较近代旅日欧美学者在某些日本作家与西方作家间切实进行过一些比较,深化了欧美读者对所述日本作家的理解。比如迪克逊(J.M.Dixon)就镰仓初期着名歌人、随笔作家鸭长明(1155-1216,一说1153-1216)与华兹华斯的文学相似性展开过研究,霍拉(Karel Jan Hora)就鸭长明与华兹华斯的生平进行过异同比较,张伯伦(BasilHall Chamberlain)也讨论过松尾芭蕉与华兹华斯的类比。
迪克逊论鸭长明与华兹华斯鸭长明是早期旅日欧美学者着墨最多的日本作家之一。《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第二十卷刊载了迪克逊的一篇论文和一篇译作,分别是《鸭长明与华兹华斯:文学相似性》和鸭长明所着《方丈记》开头部分的英译("A De-scription of My Hut")①.译作在此姑置不议,前一篇文章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探讨鸭长明与华兹华斯在文学创作与生活态度方面的异同。
按照迪克逊的说法,鸭长明与华兹华斯都喜欢亲近自然。鸭长明对待花草树木的方式与现代美学的方式有类似之处,即倾心于表现树枝或花朵的曲线或色调;而华兹华斯则相信"生物之美在于它本身",(Dixon:198)而且当他在诗中言及花草或无生命的事物时,从来没有将它们与周围的环境相剥离。二 人的 山居 生活存在分歧:华兹华斯以一种逐年延展的方式生活,而鸭长明则以一种收缩的方式生活,并最终陷入虚无。迪克逊分析鸭长明生命有如蝉蜕的说法,认为其口吻不像哲学家的人生感悟,而像一个"现世中失意的人在表达懊悔".(196)在迪克逊看来,尽管鸭长明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却绝不是一个皈依者",(195)他只是适度地遵循佛教的要求,因佛教教义无疑和他的情趣相投。当然,迪克逊也承认华兹华斯在面对宗教仪式时也无意于那些繁琐的礼仪。
霍拉的鸭长明与华兹华斯比较1907年霍拉发表了《论鸭长明的生平与着作》和《无名抄》的英译,译文前有一篇简短的序言,虽未明言,但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心目中优秀日本诗歌的标准。标准之一是和歌创作者必须注意不要离开和歌所规定的主题,但是与主题结合得过紧也不好,对"度"的把握颇见艺术功力。("Nameless":83)标准之二是应避免在某些词语的左近使用与之类似的词语,(85)因为重复用汉字表达同一个意思或许不能达意,这时需引入假名。在《论鸭 长明的生平 与着作》一 文中,霍拉从鸭长明与华兹华斯的身世与生平出发进行比较,探寻二者在精神形态与个性方面形成差异的原因。
首先,二人的家庭背景与遭际有可比之处。出身于世代神官之家的鸭长明本想继承父祖事业却遭到阻挠,父亲早逝,妻离子散。华兹华斯生于律师之家,父亲早逝似乎未对他的生活造成太恶劣的影响,因为他仍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舅父虽因不满他参与政治活动而不肯接济他,他却获得了同学的遗赠,足 以保证生活无忧。
其次,二人在各自时代诗坛的地位有可比之处。1187年鸭长明因一首恋歌入选《千载和歌集》而跻身于"敕撰歌人"行列,后以宫廷歌人身份步入歌坛,其思想和文学对于日本的歌道乃至后世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霍拉认为鸭长明"作为诗人的声誉要高于作为作家的声誉 ",("Notes":46)证据是《新古今和歌集》收录了他的12首和歌,并被视为上乘之作。华兹华斯1843年被任命为"桂冠诗人",成为继莎士比亚与弥尔顿之后的一代大家,其诗歌理论动摇了英国古典主义诗学的统治地位,有力地推动了英国诗歌的革新和浪漫主义运动的发展。最后,二人的人生阅历也有可比之处。
除了都是 幼年丧父以外,鸭长明经历过大火、飓风、大饥馑、大地震等,这些极大地刺激了他,使他深感人生无常,于是出家隐居,过着与世隔绝的贫困生活。华兹华斯也经历过思想上的大起大落,对法国革命从拥护变为反对,最后寄情山水,在大自然里寻找慰藉。
张伯伦的松尾芭蕉与华兹华斯比较一些近代旅日欧美学者将松尾芭蕉称作"日本的华兹华斯",不少日本人也随声附和,但张伯伦在《芭蕉与日本俳句》中明确指出自己不认同这种比附。他认为,首先芭蕉不如华兹华斯幸运;其次,芭蕉用于诗歌创作媒介的日语是无比低劣的;最后,芭蕉不幸被限定在俳句这种唯一的诗歌形式、也是诗歌中最贫乏的(the poorest)形式中。(291)张伯伦无意贬低芭蕉的地位,相反,他给予芭蕉相当高的评价:芭蕉成功地令他生活时代的诗歌品位得以重建;他对自然的了解与同情至少与华兹华斯一样密切;他对不同境况下人们的同情甚至超过华兹华斯;他从未与自己的同类人隔绝,而是非常高兴地生活在世界上(in the world),尽管并不是入世地(of theworld)生活;他的同时代人从他那里获得的道德教义并不比文学影响小。
(291)将芭蕉比作华兹华斯的确多有不妥,但张伯伦给出的解释也是很成问题的。首先,芭蕉的生活环境、成长条件的确不如华兹华斯,但环境的不利有时还是令诗作出彩的一个外部原因,中国就有"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说法。前述鸭长明与华兹华斯都将一生的不幸遭遇与多舛的命运化为写作的素材与动力,并成为各自时代领风骚的大家。
其次,说日语作为诗歌创作的媒介无比低劣,带有明显的英语优越论,显示出作为语言学家的张伯伦心存偏见。假如说日本人整体诗性思维欠发达,似乎与语言没有本质的联系。像张伯伦这样抱持狭隘日语观者在当时的旅日欧美学者中非常普遍,影响所及甚至如森鸥外等知名日本学者都曾一度鼓吹日语罗马化,认同所谓的日语低劣论。最后,将俳句定位为诗歌最贫乏的形式也欠斟酌。虽然俳句形式短小且定规颇多,无形中限制了它的表现力,但单纯依据篇幅长短评判诗作优劣的做法似不足取。诗歌贫乏与否,应侧重于其内容与表现力方面。俳句在日本流行逾千年而不衰,并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带来心灵的共鸣,说明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篇幅短小并不必然意味着蕴涵与表现力贫乏。
文学"类比"的合法性在旅日欧美学者的论述中常见"和庄兵卫---日本的格列佛"、"中国儒学的马丁·路德---朱熹"之类的说法,这种比附在当时是作为一种常态出现的惯例。张伯伦提到,日本批评家为了使他们的民族文学能够与莎士比亚、司各特、雨果、卢梭等人的作品对话,往往"借助欧洲艺术批评的学术性,如'主观的'、'客观的'及其他一系列行话(jargon),忙于将家鹅转变为天鹅".(302)类似表达如果仅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倒无大碍,但若片面地认定二者对等,甚至为证明这种对等而不惜在材料选取与论证过程中做出有倾向性的选择,则易产生严重的误导。
在异质文化接触、交流的最初阶段,为了理解异质文化或者便于对外来思想的接受与本土化改造,大致都要经过一个比附的阶段。如中国魏晋时代以玄学解释佛教的"格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汤用彤:152),或"以本国之义理,搭配外来思想",(汤用彤:212)即通过与中国固有义理的比附和解释说明佛经所言。
迨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近代思想家再次援用"格义"的方法,以佛教之说解释西洋之学,如谭嗣同的《以太说》借助佛教思想解释西洋哲理,(谭嗣同:433-34)宋恕的《印欧学证》用佛经印证欧洲新说,(宋恕:85)等等。平安时代末期的日本为促进佛教与神道的融合,出现了佛教的本土化表现---"本地垂迹",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比附。
博厄斯(Franz Boas)在1896年发表的《人类学比较方法的局限》一文中明确反对盲目比附:把世界不同地区的相似文化现象加以比较的人类学研究,为了发现这些现象发展的统一历史而做出假定,认定相同的民族学现象到处都以同样的方式得以发展。这种新方法的论证中的毛病就在这里,因为并不能给出这样的证据。即使是最粗略的评论也会表明,同样的现象可以以多种方式发展。
上述人类学研究的所谓比较,不过是把"相等"或"相似"的成分放置在一起,牵强地迫使现象就范于理论。以偏概全的比附省略了原本极其重要的比较平台的构建,不仅颠覆了原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而且有削足适履之嫌。
1907年劳埃德(Arthur Lloyd)批评了十五年前迪克逊所做的鸭长明与华兹华斯的比较,指出虽然华兹华斯与鸭长明都是描写自然的诗人,但前者是一个漫不经心的作家,他充沛的思想令他行文冗长,而后者因深受日本文学追求简短与清晰的定规限制,从而将自己的思想压缩到最简洁的文字中。("Minutes",1907:149)劳埃德认为鸭长明与坦尼森(Alfred Tennyson)之间的比较或许更合适,因为他们都用简练的用语表明创作的用心。张伯伦的《芭蕉与日本俳句》也多次指出坦尼森的诗作非常接近日本俳句浓缩的美。
鸭长明与华兹华斯的比较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争论的焦点其实不在于他们是否可以比较,而是比较什么的问题。劳埃德也承认虽然他们都是描写自然的诗人,但二者在行文风格方面存在差异。至于在华兹华斯与坦尼森之间选择哪一个与鸭长明进行比较更为恰当,关键是如何找准相比较的双方在诗作方面的可比性,因为在进行广泛的比较之前,材料的可比性必须得到证实。迪克逊通过对比鸭长明与华兹华斯的诗作发现,当鸭长明提及杜鹃时,总是遵循中国传统,突 出它悲哀的鸣叫;而在英语世界里,杜 鹃却 是友好的象征。同一事物在不同文化中营造出不同的意象,因而附着在其上的象征意义也有所差别。迪克逊在进行比较的过程中除了寻找常规的文学相似性以外,还隐约透露出他的宗教情怀。
首先,迪克逊指出鸭长明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皈依者,这其实是以一个宗教意识浓厚的基督教信徒的目光在丈量日本作家。张伯伦也指出过许多日本人只是在形式上成为佛教徒,虽然也有一些真正的皈依者,但多数都是处在神秘的热情与艺术、文学的修养之间。(275)就近代旅日欧美学者而言,他们都是在西方基督宗教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宗教已经内化为他们的思想意识的一部分,深刻影响到他们的言行举止与价值判断。而在日本,无论民众还是学者,多出于实用目的而有限地援用宗教信条或宗教仪式,并将其化为一种处世行为的内在指引。
或许他们难以理解日本人对待宗教的这种态度,所以在比较东西方文学相似性时会拈出对宗教的虔信与皈依与否作为标准。其次,迪克逊在观照鸭长明与华兹华斯对待社会的不同态度时也体现出其宗教情怀。在迪克逊看来,鸭长明的态度是出世的,面对社会表现得冷漠无情,对人类的苦难及其抗争无动于衷;而华兹华斯的态度则是入世的,面对社会表现出无尽的同情和更多的善意。迪克逊同样将二者的这一差异归结为是否具有悲悯的宗教情怀使然。
第三,迪克逊还从二者心灵的宗教结构入手区分他们的不同之处。他的核心观点是,面对外部世界时华兹华斯有意忽略所有原罪与救赎的问题,而鸭长明则时刻体现出一种冷淡(indif-ferentism)的态度。(197)迪克逊将鸭长明的这种态度视作日本人的国民性,他说这种冷淡给人的第一印象不错,但最终会令人不快。言外之意鸭长明是日本宗教结构影响下的一个作家,其言说方式缺乏道德光芒,缺乏力量和温暖感。
按照迪克逊的解读,华兹华斯挣脱了基督宗教"原罪-救赎"的藩篱,并在其作品中体现出对愉悦的追求和给人以教导的旨趣。且不说迪克逊将冷淡态度定位为日本的国民性是否合适,至少他称许华兹华斯作品中对愉悦的追求相对有说服力,并且也符合文学的审美性特征。但他推崇华兹华斯作品中带有"给人以教导的旨趣",这一标准的设定是成问题的,因为"说教"肯定不能成为优秀文学作品的标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结合迪克逊对鸭长明与华兹华斯文学相似性的比较来看,霍拉对二人生平的比较基本上能站得住脚,也达到了通过比较区分异同的目的。鸭长明与华兹华斯相似的家庭出身使他们都有机会获得优秀教育,这为他们日后走上文坛并引领文学大潮奠定了基础。不尽相同的不幸遭遇对他们的影响也程度不一。
一系列接踵而至的打击直接影响了鸭长明的人生轨迹与价值信念,于是他选择与世隔绝的隐遁生活,实出于对现世人生的厌倦。相对而言,华兹华斯所受的打击并非致命性的,结果尽管他也寄情山水,但并不妨碍他继续以入世的姿态写作、生活,并在诗中给人以教导。
文学比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阴影以外在的"他者"视角研讨异质文化与文学时,已然包含了 比较 的视 野在其中。比较视野并不强调两个国家或两个民族间的文学跨越性比较,那种为了形成对照而生拉硬扯的比附先在性地丧失了比较的立场。
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在18世纪中后期西欧思想家那里已有显现,在19世纪的西方社会更得以发展,表现在西方对东方以及世界的理解与认识方面。西方主要指欧洲,他们以世界的中心自居,以欧洲作为文明与进步的代表以及世界精神的体现者,认为东方是落后、停滞、没有发展并外在于世界历史的。西方中心主义对东方充满了误读与遮蔽的动机,和居高临下的傲慢心态。
在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时代,人们总是从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出发审视异族与他国文化。当西方将自己的思想观念与历史进程看作是正常的、具有普遍性时,其中包含着明显的欧洲优越论的价值取向。西方与东方被安排在高低不同的概念等级中,认为人类历史围绕西方文化展开,西方文化的特征、价值或理想带有普遍性,从而代表非西方未来的发展方向。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对一个欧洲人来说","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1)东方学"带有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殖民主义强烈而专横的政治色彩".(3)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系以西方为标准来认识和评价东方的,将思维截然划分为东西方两种对立的存在。
西方学界的有识之士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与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谴责西方流行的狭隘历史观将历史简单地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三阶段,指出它仅适用于西方。(91-92)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严厉批评了西方"自我中心的错觉",即世界环绕着西方旋转,存在着"不变的东西",以及"进步"是不可避免的。(149-57)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指出历史不是线性、透明的,而是"强调动态和多元,与历史单一性构分庭抗礼",(54)从而要对分叉的历史分别进行追踪寻迹。
但近代旅日欧美学者中抱持西方中心主义观念者大有人在。
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年,西方急剧对外侵略扩张,旅日欧美学者大多来自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上层白种人,他们因历史局限性或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量,认为经济发达等同于政治正确,进而意味着文化先进。比如丹宁(Walter Dening)1913年在《日本现代文献》一文中露骨地宣扬东西方对立、西方代表进步的观点:"论述日本的外国作家……大多数都认为,被称作西方文明的东西要优于东方文明,他们必然地支持日本全面西化(thoroughly Occidentalized)。"(40)他在提到旧有的日本观念与行为方式和新式的西方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冲突时说:"产业阶层无疑是亲欧的,也是进步的(pro-Europe-an and progressive)。"(45)像这种不加掩饰地透露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情况在这批学者中并不罕见,当然更多情况下则是从他们的论断中隐约地透露出来。
影响传播1887年艾约瑟(J.Edkins)发表《日本传说中的波斯因素》一文,列举了日本神话与波斯传说及口传历史间的六点相似之处,试图以此说明波斯信仰在古代东亚得到了广泛传播。(6)当时的评论者围绕文化因素影响传播的问题展开讨论,并普遍认为艾约瑟在论文中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支撑"波斯因素影响了日本神话传说"这一论断。("Minutes",1889:v)1896年刊发的《希腊-波斯艺术对日本艺术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Greco-Persian Art on Japanese Art")认为欧美思想与文化对日本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亚利安人种的智慧与思想最初被引入日本时刺激了日本民族的审美品位,并给日本艺术与文化以很大推动。"("Minutes",1896:156)作者也承认日本原有的文化基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日本吸收西方影响后在某些方面的发展程度远胜于欧美本身。
1910年劳埃德发表的《希腊箴言集》("A Sutra in Greek")一文提到了佛教与基督教的关联,但评论者指出这种关联不过是推测。如果没有坚实的事实依据说明基督教能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相隔遥远的佛教,那么反过来也可以说佛教也影响过基督教,或者至少基督教与佛教从共同或类似的资源中引发了神话思考。
("Minutes",1910:83)谈到文学的影响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影响源、受影响者以及影响的授受双方有迹可循的联系。历史上不同因素的不断混和会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忽略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突出某一方面的影响有简单化之嫌。在探讨不同文化间偶然出现的类似现象时最好限制使用"影响"这一术语,因为类似现象的存在并不必然意味着事实联系,偶然的相似通常是具有共同本质属性的不同文化平行发展的结果。即便在处理存在着事实联系的文化传递与接受时,也应当关注对外来观念有意识吸收的情况,接受程度的不同与接受者的主体性决定了不加节制地使用"影响"易形成误导。
《鬼取瘤事》与《诺克格拉夫顿传说》确实比较接近,但尚没有足够证据能证明一方影响了另一方,那么既合理又可以接受的判断是日本与爱尔兰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分别形成了各自的故事形态。至于两个故事在内容与寓意方面的类似,则是基于人类共同的惩恶扬善心理。因为从世界范围看,民间故事是具有共性的存在,一般都能够超越时代、地域与文化的差异。
在跨文化理解与沟通的过程中,常常需要以"比较"作为方法。但比较是非本质主义的,亦即作为研究方法的比较不是唯一的,因而不具备排他性,甚至也不是首选项,应该始终坚持历史的、个别文化的深层研究必须先于比较研究。比较旨在引入一种外在的他者视角,根本而言它拒绝对他者全部或持久的占有,因而比较本身也可以是自我否定的方法。比较作为方法应规避盲目比附与生拉硬扯造成的一方影响另一方的关联,而着眼于从异同比较出发寻求深入理解与更好的沟通。
概括而言,比较作为方法要求研究者既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又有恢宏的视野,还要有一种纯正的比较理念。比较应摒弃偏狭与极端,克服事物一成不变的僵化思维,避免材料取舍时的畸轻畸重,警惕分析阐释中的有意误读,而着力培育开放性与主体性兼备的综合思维,努力打通横亘在不同文化之间、古今时代之间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通过比较搭建跨文化理解与沟通的平台,秉持一贯万殊、和而不同的理论自觉,既深化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和认识,又取异质文化的精义补足自身,实现双向互动与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