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是纯洁纯粹的, 这在他们的相遇、翠翠的梦以及傩送对碾坊的拒绝等事情上表现了出来。它的不确定的结局既是命中注定的悲剧, 又最大程度地体现了普通人的生命韧性与强度。
关键词: 边城; 翠翠; 傩送; 人性;
Abstract: the love between Cicui and Nuosong is pure and just sheer, represented by some things such as their meeting, Cicui’s dream and Nuosong’s refusal.Its uncertain ending is not only predestined tragedy but also the embodiment of humanistic strength.
Keyword: “The Border Town”; Cicui; Nuosong; humanity;
与大一新生讨论《边城》, 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翠翠和傩送到底是不是在恋爱?按照学生们的想像与理解, 男女恋爱要送玫瑰花啊, 要出去吃饭看电影啊, 最重要的是要勇敢地说出“I love you!”可是这篇小说里什么也没有。这逼迫我不断地从文本中搜寻翠翠和傩送相恋相爱的文字证据。当然, 我也会提出我的问题, 紧接着前面的问题而来:既然翠翠傩送相爱, 且边城景美人美情美, 为何最终却是一个悲剧的结局?
本文所谓“正解”, 不是奢望本文的解释是唯一正确的, 但要求是正面而全面的理解、以文本为依据与归宿的理解与回答。当然, 本文能最终完成, 且完成得是这个样子, 得益于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作为对话者。因此, 在正式进入本文的论述之前, 首先感谢他们是必要的。
一
蓝棣之说:“《边城》这部小说最有价值的, 是写翠翠作为少女的成长过程, 写她怎样长大的”[1]202, 进一步说, 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翠翠与傩送的相遇、相爱、相知与相守。刘洪涛说:“翠翠的爱情, 萌生得简单, 来得爽快, 第一次见到二老, 一颗芳心就为之倾倒。二老对翠翠也是一见钟情”[2], 这个概括严重损害了二人邂逅时的曲折而复杂、微妙又美妙的内心感受。别的不谈, 翠翠那颗芳心是怎么倾倒的?龙永干分析得复杂些, 他抓住二人初遇时的一个细节:
那就是吊脚楼上的妓女的胡闹与两个水手的对话所形成的“性”的语境, 让其“不习惯”的同时, 给其性的觉醒与紧张。当傩送邀她到他家点了灯的楼上去, “她以为那男子就是要她上有女人唱歌的楼上去”。在其潜意识中傩送是性的侵入者, 潜意识深处也成为她性付出的指向对象。一旦这种紧张排除之后, 能干、漂亮、热诚、善良的傩送也就变成了爱的对象的最初图式, 傩送也就在她心—性意识中成了难以抹去甚至无法替代的先见[3]。
这个解释虽有新意, 但仔细推敲之后我们会发现它其实过于简单而粗糙。我们承认精神分析是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 但我们需要的是整体而全面地解读。
翠翠与傩送初遇于两年前的端午节。热闹的端午节似乎就是为了促成二人初遇 (后来香港的陷落是为了成全白流苏与范柳原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之) 。这颇有辛弃疾《青玉案 (元夕) 》的意境:热闹绚烂的元宵佳节, 属意于某位佳人, 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 她却在灯火阑珊处。不同的是, 翠翠傩送并非有意地相互追寻, 他们无心邂逅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天意玉成。唯命中注定如此, 相遇才更值得珍惜、更值得回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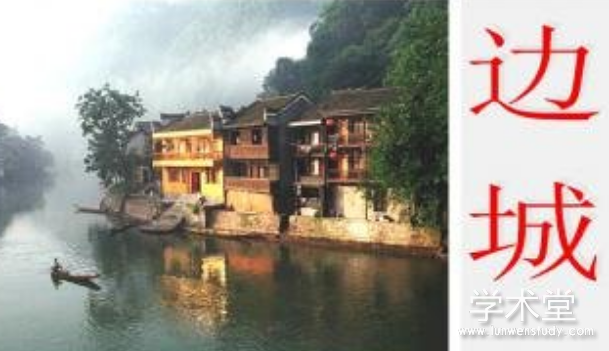
那天, 祖父带翠翠进城河边看赛船。后返回溪边, 临走告诉翠翠无论如何他会来找她一起回家。到了黄昏, 祖父还不见来, 翠翠在岸上苦等, 忽然冒起了一个怕人的念头:“假若爷爷死了?”这是亲人爽约、久等不来的一种自然的心理反应。其时, 因为责任所在, 祖父正守着渡船不能离开。正是祖父这样“死了”, 才给了翠翠孤身等待的时间, 她才与河中捉鸭的傩送相遇。所以, 值得考虑祖父为什么这样“死了”——祖孙俩进城之前, 找了个朋友守渡, 祖父返回溪边是想替换朋友让他进城看热闹, 朋友却愿意和祖父喝酒, 后来醉倒了。祖父只得守着渡船, 让翠翠担忧他“死了”。在此过程中, 祖父是出于好意, 朋友亦无过错, 然而却使翠翠陷入了孤单与焦急的不利状态。祖父不想造成这样的局面, 朋友亦不想, 然而它却发生了, 这就是人事的不谐, 这就是运命的安排。明白这一点很重要:边城景美人美情美, 然而并不缺少悲剧的种子。后来祖父真的死了, 翠翠接管撑渡的责任, 傩送却不在了。彼时的傩送恰如此时的爷爷, 他“也许永远不回来了, 也许明天回来”, 换成类似的表述就是——“假若傩送死了?”自始至终, 死神的幽灵在《边城》游荡, 运命的力量在《边城》徘徊。
“爷爷死了”的念头在新的情境下又出现了。那是在傩送上岸之前, 翠翠听到船上两个水手说话, 事关吊脚楼上唱曲的女子, 用语粗鄙, 翠翠:
很不习惯把这种话听下去, 但又不能走开。且听水手之一说楼上妇人的爸爸是七年前在棉花坡被人杀死的, 一共杀了十七刀, 翠翠心中那个古怪的想头:“爷爷死了呢?”便仍然占据到心里有一会儿。[4]81
因为爸爸死了, 楼上的女人才从事着现在的职业, 做着“丑事”;这时“爷爷死了”的念头在翠翠心中盘桓, 暗示了翠翠当时的心理活动:如果爷爷死了, 我能干什么呢, 是不是也要被迫沦落风尘, 像楼上的女人一样?翠翠最关心的是谁做她的保护者。目前能提供保护的只有她的祖父, 所以翠翠忍着难堪也要等待。应该说, 翠翠担忧祖父之死是不想成为妓女;妓女的故事使她更加担心爷爷死了。安全与生存的需要比所谓“性的觉醒与紧张”更贴近文本原意。
“爷爷死了”的念头萦绕未去, 水中傩送慢慢游近岸边, 喊船上水手, 水手“在隐约里也喊道:‘二老, 二老, 你真能干, 你今天得了五只吧?”, 既然翠翠先前能听到水手说话, 这时的喊话也必定能听到, 可奇怪的是“二老”这个称呼根本没引起她的注意。直到后来二老派人打火把送她回去, 她才惊讶地明白过来水中人就是本地大名鼎鼎的傩送二老。这表明翠翠此时只把爷爷当作唯一的保护者, 她不知道 (也不敢想像) 爷爷死了之后谁来保护她, 更不会把傩送与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但也正因为翠翠不知道当时站在自己眼前的人就是傩送, 二人的初遇才留下了越想越有味的事情 (场景) , 仿佛事情 (场景) 之发生就是命中注定。
二人在码头上相遇。问明眼前是撑渡船的孙女, 傩送说:“到我家里去, 到那边点了灯的楼上去, 等爷爷来找你好不好?”傩送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到我家里去, 我家就在那边点了灯的楼上;可是翠翠并不知道他就是傩送二老, 且“吊脚楼有娼妓的人家, 已上了灯”, 傩送请翠翠“到那边点了灯的楼上去”, 翠翠就误以为是叫她到有娼妓的人家去。傩送出于好意的一句话, 到了翠翠那里却发生了误会。明白这一点也很重要:《边城》里的人个个都是好人, 即便是娼妓也比都市里的绅士更可信任, 可是, 主词“我”的主观性、话语的歧义性、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并不因为人人是好人而减少乃至消失, 在《边城》与在都市一样并不缺少误会的影子。当然, 误会的效果并不全都是坏的。黄狗向傩送吠叫, 翠翠便喊:“狗, 狗, 你叫人也看人叫!”翠翠意思仿佛只在告给狗“那轻薄男子还不值得叫”, 但男子听去的确是另外一种好意, 男的以为是她要狗莫向好人乱叫, 放肆的笑着, 不见了。[4]82
可以说, 是运命 (祖父又称之为“天意”) 安排了这次初遇, 又是误会 (最大的误会是翠翠竟然不知眼前的男子是傩送) 使相遇变得曲折有味, 从而种下情愫。
在翠翠与傩送的互相误会之间, 是二人的一次“笑骂”:翠翠说:“你个悖时砍脑壳的!”这句粗话诅咒人倒霉, 遭报应;傩送则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 可不要叫喊救命!”比起“白鸡关出老虎咬人”, “水里大鱼来咬了你”更像是一句玩笑话, 让人感觉到一种特别的温柔与浪漫。傩送本人不正是一条刚上岸的从水里来的大鱼吗?他正用误会的嘴咬住了翠翠。有意思的是, “咬”字在后面的叙述中几乎都被换成了“吃”字, 如翠翠到家后自言自语:“翠翠早被大河里鲤鱼吃去了”。我压抑住这样一种解释冲动, 即把“吃”视为性行为的隐喻性表达, 性行为常被描写成一种野蛮的吃人行为, 即男人吞掉了女人的行为, 有人就是这样来解释小红帽被大灰狼吞吃的那个童话故事[5]。因为“吃”的叙述来自翠翠, 它传达的其实是翠翠沉浸在对初遇情境的回忆与咀嚼之中, 水里来的大鱼傩送完全占据了这个小女孩的心灵。“吃”表达的是全身心投入的爱。
翠翠整个地被两年前的端午节的这次相遇给“吃”了。上年的端午节, 翠翠又遇到了打火把送她回家的伙计, 她说:“爷爷, 那个人去年送我回家, 他拿了火把走路时, 真像个山上的喽罗!”翠翠想说的是:派这个人来的傩送二老就是山寨大王, 她就是压寨夫人, 展开了英雄美人的少女幻想。傩送下了青浪滩, 大老天保送他们一只肥鸭, 翠翠根本不在意, 而是忽然问道:“爷爷, 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还有一次, 翠翠说的话更是无头无脑:
翠翠想:“白鸡关真出老虎吗?”她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白鸡关。白鸡关是酉水中部一个地名, 离茶峒两百多里路![4]95
且翠翠还“轻轻的无所谓的”唱着歌:
白鸡关出老虎咬人, 不咬别人, 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 二姐戴副银钏子, 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 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4]95
连翠翠本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想起白鸡关, 恐怕多数读者也都在云里雾里。但在不久之后的段落中, 傩送为送酒葫芦来到翠翠家, 祖父问他:
“我听船上人说, 你上次押船, 船到三门下面白鸡关滩口出了事, 从急浪中你援救过三个人。你们在滩上过夜, 被村子里女人见着了, 人家在你棚子边唱歌一整夜, 是不是真有其事?”
“不是女人唱歌一夜, 是狼嗥。那地方着名多狼, 只想得机会吃我们!我们烧了一大堆火, 吓住了它们, 才不被吃!”[4]100
原来, 爷爷早就听说了傩送下白鸡关的事, 把它告给了翠翠。“白鸡关”就占据了翠翠的意识中心, 集合起来丰富而复杂的情绪心理:首先, 她心系傩送, 傩送走到哪里, 她的心思就飞到哪里, 正如一首歌所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其次, 传闻白鸡关的女人追傩送, 翠翠心里不痛快, 就想像白鸡关出老虎, 老虎先要吃团总小姐——她是翠翠近在眼前的情敌, 家里富有, 以碾坊做陪嫁, 翠翠便用想像除掉了她。
今年的端午节, 二老邀祖父与翠翠看龙舟。当爷爷想说:“二老捉得鸭子, 一定又会送给我们的”, “话不及说, 二老来了, 站在翠翠面前微笑着。翠翠也不由不抿着嘴微笑着。”还有比这相视一笑、莫逆于心更动人的感情吗?对翠翠与傩送的爱来说, 话是多余的。当代大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所熏染的娱乐文化皆鼓励说话、鼓励表达, 能秀的就要秀出来, 这与傩送翠翠心领神会的表意方式大相径庭。他们看不懂傩送与翠翠的爱, 实质上是还没有真正明白人的诗意存在。
二
在翠翠与傩送定情相爱的同时, 他们也面临着压力与考验:一是天保大老也喜欢翠翠, 并请人做媒;一是王团总中意傩送作女婿, 陪送一座崭新碾坊。
对于第一个冲突, 兄弟俩的解决方式是二人隔溪轮流唱歌, 谁得到回答谁就得到翠翠。傩送开口, 天保即知道自己竞争无望, 驾船出走, 淹死了。而翠翠沉浸在傩送的歌声中做了一个梦:
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 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 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 上了白塔, 下了菜园, 到了船上, 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 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悉。崖壁三五丈高, 平时攀折不到手, 这时节却可以选顶大的叶子作伞。
……
“爷爷, 你说唱歌, 我昨天就在梦里听到一种顶好听的歌声, 又软又缠绵, 我像跟了这声音各处飞, 飞到对溪悬崖半腰, 摘了一大把虎耳草, 得到了虎耳草, 我可不知道把这个东西交给谁去了。我睡得真好, 梦的真有趣!”。[4]121-2
陈思和说:“那几个人都紧张地醒着, 唯有翠翠一个人在昏睡, 在做梦, 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梦, 感到灵魂飘起来, 但是, 翠翠始终停留在梦中, 她没有对歌声发出爱的呼唤, 她的心灵没有跟这种声音发生真正的呼应。所以, 这里最知趣的是天保。天保终于有了做戏的虚无感, 他要退出这样一个荒诞的游戏, 后面就出事死去了。在人人讲道德的环境下, 翠翠的生命和爱情, 包括两个青年有血有肉的爱情都到哪里去了?看上去非常文明非常有节制的一个文化和社会环境, 年轻人的生命冲动或者生命力量最终被压制了, 消失掉了。悲剧就出现了。”[6]107-8这种解释的疑问是:翠翠听到歌声, 梦中灵魂就飘起来了, 难道这不就是翠翠对傩送歌声的“真正的呼应”吗?难道只有翠翠起来唱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才是“真正的反应”吗?如果女孩子第一次听到异性的歌声就作如此反应, 是不是又要说这女孩子不要脸?要用持续的努力、要唱三年六个月的歌来打动女孩的心 (“把翠翠的心子唱软”) , 绝非仅凭一晚上的工夫。此外, 天保傩送走马路唱歌是竞争的游戏而非“荒诞的游戏”, 有竞争就有失败, 傩送一开口, 天保就明白自身处于绝对的劣势, 根本没有胜利的希望, 哪里涉及到文化社会环境对年轻人生命冲动的压抑?
赵园说:“梦中被歌声浮起来, 是都市少女也可能有的经验, 但飞到悬崖半壁‘摘虎耳草’的, 却只能是山里水边长大的摆渡人家的翠翠。这一笔本色, 亲切, 贴近人物, 惟沈从文才能写出。小说第17节写翠翠在‘微妙’的心情下又摘了一大把虎耳草——正与前面的描写照应。虎耳草, 俗称‘金丝荷叶’, 属多年生草本, 夏季开白花, 可供观赏, 也可入药。”1[7]虎耳草的植物学形状与歌声和灵魂可有什么关系?难道写“摘虎耳草”就是为了体现出翠翠与都市少女的区别?
蓝棣之说:“虎耳草象征一种可以触到的希望, 象征一种保护, 但翠翠得而复失, 快乐的梦里含有不祥之兆。”[1]207虎耳草生长于悬崖半腰, 平日里够不着, 如何象征“可以触到的希望”?翠翠梦中拿虎耳草作伞, 可以认为象征着遮挡与保护, 但这种解释便与梦中飞起来相抵牾, 飘浮在空中不是比脚踏实地更加危险吗?解释需要全面客观地把握文本, 至少不能自相矛盾。
本文认为, 这个梦整体上表达了翠翠与傩送之间的爱是纯粹的、刻骨铭心的, 这样的爱追求的是精神上的愉悦和灵魂上的诗意享受!根本无关乎任何俗世生活与现实利益的考虑。相形之下, 大老的爱就太平常太无趣了, 他要的是个照料家务的好媳妇, 其动机与目的完全受到现实生活的支配。听着傩送的歌声, 翠翠的灵魂浮了起来, 飞了起来——飞, 是对沉重现实的超越, 是大自由与大解放的状态;借着歌声, 翠翠完成了日常生活中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摘悬崖上的虎耳草 (不是轻巧的玫瑰花) , 这充分表现了翠翠因梦而得、因爱而生的喜悦感与满足感 (“我睡得真好, 梦的真有趣!”) 。如是理解当较之前诸说更令人满意些。
三
车路马路的冲突, 以天保之死作为结束, 但它却为傩送与翠翠的爱情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是故事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天保未死之前, 傩送明确地说:“第一件事我就不想作那个碾坊的主人!”[4]108;天保死了之后, 他就变得犹疑起来:“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 还应当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因为祖父令他生气:“我想弄渡船是很好的。只是老的为人弯弯曲曲, 不索利, 老大是他弄死的。”
《边城》悲剧的一个肇因便被派给了祖父。据陈思和先生的看法, 边城人是“非常豪爽, 非常坦诚的”[6]106, 以此为例:
大老对二老说:“二老, 你倒好, 作了团总女婿, 有座碾坊;我呢, 若把事情弄好了, 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来划渡船了。我欢喜这个事情……”可是二老和他哥哥一样, 也是很直爽, 说:“假若我不想得这座碾坊, 却打量要那只渡船, 而且这念头也是两年前的事……”两兄弟把话说得都很清楚, 还说, “你信不信呢?”这么下去会是多么精彩多么尖锐的冲突![6]108
祖父说话则“绕来绕去”, 表现得很有机心:“明明知道唱歌的是二老, 还跟翠翠讲故事说:‘假若那个人还有个兄弟, 走马路, 为你来唱歌, 向你求婚, 你将怎么说?’绕来绕去, 把大家绕得都误会了。这里的人都没有那么多的心机, 常常直来直去的, 他这么绕来绕去, 很有文明人的样子, 人一讲文明, 事情都搞乱了”[6]106。
上述解释和大多数论文一样, 按其自身的逻辑看, 说得很有道理, 可若细心读一读原文, 就会发现是断章取义, 不能服人的。比如大老二老不是边城人直爽的代表, 而是有着“情敌见面, 分外眼红”的普通心理与样子, 这事上说话能不直爽吗?再者, 怎样才算是“直爽”呢?大老说话并不这样直白爽快:“兄弟, 我喜欢翠翠, 你别跟我争!”二老也没有:“大哥, 我早就喜欢翠翠了, 咱们决斗吧!”而是用“假若”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这跟祖父对翠翠说的那个“假若”有区别吗?祖父用“假若”表达的意思很明白了, 翠翠能不理解吗?——边城人固然“没有那么多的心机”, 但他们本质上和我们一样, 彼此不是完全透明的, 智商与情商也是正常的。
陈思和先生的解释是按着“自然/机心”之间对立的思路来推进的 (显然这个思路对《边城》来说是不合适的) 。说话直爽是“自然”的, 祖父不直来直去则是一种“人为的心机”:“一个自然的世界当中不应该有一种人为的心机在中间起作用, 有了心机就不自然了, 不自然就把事情搞坏了, 最后导致了一系列的说不出原因的悲剧。老祖父枉费了心机, 最后什么都没做到, 郁郁而死了”[6]107。这里的问题是:边城民风淳朴, 未受现代商业文明的 (严重) 污染, 堪称一“自然的世界”, 但“自然的世界”里的人事是否就得是“直来直去”的?至少《边城》里的爱情可以直来直去, 也可以不直来直去:前者是车路, 后者是马路;前者由人直接去说媒, 后者自己去唱歌, 直到打动心爱的人为止。涉及人心感情, 弯弯绕绕是少不了的 (前面说过, 边城并不缺少人事的不和与误会的发生) 。并且, 与陈思和先生说得相反, 按照精神分析的看法, 文明人刻意压抑性本能与暴力倾向, 他们才显得弯弯绕绕呢。实际上, 我们更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祖父办事“不索利”。
陈思和先生认为, 翠翠母亲与屯戍兵恋爱的时候, 大家都很直爽, 祖父不愿意女儿嫁给当兵的, 因为当兵的要开拔, 要离开自己, 于是横加阻挠, 造成了女儿自杀的悲剧。因此, 他吸取的教训就是在翠翠的事情上“变得小心翼翼”, 吞吞吐吐[6]105-106。这个解释并不符合小说本意。首先, 翠翠父母是在未认识之前对歌相熟的, 而后发生了关系, 女方怀了身孕——看来也并非是“直来直去”;其次, 祖父不愿意女儿嫁给当兵的, 这一点无法从文本叙述中得出;即便这个猜测有道理, 但说祖父横加阻扰则是无中生有。因为祖父知情是在女儿怀了孩子之后, 他“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 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 仍然把日子很平静的过下去”;再次, 屯戍兵因见情人不愿离开父亲且自己也不愿意破毁做军人的荣誉, 在一场急病中死去了;情人之死才是翠翠母亲后来自杀的最重要的推力。在整个过程中, 老船夫表现得忠厚仁道, 并未施加任何的刺激与打骂, 更重要的是他对女儿的私生女加倍呵护, 活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 手续清楚”, 以此补偿上天对女儿的不公平, 所以在翠翠嫁人的事情上, 才变得小心翼翼。
祖父的意图 (动机) 是善良与美好的, 然而事情从一开始就不是他能左右的。是在他“死了”的情况下, 翠翠邂逅了傩送, 种下一生情愫, 此事他不晓根底, 根本不能施加任何影响。他见到的是天保追求翠翠, 他想的是:“翠翠若应当交把一个人, 这个人是不是适宜于照料翠翠?当真交把了他, 翠翠是不是愿意?”。当地人以为, 翠翠的婚事由祖父作主, 中与不中, 就听祖父说一句话。他们, 包括把天保之死归咎于祖父的傩送, 皆错怪了祖父2。如果此事由祖父完全作主, 他也说话痛快, 要么“行, 翠翠嫁给天保”, 则违背翠翠意愿, 二老受伤, 亦难免负气出走;要么“不行, 翠翠嫁给傩送”, 则天保不能如愿, 还是要走上淹死的道路。与其怪祖父如何如何, 不如怪兄弟俩何以都爱上同一个翠翠——但这也怪不得, 因为这就是命运与天意。这本是一个很通俗的三角恋故事, 不过在男女感情之外纠缠着手足亲情。前者是排他性的 (照茶峒人规矩, 两个男子要动刀子) , 后者是亲和性的。圆满的、皆大欢喜的解决方式只有一女侍二夫, 其他方式皆会造成人伦悲剧。把《边城》悲剧的原因派给祖父才是不公平的。
祖父说话不那么直接痛快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与顺顺和王团总比较起来, 他和翠翠属于穷苦人家、处于弱势地位。“有钱船总儿子, 爱上一个弄渡船的穷人家女儿, 不能成为希罕的新闻”[4]115, 但更不希罕的, 是有钱人与穷人的言行举止是不一样的。在小说第十九章, 病刚好的祖父进城见顺顺, 顺顺正同人打牌, 他只得站在旁边等候, “顺顺似乎并不明白他等着有何话说, 却只注意手中的牌”, 有人认为顺顺的这种态度“正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对于普通人的优越感的微妙表现!”[8]本文认可这个解释, 且要补充介绍老船夫为什么得病:王团总派人来探问口风, 那人过渡时有意说谎, 对老船夫说傩送会打算盘, 要碾坊不要渡船, 老船夫为此才病倒了三天。王团总可以派人去探口风, 而老船夫只能自己去当面问, 这就是二人的差别。
老船夫是穷人, 称翠翠为“光人”。面对财主家小姐手上的银手镯, 翠翠不免露出歆羡之意;面对摇撼不动的碾坊, 翠翠只能在“白鸡关”的歌中用老虎咬死团总小姐。现实中的贫乏与无能为力, 只能通过想像来解决问题, 这就是“绕”。翠翠难免绕, 我们更要理解老船夫不得不绕:面对碾坊的诱惑, 他不知道顺顺与傩送到底怎么想、怎么选择。他面对的不是顺顺是不是好人的问题, 而是“人心隔肚皮, 做事两不知”的难题, 这叫他如何直接痛快地说话!诚如刘洪涛所言, 《边城》是沈从文在人性善基础上构建的一个纸上乐园, 这个乐园构想投射到了人物性格、人际关系、茶峒社会与习俗、甚至自然环境等各个方面, [2]然而, 边城非但不是个世外桃源, 并且里面的人仍然只是个人, 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种无毛两足动物的最普通最平常的喜怒哀乐、它的存在的有限性与悲剧性从来就没有因为边城里的人是好人而减轻过或减少过。对此, 《边城》叙述中流露出来的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 而陈思和的分析传达的则是一种个体思想性的批判。
换一个角度看, 人物说话绕正与《边城》含蓄的抒情方式、有味的隐喻性表达相契合。通过前面对初遇场景和摘虎耳草梦的解读, 我们会发现沈从文写作《边城》的叙述方式就是绕的。因为绕, 《边城》才有田园牧歌情调, 才是一首抒情诗。
四
《边城》开始两章予人印象太美, 往往使人忽略了叙事开始时就埋下的死亡气息。无论边城民风如何淳朴, 改变不了一个事实, 即翠翠是个遗腹子;即便这个遗腹子“从不想到残忍事情, 从不发愁, 从不动气”[4]67, 也无法改变她的出生源于一场爱情悲剧的事实。悲剧先于翠翠而存在, 翠翠身上流着悲剧的血液。起初, 她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但这并不妨碍死亡的来临:两年前的端午节就起了“假若爷爷死了”的念头。这个念头也存在于爷爷的心中, 他自称不久就要“喂蛆吃”[4]101, “打量着自己被死亡抓走以后的情形”[4]126。等天保突然死去, 这使祖父很惊讶, 因为“从不闻水鸭子被水淹坏的”, 杨马兵则说:“可是那只水鸭子仍然有那么一次被淹坏了”——“仍然有那么一次”, 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这就是人存在的偶然性。沈从文另一篇小说《菜园》里的一句话, 用在这里也合适:“命运把一件事情安排得极其巧妙”。天保之死使得老船夫失去了往日的从容, 使得二老父子明白老船夫的意思但又“俨然全不明白似的”, 要么不说话、不理会, 要么叫老船夫闭嘴。这予老船夫的心灵重创可想而知, 在一个雷雨夜他也无声息地死去了。这样, 凡与翠翠有关的人, 凡爱着翠翠和翠翠爱着的人, 要么非正常地死亡 (翠翠父母、祖父、天保) , 要么不知死活 (傩送) 。死神一直纠缠着翠翠。边城里的人“除了家中死了牛, 翻了船, 或发生别的死亡大变, 为一种不幸所绊倒, 觉得十分伤心外, 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 似乎就还不曾为这边城人人民所感到”[4]75;确实, 边城没有统治者的剥削压迫, 没有军阀混战与土匪横行, 但这里并不缺少死亡和死亡带来的伤心。虽然边城人不惧死亡, 所谓“对付仇敌必须用刀, 联结朋友也必须用刀”[4]74, 但他们并不能痛快地忘掉死亡:祖父忘不掉翠翠母亲, 翠翠忘不掉祖父, 二老父子忘不掉大老——亲人的死亡照样改变他们的心态与举止, 使他们有所怨憎, 阻止了美好如愿生活的最终实现。换言之, 边城生活其实也是一种充满龃龉与分裂的生活, 人美景美情美的世外桃源也不能达成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这种存在状态其实更让人恐惧, 因为边城里的死亡并非由某种可见的外力 (如被统治者、军阀或土匪杀害) 造成, 《边城》的叙述归咎于不可见的运命或天意。如果死亡由某个具体的统治者造成, 那么人们可以起来反抗他;如果由运命或天意造成, 反抗该如何进行?公平会如何实现呢?当然, 《边城》把悲剧归咎于运命或天意, 并不是悲观的宿命论思想, 而是要像祖父反复叮嘱翠翠的那样, 承担着自己的那一份命运, 硬扎结实地活在这块土地上, 一切要来的都得来, 不必怕!这也迥异于当时流行的革命乐观主义思想, 却最大程度地体现了普通人的生命韧性与强度。
作为爱与被爱的焦点, 翠翠沉浸在对美好初遇的回味与摘虎耳草的梦境之中。她从梦中醒来的代价就是祖父的死去。她继承了祖父的工作, 继续在碧溪岨撑船, 既不离开祖父的坟墓, 又等着傩送回来;既可看成是对爱情的坚贞, 亦是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同时继续着祖父对不公平摊派的抗争! (我们或许可以体味到翠翠孤单撑船的身影里面寄寓了作者沈从文沉默而坚韧的人格气质) 因此, 《边城》的结局是悲剧性的, 然而又是用人性的坚韧超越了悲剧的。
参考文献:
[1]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202.
[2]刘洪涛.《边城》与牧歌情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1 (1) :72-93.
[3]龙永干, 凌宇.“自然人性的纯化、规约及其困窘:《边城》创作心理新论[J].民族文学研究, 2013 (3) :94-100.
[4] 沈从文.边城[A]//现代中篇小说选 (三) [C].北京:宝文堂书店, 1984.
[5]埃里希·弗洛姆.被遗忘的语言[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7, 163-164.
[6]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7]赵园.《边城》——一个关于水的故事[A]//《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着导读》自学指导[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01.
[8]陈永志.论《边城》的悲剧特色及其意义[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1991 (2) :112-116.
注释:
1 赵园的解释是把虎耳草作为一种植物来看待, 而蓝棣之则把它解释为希望的象征, 因为它出现于翠翠的梦中--梦中的事物可以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 而解释不可避免地带着解释者本人的主观趣味, 很难达到全面而完美的统一。本文提供另一种解释:虎耳草, 拉丁文直译为“割岩者”, 耐性强, 喜欢生长在背阳的岩石裂缝处, 久而久之, 或可割开岩石。这似乎预示了翠翠傩送爱情的结局:天保死后, 傩送虽然爱着翠翠, 但以为是翠翠祖父弄死了哥哥, 这是他心中的一个硬结, 即盘踞在他心中一块岩石。要化开他心中的结, 需要的就是时间和耐性, 需要等待, 像虎耳草割开岩石那样。
2 与祖父不能决定翠翠的婚事类似, 顺顺也不能决定傩送的去向, 他也得照顾到傩送的意见, 傩送同他争吵, 下桃源走了 (详见小说第十九章) 。可见, 怪老船夫弯弯绕绕, 不能痛快决定翠翠的婚事, 实是片面之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