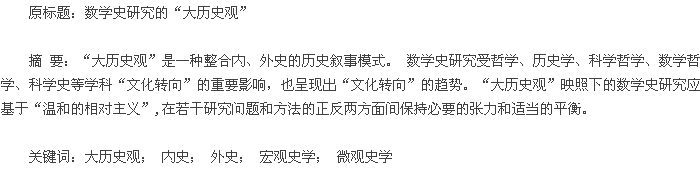
引言
近年来,数学文化研究与教学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并从大学蔓延至中小学,为数学史研究与教学走向“内史”与“外史”融合提供了契机,数学史研究出现“为文化而历史”的转向,[1]数学史研究呼唤整合内、外史的“大历史观”.
1 何谓“大历史观”
西方从古代到 20 世纪的大部分历史着作一般都是“通史”类的,或称之为“普遍史”、“整体史”( Uni-versal history) 的观念,这是西方历史编纂学的经典传统,“文化史”研究在 18 世纪的德国就已经出现,19世纪英国和德国开始的“文化”、“文明”的历史研究,引发了历史上的“文化之战”( Cultural Wars) . 20 世纪出现“新文化史”,新、旧文化史的区别就在于“旧文化史”希求解释文化的时代变迁,而“新文化史”则倾向于描述孤立的、微小的事件和人物,也即所谓的“微观史”( Microhistory) . 西方历史学家们逐渐开始避免讨论宏观的历史趋向问题,企图“解构”( Deconstruct) 原来的解释框架,可以看到这种发展趋势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后,历史学家开始了区别“大写历史”( History) 和“小写历史”( history) 的工作,“大写历史”是对历史进程的思考和总结,是启蒙运动思想的产物,坚持“历史是一个有头有尾的过程”的基本假设; 主张历史总的方向是进步的,是向上、向前发展的; 认为“历史总是有意义的”. 这一观念也可用“宏大叙事”( Grand Narrative) 来表述。 史学家想展现一个更为重要、更为宏大的对于历史进程的思考。“小写历史”就是考虑在具体写历史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属于历史认知或历史认识论的问题,这是后现代主义提出来的。 西方后现代史学的特征就是放弃了“大写历史”的传统,历史学家安克斯密特( FrankAnkersmit) 曾用一棵大树来形容西方史学,历史学家原来更注重研究树干是如何延伸的,现在秋天到了、落叶缤纷,历史学家的研究取向从树干转向每片树叶了。 后现代的“小写历史”趋势更倾向于分析化和实证化,走向研究一片片“树叶”而且还会有意欣赏树叶的色彩斑斓、五彩缤纷。 这种后现代史学观念对中国史的研究也有深刻影响,例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等篇幅不大、事件也小的历史着作。 着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也有《万历十五年》这种历史着作,但他对于中国史研究却是基于一种“大历史观”( Macro-history) ,试图“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2]
西方现代史学的困境就是“大写历史”的瓦解和“小写历史”遇到的一些研究困境,但却为“世界史”、“全球史”的兴起创造了契机。 全球史家希望能寻找到理解人类发展状况的钥匙: “超越过去几个世纪的曲解,透过帝国和霸权遗留下的表面结构洞察其本质,以此来理解在全部历史中塑造人类命运的力量,并且预测未来。 ”[3]
全球史与历史学的碎片化之间的关系恰好折射出史学的未来发展前景。 柯娇燕( PamelaKyle Crossley) 指出,从来只有两种史家,一种喜欢做宏观的考察,而另一种偏重微观的研究。 而这两者之间又常有交流和互动。 微观和宏观研究之间、历史的碎片化与全球化之间可以相互补充、交流甚至融合。 未来的史学发展虽然难以预测,但呈现出一些线索: 一是全球史本身具有巨大的潜力和活力,史家如能跳出民族国家的视角来考察历史现象,就能创造出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 二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史学总体呈碎片化发展,但随着全球化的高歌猛进,已然出现整合的趋势; 三是当今的全球史研究还跟过去的世界史和宏观史研究不同,历史学家不一定非得对历史的总体走向作出笼统概括和规律性预测,可就某一历史时期、世界各地区都有过的文化历史现象,给出跨民族、跨地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和不同的理解。[4]
近年来,自然科学史中也出现了“大历史”的叙事模式,并且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更大的时间尺度。 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 David Gilbert Christian) 在《时间地图: 大历史导论》一书中运用众多学科的方法和知识,阐述了他的“大历史”( Big History) 叙事模式。 他把自然科学史和人类发展史结合起来,打破以往人类历史与史前时代的人为划限,拓宽大历史的时间尺度,从不同时段和尺度考察宇宙和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变化,探寻背后的基本规则和发展特征。 为和微观史( Microhistory) 相对照,他也曾使用“Macrohistory”一词来代替“Big History”,但和历史学家使用的有区别,他主张七种不同的时间尺度。[5]
他主讲的 48 集 TTC 课程《大历史: 大爆炸,地球上的生命,人类崛起》风靡全球。 比尔盖茨设立基金资助“大历史项目”,越来越多的美国和澳大利亚高中开始免费学习这一在线课程。 在他的“大历史”中,自然科学史部分涵盖了宇宙大爆炸以来 99. 9%的时间,人类发展史所占时间不足 0. 1%. 而这也是很多历史学者所批判的,“大历史果真能够赋予人生以意义吗?”[6]
他虽然大量使用文化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但却忽视了马克斯·韦伯这类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不同文明的比较研究很少。[7]
总之,“大历史观”无论在全球史学还是在自然科学史领域都成为一种整合历史的叙事模式,其他分支学科的历史研究可以借鉴“大历史观”. 虽然数学学科所研究的抽象对象是不存在的,但其生命本质上是文化的、文明的乃至世界的。 数学与人类的生命起源、种族生存和社会发展等息息相关,数学又与宇宙的起源、行星轨迹和天体结构等紧紧相连,抽象的现代数学可以描述的东西在纵向时间尺度上从宇宙大爆炸、远古到近现代,横向的时空尺度上包括所有的星球结构问题、各个文明的历史社会问题。 数学作为与哲学出于同源、至今比肩的学科,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典范和美学评判。 因而,坚持数学史研究的“大历史观”应该把数学放置在一个宏观的视野下、考虑更大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下的数学历史发展,数学与其他的学科的密切关系也决定数学史研究应该是跨学科、跨文化的。 尤其是数学在古代中国、埃及、巴比伦、印度等各个不同文明、民族文化的发展差异和共性,需要基于“大历史”观念破除以往的“西方文化中心论”去给予客观公正的研究与评判。
2 为何数学史研究要坚持“大历史观”
任何学科的研究范式转换都不是突然的,都经过了长期的孕育、发展和学术共同体对范式的接受和共同遵守。 任何学科也都不是孤立发展变化的,都受到其他学科的影响。 数学史研究受到哲学、历史学、科学哲学、数学哲学、科学史等学科“文化转向”的重要影响,也呈现出“文化转向”的发展趋势。
2. 1 哲学的文化转向
文化哲学是 20 世纪西方哲学发展的重要思潮,是通过早期文化进化论学派、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文化功能学派、文化结构主义学派和新文化进化论学派来实现的。 从总体上看,哲学与文化的结合造就了科学主义文化哲学和人文主义文化哲学两大思潮,并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折。[8]
文化哲学的演变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波普尔、弗雷格等人的努力,也可以清晰地看到逻辑主义、结构主义等哲学流派和数学哲学流派的相互影响。
2. 2 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文化转向”既构成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成形的“新文化史”的灵感源泉,也成为它的研究对象。
[9]
“新文化史”源于 1989 年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 但正如彼得·伯克所指出的,文化史的发展很不平衡,甚至有些参差不齐。 近十年来,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被写成了文化史。[10]
1999年,林·亨特以“文化转向”取代“新文化史”. 海登·怀特在后记中指出: “文化转向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意义在于,它提出在‘文化’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社会现实中的一个适当位置,由此出发,任何特定的社会都能够被解构并表明它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必然。 ”他强调历史文化转向的后现代解构性,并为弥补这种结构的不完美性,提出一种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主义”.[11]
2. 3 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
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是经过逻辑经验主义受到挑战、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实现的。 其独特立场大致是文化学和人类学的立场,即一种广义的文化哲学立场。 科学哲学必须溢出自然科学亚文化的范围而面向整个科学文化,走向科学文化哲学才是真正的出路。[12]
但当科学哲学看来确实处在前进之中,数学哲学为什么看似不前进呢? 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范式对数学哲学的文化研究影响巨大,正如赫斯所指出的: “库恩的名着( 科学革命的结构) 是深入这类科学哲学问题的典范,它只有基于对历史的研究才能成为可能,这类工作必须在数学史和数学哲学领域开展下去。 ”[13]
2. 4 数学哲学的文化转向
拉卡托斯将科学哲学推广到数学领域,提出“拟经验主义”的数学哲学观。 历史主义使人们认识到数学创造在本质上是一个“数学共同体”的社会活动。 社会建构主义数学哲学指出数学归根结底是一种人类活动,它具备人类社会所创造的文化的一切特征[14]. 数学家提出“数学是模式的科学”的哲学观,一个数学模式建立以后,如果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 这取决于实践---社会实践和数学实践的检验) ,就会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成为整个思维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 既要肯定数学的经验性的同时,也要肯定数学的拟经验性。 数学即是对于模式的研究,而思维活动又总是按照一定的模式进行的,因此,我们也应当充分肯定数学研究的普遍的认识论意义,这也就是促使人们去谈及“数学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15]
2. 5 科学史的文化转向
科学史家拉卡托斯在“科学史及其理性重构”中强调科学史的“理性重构”或“内在的历史”. 当历史与它的理性重构不同时,“外史”只是提供了一个经验解释。 以默顿为代表,科学史研究开始从“内史”向“外史”转向。 1982 年,夏平( Steven Shapin) 的“科学史及其社会学重构”标志着科学史“理性重构”开始转向“社会重构”. 科学知识社会学( SSK) 的出现使得内、外史逐渐从争论走向消解和融合。 当时“最有影响的科学史家,以及那些与他们接近的医学史家,承认思想和社会关系的二分法使得人们不可能把任何历史的境遇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16]科学史家开始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开展多样性研究。
2. 6 数学史的文化转向
20 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数学史“外史”研究开始逐渐得到重视。 斯特洛伊克提出“数学社会学”,怀尔德认为“数学是一种文化体系”,M·克莱因指出“数学从来不是独立于文化而存在的”. 中国数学史学者李迪主张研究“大数学史”,“是把数学放在整个社会中,把数学和社会结合在一起,而不是把社会历史拿出来作为背景考虑。 这样,所谓的‘内史’和‘外史’是一个整体,本来就不能分开。 也就是把社会史作为一个系统,而数学史为其子系统,研究时不能脱开大系统,这样才能解释中国数学发展中的许多现象和事实。 ”[17]
早期由李俨、钱宝琮所领导的范式是以“发现”为主旨,吴文俊将范式转换为“复原”. 当前,数学史学者提出第三种范式,即“为什么做数学?”的问题。[18]
这种范式更关注不同社会、不同文化、不同数学家共同体对数学的追求取向问题,出现了研究范式的“文化转向”.[19]
3 基于“大历史观”的数学史研究应注意哪些问题
大卫·布鲁尔( David Bloor) 在科学史方法论上坚持相对主义,提出的“无偏见性”、“对称性”等原则,是值得数学史研究借鉴的,即“应当对于真和假、理性或非理性、成功或失败等来说( 是) 不偏不倚的。 这些对立体的两面同时都……需要解释。 ……且其解释类型上( 是) 对称的。 相同类型的原因……既解释真实信念也解释假信念。 ”[20]因此,在“大历史观”映照下的数学史研究应基于拉里·劳丹的“温和的相对主义”理念,在若干研究问题和方法的正反两方面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适当的平衡。
3. 1 坚持“大历史观”要在内史研究和外史研究间保持必要的张力,避免数学史研究的内外对立和壁垒分明
数学史研究要把数学作为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子系统开展整体性研究,而不应该绝对化内、外史的研究疆域、设置二者间的学科壁垒。 坚持“内史”观的基本立场认为“数学的历史发展主要取决于内在的因素,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可被归结为一种逻辑的必然性,并主要地体现于某些大数学家的某些伟大思想。 ”[21]
这样的数学史研究容易用当代的数学观去评价过去的数学工作,缺乏历史的观点。 事实上,很多历史研究需要内、外史的完整研究才能获得可靠的研究成果,忽略了“内史”研究的“外史”研究容易缺乏学科的根基,尤其是现代数学的抽象程度已非普通历史学家甚至科学史家所能深刻领悟的,需要纯粹数学家的研究基础和详尽阐释,我们才能梳理出一个数学思想是如何诞生于所在的文化传统和学术共同体之中。
同样,缺乏外史研究的内史研究也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得到错误的研究结论。 郭书春教授借鉴科学史中的“文化簇”研究方法指出,长期以来中国数学史中秦九韶“为人阴险,为官贪暴”的观点占有主导地位。
但从“文化整体”的多视角、多维度研究可以看到,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以往单纯采用其政敌刘克庄等人的信札进行研究,得出的对秦九韶“爆如虎狼,毒如蛇蝎”的评价,忽略了宋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大背景。[22]
数学“内史”和“外史”作为数学史的整体也不应该有主次之分,强调内史研究的拉卡托斯曾指出“内部历史是首要的,外部历史只是次要的,因为外部历史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由内部历史限定的”.[23]
这种主张在科学史、数学史研究中有一定道理,但有些外史研究内容对于内史研究也是具有决定性或关键性作用的,外史的研究对于深刻理解一些内史内容也是很有裨益的,例如,Motive 是格罗登迪克在代数几何学中提出的重要理论,被他自己认为是呈献给世人的数学事物中最曼妙和充满神秘的,被他认为是“几何”与“算术”在深层面上的同一所在。 而他与被誉为“现代艺术之父”的保罗·塞尚在绘画中使用的母题( motif)思想,在艺术和神秘感上具有超验性的相似性。[24]
数学家的“外史”研究对于深刻的理解抽象的现代数学概念也是极为重要的。 在开展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时,对筹算数学中所涉及汉字的语言学考据和文化背景分析决定了一条算理的本质意义。 中西方数学史比较研究由于涉及到不同文明、文化中数学发展模式、理论体系、运算规则、符号表达等方面的比较,就更需要内、外史的共同研究才能得出客观的比较研究结论。
3. 2 坚持“大历史观”要在微观史学和宏观史学间保持必要的张力,避免数学史研究的过于精专和宏大叙事
“宏观史学”和“微观史学”两种研究方法各有利弊,宏观史学就像用望远镜观察历史,时间跨度久远,线条较为粗旷,历史场景恢宏,分析因果关系,研究视野虽然比较开阔,但有时难免会得到较为肤浅的研究结论,显得研究深入的力度不够,这种过度的“宏大叙事”每每容易使人只知历史的所以然,而难知其然;微观史学就像用显微镜观察历史,历史事件较小,线条清晰分明,人物案例具体,但有时不免会局限于一隅,不能触类旁通,容易使人只知历史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其然也只是一隅之其然,放置更大范围或从其他视角则不必然也。 当然,这种两分法只代表了史家历史考察法之倾向性,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
尤其在“大历史观”映照下,二者并非泾渭分明,严格划清,而应是互有参杂、互为补充。 在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也就意味着,所谓的“大历史观”在开展宏观历史研究时也只是相对于微观历史而言的,宏观历史并不都是以往通史强调的事件、制度一类的,也不是宏大叙事的宽泛概括,以小见大的微观案例研究更容易帮助理解大历史。[25]
数学史研究中的“微观史学”毕竟需要说明小至一隅数学知识之本质,一书包含之数学方法,一人对数学理论之贡献,但也需要从“宏观史学”视角分析文化历史背景中的数学发展演变规律。 例如,微积分知识、牛顿---莱布尼茨贡献等历史的微观史学分析固然重要,但其从古希腊即开始的无限思想、工业革命对数学应用知识的需求都需要从宏观的文化历史背景做长时段的分析,无穷小幽灵所引发的危机和争论亦需从哲学、宗教的大视野去考量,为何会引发微积分发明权的争论也要从心态史的角度予以分析,波尔查诺、魏尔斯特拉斯、柯西、戴德金等人为微积分严格化所做出的努力也要从数学哲学的角度进行宏观讨论,可见整个微积分的历史需要从“大历史观”角度才能窥见其历史真相的整体全貌。 中国数学史研究还应该加强对于数学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外史研究。[26]
不仅需要着眼于微观,还需着眼于宏观。
3. 3 坚持“大历史观”要在辉格式和反辉格式史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避免数学史研究的极端辉格解释和极端反辉格主义
西方科学史“从辉格式的到反辉格式的再到两者统一”的研究历程,告诫我们必须有一种辩证的眼光努力在两者间保持“适度的平衡”和“某种必要的张力”. 克拉夫指出: “在实践中,历史学家并不面临在反辉格式的和辉格式的观点之间的选择。 通常两种思考方式都应存在,它们的相对权重取决于所研究的特定课题。 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象罗马神话中守护门户的两面神( Janus) 一般的头脑,能够同时考虑彼此冲突的辉格式与反辉格式的观点。 ”[27]
数学史研究中一直是一种较为明显的辉格史学观念占据主导地位。 数学史家习惯于从现在的数学概念出发去分析古代数学文本( 尤其是数学史家总是利用西方现代数学描述中国古代数学) ,他们认为这些文本所包含的数学概念和思想能被更加清晰和容易理解的现代数学语言来重新表达。 从这种观念出发,古代数学家的贡献无非就是有意无意的阐述出了有现代意义的数学概念和命题,从而被数学史家认定为某种现代数学理论和方法的历史先驱。 这种辉格史观念下的数学史无疑是一部胜利者为胜利者书写的历史,那么精通现代数学的数学家就理所当然的成为撰写这种历史的最佳人选。数学史家超越辉格史观的努力是把数学史作为一门思想史研究,显然受到柯瓦雷科学思想史的影响。 “[28]数学史家超越辉格史的努力可以考虑跟政治思想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等其他史学相衔接,并从文化哲学、技术哲学、政治哲学等相关学科资源得到启发。 柏拉图在古希腊曾赋予数学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认识你自己“,他认为一个人只有经过数学的学习才能进入到理念世界,从而成为他的理想国中城邦政治生活中发挥应有作用的合格公民。 中世纪大学的”四艺“课程继承了数学作为人文教育的传统。 而现代数学教育却渐渐忘记了这种”认识你自己“的教学任务,数学史的研究与教学应该义不容辞地把人文教育承接下去,这是我们不可回避的数学教育使命。
3. 4 坚持”大历史观“要在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避免数学史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
历史是具有强烈民族性的,每一个文化对历史的研究除了给人以知识的盛宴,训练人们的心智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建立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认知,过去的文化传统在一个需要建立历史和形塑现在的国度而言,其功能是提供历史记忆、凝聚当代共识、确立文化认同。 巴赫金曾指出,历史必须是”众声喧哗的“( Polyphonic) .[29]
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发展所存有的基本形式,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起源、地域环境和历史进程各有相同,然而历史所呈现出来的色彩斑斓的人文图景,应该成为不同文明间互相解读、辩误、竞争、对话和交融的途径,并成为自己本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前进动力。 中国传统筹算数学曾在 13 世纪宋元时期达到世界数学的顶峰,但受近代中国社会原因、科学落后导致世界学者对中国古代数学的非客观评价,很多西方的科学史家常常带着”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眼镜看待中国古代传统数学,这些学者的立论前提和研究假设是把西方数学看作是历史上唯一正确的标杆。
数学史学者应该以多元文化的视角来开展数学史研究,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是我们应该秉持的客观态度。 一方面要把握好”自美“的尺幅,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树立民族自尊心。 另一方面,也不能老是在”我们的数学是天下第一“的感觉之中,而无视我们在真正实力上的差距和不足。 正如张奠宙先生曾指出”赶超是进行历史教育的基点,而不能只是躺在历史先进的包袱上自豪。[30]
我们既不能敝帚自珍,也不能总是妄自菲薄。 中国数学史学者们经常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数学神位的不当放置懊悔不已,但历史就是不容假设也不接受忏悔的。 但历史却告诫我们,再造历史殿堂时我们应该客观公正的阐述数学史,也不应漫无目的的随手放置数学。[31]
我们要学会基于“大历史观”去兼顾中西,学习和体会西方数学的理性精神,欣赏中国古代数学曾经取得的辉煌成就,在避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同时,也要避免“民族沙文主义”. 正如张君劢提出的,理应“会合东西,熔铸于一炉之中,知自己之所长所短而后,就其长者而守之,就其短者而去之。 ”同时也要“知西方之所长所短,不论其为近代古代为玄学为科学,一律平等视之,再定去取。 此乃今后廓大自己闻见、智识以求文化复兴之惟一方法也。 ”[32]
3. 5 坚持“大历史观”要在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避免数学史研究的工具理性凸显和价值理性忽视
彼得·伯克指出 20 世纪西方史学“文化转向”的文化史学家们研究兴趣从过去主张不变的理性日益转向价值观,即特定的群体在特定的时代和特定地点所持有的价值观。 雅克·勒戈夫指出,心态史是指一定时代一定社会领域里人们所表达的思想体系。[33]
一个人的心态( 即使是伟大人物的) 跟同时代的其他人有着共同之处; 心态所形成的不知不觉、内在的影响,使得一个时代的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无意识的就赞同同一种价值体系。 所以在乔治·杜比看来,“心态史就是价值观念的历史”. 文化学研究表明,价值观是文化系统的核心成分,“在构成文化的诸多因素中,带有不同程度价值倾向的基本观念,无疑属于其基础的部分。 各种象征、隐喻、想象、仪式和心态等文化现象的深处,往往积淀的仍然是价值观念的东西。 ”[34]
数学史研究中,数学知识与理论结构的形成、演变等方面的发展史固然重要,数学家群体的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也是尤为重要的内容,涉及到数学家们“为什么做数学”的核心问题,价值观作为认识主体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决定了前者。 尤其是历史文化现象背后所隐藏的一个民族文化的数学价值观应该是数学文化研究的核心内涵。[35]
数学史研究必然要考虑数学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问题,并认识到数学家总是作为“数学共同体”的一员在一定的“数学传统”影响下开展自己研究活动的,数学家群体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研究取向。 数学在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价值地位不同,西方文化中数学从古希腊开始就有较高的价值地位,数学一直被视为一种理性精神,一直处于文化系统的“形而上”层面。 这一点上,中国古代数学从来没能做到,中国古代数学始终处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文化价值观念至今犹存。 数学本身作为一种理性,我们必须注意保持其“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必要张力[36]
参 考 文 献
[1]刘鹏飞,徐乃楠,张建双。 数学文化史研究: 为文化而历史[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33( 2) : 52 ~57.
[2]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3][美]柯娇燕着,刘文明译。 什么是全球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王晴佳。 新史学讲演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David Christian. Macrohistory: The Play of Scales[J]. Social Evolution & History,2005,4( 1) : 22 ~59.
[6]孙 岳。 超越人类看人类? ---“大历史”批判[J]. 史学理论研究,2012,( 4) : 49 ~59.
[7]刘耀辉。 大历史与历史研究[J]. 史学理论研究,2011,( 4) : 38 ~50.
[8]洪晓楠。 20 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演变[J]. 求是学刊,1998,( 5) : 14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