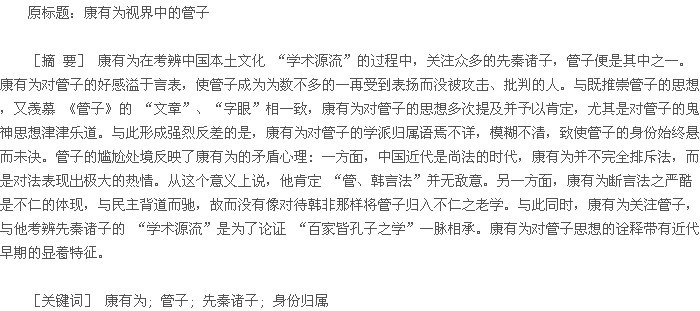
在戊戌政变之前的十多年间,康有为拥有一段相对平静的学术研究时间,专注于考辨中国本土文化的 “学术源流”。在此过程中,他将目光聚焦在先秦时期,在阐发先秦诸子思想的同时,对先秦诸子的学术身份和学派归属予以厘定。管子是被康有为关注的先秦诸子之一。一方面,康有为对管子的态度是明确的、肯定的,管子的思想被他多次提及并受到赞扬。另一方面,康有为对于管子的身份定位和学派归属是模糊乃至暧昧的,致使管子的身份一直悬而未决。管子的尴尬处境反映了康有为的矛盾心态,与他考辨 “学术源流”旨在论证 “百家皆孔子之学”的立言宗旨密切相关。有鉴于此,在康有为那里,管子的尴尬可以说是必然的,因而具有典型意义。
一、对管子的好感和推崇
在康有为论述、提及的众多先秦诸子中,管子是为数不多的一再得到赞扬而没有被攻击、批判的人,这实属难得。管子受到的 “优待”通过与康有为对其他先秦诸子的态度比较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明白和直观: 老子、墨子是康有为攻击的主要对象,老子更是成为他屡屡批判的靶子; 作为孔子后学的荀子在与孟子一起被康有为誉为战国孔门 “二伯”的同时备受诟病,最终被边缘化,孔子嫡传只剩下了孟子和董仲舒; 即使始终是孔学嫡传,孟子也没有逃脱被康有为微词的命运; 庄子得孔子 “择人而传”的大同之道,却一再被批评,最终被逐出孔门之外; 至于老学嫡传———申不害、韩非遭到的痛斥和贬损更是登峰造极,韩非是 “最大之蠹”的定位将康有为的愤怒之情发挥到了极致。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翻遍康有为的着述,很难找到菲薄管子的言论。
康有为对管子的好感溢于言表,对 《管子》在文辞方面的卓尔不凡更是不吝溢美之词。例如,对于 《管子》文章、用词的优美,他不禁一次又一次地赞叹: “周、秦诸子宜读。各子书,虽 《老子》、《管子》亦皆战国书…… 《吕氏春秋》、《淮南子》为杂家,诸家之理存焉,尤可穷究。子家皆文章极美,学者因性之所近,熟读而自得之。”“《淮南》、《吕览》、《管子》、《周书》,字眼伟丽。”
正由于对 《管子》 “文章”、“字眼”的叹服,当有人请教 “为文”时,康有为立即推荐了《管子》。他在回信中如是说: “其 ( 指 “为文”一事———引者注) 本在积理,次在积词。积理有得于书传,有得于阅历,积词则用周、汉之词也。简要最上之法,取 《庄子·齐物》篇、《管子·侈靡》篇、《荀子·解蔽篇》熟读而察之,见其布局、结构、运笔而学之。它若 《素问》之峭,《楚骚》之浓,《考工记》、《战国策》皆可采其腴,下及 《史记》、《汉书》,旁采秦碑,熟浸之,上法 《诗》、《书》、《易》、《礼》之奇奥。如是则自有境界,若春云出岫,秋壑生花。至若山海之雄奇,则视人心境矣。”
在这里,康有为一共提到了 13 部书,作为 “简要最上之法”的只有 《庄子》、《管子》和 《荀子》,将 《管子》的 《侈靡》篇与 《庄子》的 《齐物论》和 《荀子》的 《解蔽》篇相提并论,对 《管子》的喜爱和膜拜之情可见一斑。不仅如此,与对《管子》地位的提升息息相通,康有为建议对 《管子》要 “熟读而察之”,期望从中发现 “布局、结构、运笔”之妙; 并相信掌握这些加以学习和效仿,便能够在 “为文”时纵横捭阖,妙笔生花,挥洒自如。
更为重要的是,康有为折服 《管子》的 “文章”、 “字眼”,并且推崇管子的思想。这在他那里是不多见的。通过管子与韩愈的比较,可以更直观地窥见康有为对管子的情有独钟。众所周知,韩愈是着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无论是思想还是文采都堪称一流。不仅如此,韩愈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诗文是合一的,主张 “文以明道”,开 “以文为诗”之风。然而,康有为却对韩愈的思想不以为然,即使是对韩愈的文风和文学成就也嗤之以鼻。据康有为本人在自传中回忆: “先生 ( 指康有为的老师朱次琦———引者注) 甚称韩昌黎之文,因取韩、柳集读而学之,亦遂肖焉。时读子书,知道术,因面请于先生,谓昌黎道术浅薄,以至宋、明、国朝文学大家巨名,探其实际,皆空疏无有。窃谓言道当如庄、荀,言治当如管、韩,即 《素问》言医,亦成一体。若如昌黎不过为工于抑扬演灏,但能言耳,于道无与。即 《原道》亦极肤浅,而浪有大名。千年来文家颉颃作势自负,实无有知道者。”
据此可知,康有为一面抨击韩愈,一面推崇管子。更有甚者,为了管子,康有为不惜背弃师说。
张伯桢的说法与康有为的回忆相印证,并且将攻击韩愈而心仪管子说成是促使康有为思想发生转变、尽弃师说后而转向佛学的契机。对此,他在 《南海康先生传》中如是说: “光绪丁丑、戊寅二年……时朱先生 ( 指朱次琦———引者注) 极推尊韩昌黎,先师 ( 指康有为———引者注)谓: ‘昌黎道术浅薄无实际。言道当如庄、荀,言法当如管、韩,即 《素问》言医亦成一体。若如昌黎,不过工为文耳,于道无与, 《原道》尤极肤浅。’朱先生素方严,责为猖狂,即同学亦暗讥之。是年冬,先师乃尽弃其所学,闭户静坐,忽觉天地万物皆我一体。自以为圣人可学而至,则欣然笑; 一念及苍生困苦,则又流涕痛哭。更思有亲不事,何以学为? 即欲束装归庐墓上。心潮起伏,歌哭无端,自云思想变迁从此始。先师云: 此 《楞严》所谓 ‘飞魔入心,求道迫切’,未有皈依之时多如此。”
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康有为对管子的崇拜在他关于大同社会合祀偶像的选择中更直观而生动地体现出来。对于大同之人的精神崇拜,他作如是遐想: “前古之教主圣哲,亦以大同之公理品其得失高下,而合祠以崇敬之,亦有限制焉,凡其有功于人类、波及于人世大群者乃得列。若其仅有功于一国者,则虽若管仲、诸葛亮之才,摈而不得与也; 若乐毅、王猛、耶律楚材、俾士麦者,则在民贼之列,当刻名而攻之,抑不足算矣。若汉武帝、光武、唐太宗,皆有文明之影响波及亚洲,与拿破仑之大倡民权为有功后世者也。自诸教主外,若老子、张道陵、周、程、朱、张、王、余、真、王阳明、袁了凡,皆有影响于世界者也。日本之亲鸾,耶教之玛丁路得,亦创新都者也。印度若羯摩、富兰那、玛努与佛及九十六道与诸杂教之祖,欧、美则近世创新诸哲,若科仑布、倍根、佛兰诗士,凡有功于民者皆可尊之。”
康有为遴选出来的大同社会合祀的教主圣哲,从中国到日本、印度、欧美,遍布全世界,统统加起来也不过区区 22 人。其中,中国人除了汉武帝、光武帝和唐太宗之外,便是包括老子在内的 11 人,管子并不在其中。尽管如此,有两点尚需进一步加以澄清: 第一,康有为指出,“有功于一国”者仅管仲、诸葛亮二人,可谓人才难得。第二,就先秦诸子而言,被康有为念念不忘的仅有管子和老子两人而已。综合两方面的情况可以说,管子无论是与诸葛亮一起成为 “有功于一国”的人才———中国仅此两位,还是作为与老子一起被肯定的两位先秦人物之一,其荣耀都已经不证自明。如果再联想到曾几何时被康有为顶礼膜拜并奉为教主的孔子此时由于孔教被废除——— “至于是时,孔子三世之说已尽行……盖病已除矣,无所用药; 岸已登矣,筏亦当舍”,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管子可谓是虽败犹荣———即使是没有在大同社会被合祀,也无损于他的地位和荣耀。
二、对管子思想的阐发和诠释
康有为对管子的好感和崇拜与管子的思想———至少是康有为认定的管子思想密不可分,这在其自传中已露端倪。他之所以对韩愈怒不可遏,大加鞭挞,是因为韩愈 “道术浅薄”、 “极肤浅”,只不过是 “浪有大名”而已。由此反观,康有为心仪管子,是因为管子言治,裨益于救亡图存,管子的思想对于中国近代的振衰疗弱具有现实意义。对于这一点,康有为下面的这段话是最好的注脚: “王、霸之辨,辨于其心而已。其心肫肫于为民,而导之以富强者,王道也; 其心规规于为私,而导之以富强者,霸术也。吾惟哀生民之多艰,故破常操,坏方隅,孜孜焉起而言治,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虽尧、禹之心,不过是也。所以不能不假权术者,以习俗甚深,言议甚多,不能无轻重开塞以倾耸而利导之。若人心既服,风俗既成,则当熙熙皞皞,以久导化之。为之君、相,只以为吾民无所利焉,此非迂儒所能识也。昔武侯治蜀,有取于管子、韩非,岂非以治国所当有事耶? 且圣人岂能无开塞之术哉! ”
循着这个思路,康有为对管子的好感、推崇顺理成章,同时也可以想见他对管子思想的阐发以法治为中心而展开。事实正是如此。
康有为在论及管子的思想时,对其法治方面的内容多有论及,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断言:“管、韩言法,《内经》言医,孟、荀言儒,庄、列言道。”“言治当如管、韩,即 《素问》言医,亦成一体。”“《管》、《韩》言法,《内经》言医,《孟》、《荀》言儒,《庄》、《列》言道。”
此外,康有为还注意到了管子其他方面的思想。例如,他指出: “孟子、荀子、管子皆以心物对举,可知物指外物。”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康有为对管子的鬼神思想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断言: “或有谓宗教必言神道,佛、耶、回皆言神,故得为宗教; 孔子不言神道,不为宗教。此等论说尤奇愚。试问今人之识有 ‘教’之一字者,从何来? 秦、汉以前,经、传言教者,不可胜数。是岂亦佛、回、耶乎? 信如斯说,佛、回、耶未入中国前,然则中国数千年为无教之国耶?
岂徒自贬,亦自诬甚矣! 夫教之为道多矣,有以神道为教者,有以人道为教者,有合人、神为教者。要教之为义,皆在使人去恶而为善而已,但其用法不同。圣者皆是医王,并明权实而双用之。古者民愚,阴冥之中事事物物皆以为鬼神,圣者因其所明而怵之,则有所畏而不为恶,有所慕而易向善。故太古之教,必多明鬼; 而佛、耶、回乃因旧说,为天堂地狱以诱民。今读佛典言地狱者,尚为之震栗。而常人循行城隍庙廊之地狱,亦多有所动而改过者。欧亚之人,俗皆略同,此耶、回所以成教宗而能大行。在中世愚俗,其有益于人心风俗,岂浅鲜也! 管子曰: 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孔子亦言: 圣人以神道设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今六经言鬼神者甚多,肃祭祀者尤严,或托天以明赏罚,甚者于古来日、月、食、社、稷五祀亦不废之,此神道设教之法也。”
康有为又指出: “中国开明最早,以孔子早扫神权,故后儒承风,为无鬼之论。然在孔子之意,以生当乱世,人性未善,不能不假借鬼神以怵之,仍而不绝。如管子所谓: 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也。故庄子称孔子曰: 古之人其备乎! 配神明,亦通四辟,无不在,以神道为教。是孔子何尝不兼容并包? 但不欲以此深惑愚民,若异氏之术自取尊崇耳。今多谓孔子不言天神、灵魂、死后者,皆误因 《论语》之一二言,如 ‘子不语神怪’、‘远鬼神’等说。则 《易》曰: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故知鬼神之情状。群嵩凄怆,天地之精,乃取而祀之。经说固已无限,即以《大学》言,开端即曰 ‘在明明德’,岂非灵魂? 而 《中庸》始则曰 ‘天命’,终则曰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 ’此又何言?”
在这里,康有为认定管子所讲的 “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与孔子言鬼神而神道设教同一旨趣。甚至可以说,与记载孔子言行的 《论语》相比,管子显然深得孔子大道的精髓。其中最明显的证据是,尽管由孔子亲授弟子和再传弟子编纂的 《论语》记载了孔子的言行,却不了解孔子的思想旨趣。例如,书中一再说 “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等等。正是这样的记载误导了人们对孔子大道的理解,尤其是宋明理学家冒言孔子不言鬼神,将鬼神方面的内容从孔子大道中剔除,使孔教 “割地”。孔子后学的这些做法导致了致命的后果: 孔教不言鬼神,给他人甚至是外国人否认孔子思想是宗教,否认中国有宗教提供了口实。由此看来,即使不是孔子后学,至少管子与孔子同调,在对鬼神的看法上远远胜过孔门弟子。更何况从上下文的语境和气场来看,康有为讲这两段话是为了反对人们说孔子不言鬼神,目的是证明孔子的思想是宗教。其中提到的管子,显然是作为孔子言鬼神的证据出现的。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管子属于孔学,故而像孔子那样言鬼神。
与孔学的学术归属相一致,康有为有时将管子与孔子、儒家思想联系在一起。下仅举其一斑: “一部 《易经》,专讲中和。孟子言忍性,则性不尽善可知。子路闻过最喜,为善最勇,的当得 ‘雷霆走精锐,冰雪净聪明’二句。孔子最贵有耻,故诗人言: 人而无耻,不死何为? 子贡问士,告以 ‘行己有耻’,即管子亦以礼义廉耻为四维。”“《洪范》: 思曰睿。 《管子》谓: 思之思之,鬼神来告之。《中庸》言: 慎思之。《诗》: 思无邪。《孟子》: 思则得之。”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孔子最贵有耻,孔子教诲子贡的 “行己有耻”就是管子所讲的礼义廉耻四维。同时,孔门贵思,管子的 “思之思之,鬼神来告之”便在其中。如此说来,讲究礼义廉耻和贵思成为管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管子的尴尬与康有为的困惑
上述内容显示,管子在康有为那里有时与孔子、孟子、荀子一起出现,管子的思想也多次与儒家相提并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管子应该属于孔学。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康有为还是将管子与法家人物商鞅、申不害、韩非等人联系在一起出现,甚至对管子与韩非的思想相提并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管子应该与韩非的归属一样,属于老学。至此,管子在康有为那里遭遇了身份和归属的尴尬。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对于韩非是有明确定位的,那就是: 韩非是老子后学,并且是老学嫡传。与对待韩非的态度截然不同,康有为虽然让管子频频亮相,却对管子的身份归属语焉不详———既没有因为将管子与孔子、儒家联系在一起,而明确地肯定管子属于孔学;也没有因为管子与韩非屡次并提,而明确指出管子属于老学。
要之,管子在孔子、老子之前,不便成为两人的后学。然而,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或明了。众所周知,管子字仲,名夷吾,谥号敬,又称管敬仲,是春秋初期的政治家,孔子、老子则是春秋末期的人。从年代上看,无论将管子归入孔子后学还是老子后学都不合适,都会因为 “时光倒流”产生时代错位而出现错误。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在康有为那里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尽管管子 ( ? —前 645) 与孔子 ( 前 551—前 479) 相差将近二百年,然而,对于康有为来说,年龄不是问题。他的 “诀窍”是: 将先秦诸子的生存时间后移,说成是战国时期的人,以突出孔子在时间上的优先性。这是康有为惯用的伎俩,与孔子同为春秋末期的老子和墨子到了康有为那里统统都成了与孟子同时的战国人。他明确肯定老子和墨子都是战国人,理由是: 老子是作 《道德经》的老子,即 “老子 《道德经》是战国时老子所纂”; 墨子与孟子等人是一辈,“墨子为子夏后辈。杨、墨、老,孟子一辈”。康有为对管子生卒年代的考量,亦可作如是观。循着这个思路,管子完全可以作为孔子后学,当然亦不排除成为老子后学的可能性。更何况孔学、老学在康有为那里拥有相对广义的内涵,并不单单指孔子、老子创立的学派。这就是说,退而言之,即使时间不在孔子、老子之后,不能成为两人的后学,也不妨碍管子思想的孔学或老学归属。
问题恰恰在于,即使如此,在康有为那里,管子的身份始终只能是一个谜,因为他对管子的归属始终是模糊不清的。试看康有为的这段话: “虽 《老子》、《管子》亦皆战国书,在孔子后,皆孔子后学。说虽相反,然以反比例明正比例,因四方而更可得中心。诸子皆改制,正可明孔子之改制也。”
这段话一面将 《管子》与 《老子》并提,指出其学说与孔子相反,在改孔子制上与纷纷创教的战国诸子别无二致; 一面肯定 《管子》是 “孔子后学”。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这段话中出现的是 《管子》之书而非管子之人,然而,这段话同样将康有为对管子学术归属和表达的模糊、矛盾推向了极致。这是因为,康有为并没有对管子与 《管子》的时间予以区分,也没有指出 《管子》并非管子所作,而为后人假托。更加值得深思的是,此处的 “孔子后学”没有确诂,完全可以对此从不同角度去解读,而意思却大相径庭乃至完全相反。第一种解释是,由于时间上 “在孔子后”,故曰 “孔子后学”; “孔子后学”之 “后”只是时间之谓,并不代表学术传承。因此,管子的思想与孔子之间并无源流上的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管子即使为 “孔子后学”,也不排除其思想与孔子学说 “相反”。第二种解释是,与老子一样作为战国人的管子,不仅在时间上晚于孔子,而且作为孔子后学传承了孔子思想,因为康有为宣称“‘六经’皆孔子作,百家皆孔子之学”———在这种情况下,管子改孔子制,也 “正可明孔子之改制”。吊诡的是,从康有为一贯的思想来看,这两种解释都是成立的。而这两种解释之间是矛盾的,因而是不能同时成立的。更为致命的是,这个矛盾不在于解释者,而是根源于康有为本人关于孔子与诸子尤其是孔子与老子关系的矛盾看法和表述,可以说与生俱来。
综合考察康有为对管子的表述可以得出两个基本认识: 第一,康有为对待管子没有像对待另一位法家先驱———子产那样归为孔子之学,以证明西方的民主政治、经济制度原本就是孔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政治之学最美者,莫如吾 《六经》也。尝考泰西所以强者,皆暗合吾经义者也。泰西自强之本,在教民、养民、保民、通民气、同民乐……其保民也,商人所在,皆有兵船保护之。商货有所失,则于敌国索之,则韩起买环,子产归之,且与商人有誓,诈虞之约是也。”
第二,康有为也没有像对待他频繁并提的 “管、韩言法”的韩非那样毅然决然地将管子推给老子———恰好相反,他有时试图拉近管子与孔子之间的距离。如上所述,康有为不止一次地将管子与孔子联系在一起,以此证明孔子言鬼神,孔子的思想是宗教。
诚然,在其他场合,康有为给了管子 “明确”的学派归属,那就是: 将管子与商鞅、申不害和韩非一起归为 “法家”。于是,他宣称: “同是法家,管子心最公,重民也; 商君次之; 至申、韩,直视民命如草芥。”
问题的症结恰恰在于: 在康有为那里,“法家”是不存在的,因为法家不是独立的学派。这就是说,康有为尽管使用了 “法家”这个字眼,然而,法家却不是与孔学、老学或墨学并列的; 这便意味着即使是康有为将管子明确地归入了法家,实质上还是让人不知所云,说来说去,管子还是等于没有归属。更有甚者,康有为也没有认定全部法家都属于老学———子产被归为孔学就是明证。此外,与管子同为法家的除了申不害和韩非,还有同样作为法家先驱的商鞅,而商鞅也像申不害、韩非那样被康有为归到了老学之中: “尉缭、鬼谷、商君,皆老子学。”
由于不是所有法家都归为老学,便不能由康有为 “明确”地说管子属于法家而推出管子是老子后学或属于老学。至此,在康有为那里,管子并没有因为被说成是 “法家”而归属于法家,甚至不能因为是法家而拥有明确的归属。恰恰相反,无论是法家的尴尬处境还是法家人物与孔学、老学错综复杂的关系都增加了管子身份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有为越是对管子的学派予以归属,就越是增加了管子身份的悬疑性和不确定性。
进而言之,康有为对法家先驱的不同归属与法家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不是独立学派具有一定联系,因为法家不是独立学派,不能让法家人物单独组成一派。在这方面,正如上文所引,即使是组成一派——— “同是法家”,到头来还是由于没有学派而只好将他们或归入孔学,或归入老学。
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可以假设,如果仅仅由于这一个原因的话,那么,所有的法家人物都应该被归入同一学派之中,而不是像康有为所做的那样: 将法家人物或归为孔学,或归为老学。之所以如此,这里隐藏着更为深层的原因,暴露出康有为对法家的矛盾心理: 一方面,中国近代是崇尚法治的时代,康有为并不绝对地排斥法。恰好相反,他对法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例如,康有为从日本转译的西学书目中即有 “法律门”,这从 《日本书目志》的目录中即可见其一斑。此外,康有为强调法与治密不可分,肯定孔子言法,同时指出 《春秋》就是孔子言法的代表作。与商鞅一样重法的子产、吴起和李悝等人也被康有为义无反顾地归在了孔学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他承认 “管、韩言法”,肯定管子与韩非的思想一样以法为主,并无敌意。另一方面,康有为将法与刑术相提并论,认为二者都是不仁的表现。沿着这个思路,他一面将大部分法家人物归为老学,一面对精于术的申不害和韩非极为仇恨,将两人说成是老学中不仁的极端代表。这样一来,康有为便在对管子的归属上陷自己于两难境地: 一方面,由于对法的消极理解,他不便明确地将 “言法”之管子归入孔子之学———因为孔教以仁为宗旨,与法之严酷、不仁截然对立。另一方面,出于对管子的好感乃至倾慕,康有为即使是在将管子和韩非皆归入 “法家”时,也对两人分别对待———一面强调管子之心最公正,民主爱民; 一面强调不可对管子与韩非同等对待,因为韩非视民命如草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康有为没有像对待申不害或韩非那样,将管子归入以不仁为宗旨的老学。矛盾终归是矛盾,人们看到的结果是,管子的身份在康有为那里始终悬而未决。
在康有为那里,对管子的阐发是考辨中国本土文化 “学术源流”的一部分,与他对孔子、老子关系的认定一脉相承,并且服务于 “百家皆孔子之学”的立言宗旨和最终目标。从整个近代哲学来说,康有为视界中的管子带有近代早期的显着特征,是管子在近代的最早亮相。这主要表现在: 康有为对管子的解读无论是与韩非等法家人物相提并论一起出现,还是与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人物联系在一起,都是在中国本土文化的视域内进行的,与严复、梁启超等其他近代思想家将管子与西方思想和人物相互诠释呈现出明显差异。
[参考文献]
[1] 康有为: 《桂学答问》,《康有为全集》第 2 集,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2] 康有为: 《万木草堂口说·经策》,《康有为全集》第 2 集,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3] 康有为: 《答某君书》,《康有为全集》第 7 集,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4] 康有为: 《我史》,《康有为全集》第 5 集,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5] 张伯桢: 《南海康先生传》,《康有为全集》第 12 集,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