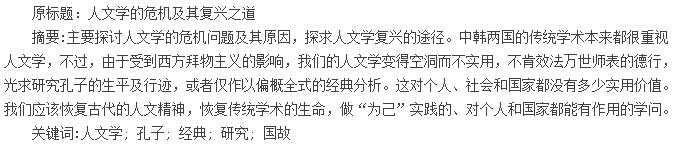
一、人文学和现实
我们时常提及“人文学的危机”,并向政府要求拟定有关对策。其实“要求对策”也没有具体的项目要求,只是要求多增加研究经费而已。在自然科学方面没有钱当然不能做研究,不过人文学不一定都需要钱,也不一定要助手,一般来说有书和电脑就差不多了。与自然科学要求合作研究不同,人文学研究更多的是独立的,独立性越强思想性也就越强。
在过去中韩两国的历史里,不要说呼吁人文学的危机,就是提及人文学的字样都没有。不过,中韩两国的历史就是人文学的历史,我们的文化就是以人文学为枢纽发展起来的。中韩两国在过去都重视个人的教育,鼓励个人修身齐家的人格陶冶,并以此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个人和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单位,如果每个人能够实现人的固有的价值而得到平安,则社会、国家也能维持圆满稳定的局面。所以,在文化上,两国一向崇尚敦厚的冠昏丧祭之礼,如对人民的婚姻、家庭,国家也保持负责的政策,对鳏寡孤独特别加以照顾,这些良好的民风以及历代王朝的德政,都是靠孔孟教育而得以实现的。
如今,韩国未婚比率全球第一高,居住在首尔江南地区的 30 多岁的女性中未婚者几乎占了一半。结了婚又不一定偕老,离婚率也最高,生育率又全球最低。传统家族体系逐渐瓦解,伦理结构失去了均衡,社会变成无机化,人情越来越淡化、越来越冷漠。
对社会的这种现象,大学的人文学有何功能;大学学者们累积的研究成果对社会有何贡献; 我们的论文会有多少人看; 大学的教材校外的一般人看不看; 我们的学术著作对社会有多大的贡献……本文尝试着检讨中韩两国所面临的人文危机及其原因,进一步寻求人文学本来的面目,探讨人文学的复兴途径,并说明人文学的现实意义。
二、孔子的人文学传统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化都看重人文精神,也就是注重伦理道德以及人格陶冶。人文是可以与天文相对而理解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周易·贲卦》)
观察天的纹饰,以明了四季时序的变化规律; 同样,观察人的伦常秩序,可以教化天下,实现移风易俗的德政。察看天文得到宇宙的时间表,最早造出非常科学的太阴太阳历( 现在一般说的是阴历) 。我们现在所用的阳历只有一年的周期才有根据,分十二个月及每个月的日数都没有科学根据,就是少的二十八日,多的三十一日,这一切都是偶然组成的,不如阴历十二个月都依照月的空转周期( 朔望) 来准确确定日数。万物都随着时间而变化,森罗万象皆与天合一而转化,人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根据。
换句话说,万物都随着天文而顺应发展,人也以顺天为善,先人力求顺应自然,这就是人文的开始。再者,人模拟天文所呈现的时序规律及时序所起之生长收藏的化生原理,组织人与人之间的伦常规范。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如古人认为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 《周易·序卦》)
原来先有万物后有男女,再后有人伦规范,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如此形成了礼仪秩序,这就是人文( 当然国家的行政机构也引入天文的自然规律体系,分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 ,如此确立了人文的大纲,剩下的就是要实现圆满的人文世界。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颜渊》依照天体的运行秩序,结成伦常模型,首先要弄清楚每个人的位置及社会的身份。“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则社会和国家无法维持稳定的秩序。天体每颗星都有准确固定的位置及轨道,人也都有一定的位置及社会上的功能,因此人文学注重强调做人的道理。
中国的文化及学问都是以人文学为枢纽而发达的,代表就是孔子所创办的儒家思想。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是独尊的人物,两千多年来成了“万世师表”,在韩国也同样被尊奉为至圣先师,也就是历来传统文化和学问的中心人物了。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述《春秋》,完成儒家经典,奠定了后世立教的具体教课内容。
这六种经典可说是中国最早的人文学典籍,也是中国学问的渊源,在中国及韩国均成为两千多年的传统教学核心内容。孔子通过六经要实现理想的人文世界: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致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礼记·经解》)
六经就是实际意义的教材,加强道德修养的德育,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标。因此学与仕不分,“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论语·子张》) ,为学不离从政,也是中韩两国传统人文学的特征。韩国朝鲜王朝五百年,一直是文人统治的,从来没有武人参与过,也就是人文学的力量。六经就是实践的学问,继承先人的文化,适用于现代,又传给后代,成为生生不息的生命源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周易·象传( 乾卦) 》)
人文是效法天文的。天体运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停止。人也一样,一代复一代,如孔子已经有八十代后孙,传宗接代不会绝后,人文也随着天文转化无穷。因此人文的人道是与天道和谐一致的。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天人之间的协调和谐,就是人文的本质,人文由此得到生命活力,人伦道德的实在意义也在于此。
三、人文学的断绝
孔子的人文学在中国和韩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里,一直是传统学问及文化的主干,各级学校的教学内容也没有多大变化。不过到了清末( 韩国朝鲜末期) ,西方列国入侵,几千年的传统国家一朝就垮了,开始了“以夷变夏”的现代历史。从衣食住行的生活形态到学校的建筑及教学内容,一切都随从西方而改变,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一律变成羞耻的对象,甚至傅斯年、鲁迅等人主张废除中国文字,至今中韩两国可说是文化殖民地。文化殖民地当然没有自己的文化,不是说没有文化,是没有以自己人为中心的文化。韩国人如果没有以韩国人为中心的文化,只是模仿穿西服,吃麦当劳,喝咖啡洋酒,过西方的情人节及圣诞节,这样可以说韩国有文化吗? 这是很难让人接受的。文化一定有文化的主体,失去了主体,我们就不是以我为主来吸收西方文化,而是彻底被同化而自愿成为殖民地。
文化的枢纽是人文学,人文学是以人为中心的学问,不过天下没有全球性的人文学。西方的文化是以神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西方大部分的国家没有发达的人文学,可以说只有发达的神学。在我看来,所谓西方的哲学也不能算是人文学,不外乎是观念的论证,并没有实在意义,只是崇尚空虚的学问而已。
现在我们一直追求西方的文化及学术,结果我们只有科学及其旁系学术,没有人文学,这就是现在中韩两国社会及学界最大的问题。过去个人的修养教育以及国家的经营都靠人文学,不但可以维持长久的历史,也没有发生过如现代违背人性的乱世现象。
何以说没有人文学呢? 如上述,人文学是实践的,六经是教化国人用的,并不只是学者们研究用的。现代的大学是非常闭锁的,不与社会交流,也没有国家意识,在校内传授不很要紧的知识( 亦可说买卖知识) 而已。学校按照教授的论文数量而估计研究成果,教授都力求写论文,不过刊登了以后不会有人看,即使看了也没有任何影响。六经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人看了六经,会有心理上的变化,影响到个人的思想并形成新的世界观。
脱离修身需要单纯研究六经则不然,抽出一些知识,加以分析综合,这已经离开六经很远了。从开始模仿西方的学术之后,我们做学问的目标及方法都变了。
大学注重理论,国文课也不很重视写作,多偏重于西方的语文学理论。历史课也无意继承传统,只是分析史料,并以之为故物。1919 年刘师培、黄侃等人成立了《国故》月刊社。胡适提出“国故学”的三个方向: 历史眼光、系统整理、比较研究。“国故”是指过去的故物,把经学也看成博物馆的遗物,是进行科学整理以及比较的客观对象,并不是要继承的自己的历史。现代的学者常把自己的历史看成人家的历史,喜欢研究、整理、比较。
北京大学的哲学系成立一百年了,拥有专职教师 67 人,人数比哈佛大学多三倍。“哲学”这个名词莫名其妙,“学”的对象就是非常模糊的,“哲”也没有具体的意思,不像国文系、历史系指的是国文和历史,谁看都可以知道。搞了一百年的哲学,哲学的意义都不清楚,“philosophy”其实和我们毫无关系,是西方这个地区的学术,是一种以观念为主的虚学。如此看来,我们的大学和学问里的确遗失了人文学。
四、复兴人文学的必要
对传统学问我们一直保持了非常模糊不清的态度。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里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在这里“选出”的一些资料已经不是学问,更不能说是中国的。在《论语》里找一些片段的字句,就说是孔子的哲学,这是笑话,孔子与哲学实在毫无关系。不过我们从冯友兰的时期以后一直到现在,还是维持着这种态度,以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学术,重新建造一个很空虚的观念体系。
我们看完《中国哲学史》以后除了一些片段的知识以外,还可以得到什么呢? 这些知识又用在哪里呢?
黄玉顺教授指出: “经学热中无经学,国学热中无国学”,这话很实在。黄教授提出国学应有的五大基本特征: 第一,就其性质而论,国学既非西方的“汉学( sinology) ”,也非原教旨的“经学”,而是一种现代性的中国学术; 第二,就其方法而论,国学并非学术史( 史学) 那样的对象化或“客观”化的“科学研究”,而是经典诠释; 第三,就其形式而论,国学并非“文史哲”那样的多元的分科研究,而是传统经学那样的一元的统合学术; 第四,就其地位而论,国学并非与“文史哲”等等相并列的一个学科,而是可以统摄诸学科的一门奠基性学术;第五,就其作用而论,国学作为一种学术,并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所谓“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柔性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论或学说。
黄教授的话,宗旨是要脱离冯友兰的角度,国学应该从现代中国的角度来看,看成中国固有的学问,这样才能建构真正的国学。他指出我们现代范式的文史哲,“其本质是一种西方科学实证主义,其立场是客观化,其特征是对象化,总之是不切己的,不是‘为己’( 《论语·宪问》) 之学。”黄教授说的五大特征主要是说现代对经学的研究方法论,其中他特别提出以“经典诠释”作为真正的国学的研究方法。
我们在大学研究的人文学,都有黄教授所提到的毛病,用西方的眼光来分解传统学问,结果是传统学问丧失生命活力,变成呆板的历史遗物。这是破坏传统,也没有学问价值。在现代社会里传统学问有何意义? 又如何攻读呢?
第一,我们先要恢复文化的精神及生命活力。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全球性的文化,各个民族都有自己固有的文化,都有不同的衣食住生活形态、不同的岁时风俗、不同的历史背景,这才是文化的生命。因此,每个文化都有主体,若仿效他民族的文化,做不成主体,也就没有生命。
第二,要复兴我们的文化,就要兴起人文学。人文学并不是西方的实证科学的学科,而是如同经学一样的实践学问,使人受到感动而起着提升人格修养的教育效果。这是文化的生命,也就是传统人文学的力量。
第三,大学的人文学科要尽快放下西方搞科学的态度,努力与社会共同体认传统学问。现在学者的论文是适合于自然科学的,不适合于人文学。中国的小说及诗歌都是很有力量感动人的,人文学也一样,通过著述( 包括传统古典的诠释)可以发挥这种力量,这当然不包括现在那些为了研究成果而写的死板的学术著作。
第四,大学不应该与社会隔离,大学的学术活动都需要开放,引入自由市场经济原理,教材著述必须要配合供需的原则。人文学并不是要强制或要特别保护的对象,它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
中韩两国都有受屈于西洋武力的近现代史,因此两国在走上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之路的时候,忽略了对自身优良传统文化的继承,拚命地模仿西方,盲目崇外,结果现在失去了整个文化的有机性,丧失生命活力,陷入了整个社会的混乱。大学的学问也是一样,本来是说中体西用,不过现在变成了西体中用,盲目崇外,很难找到“为己”的学问。
个人是难免摆脱生老病死的规律,不过人类的生命是子子孙孙永不休止的。我们的文化也是有生命的,如果失去了生命,那不是文化,自强不息的才是文化。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1.
[2] 黄玉顺. 中国学术从“经学”到“国学”的时代转型[J]. 中国哲学史,2012( 1) :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