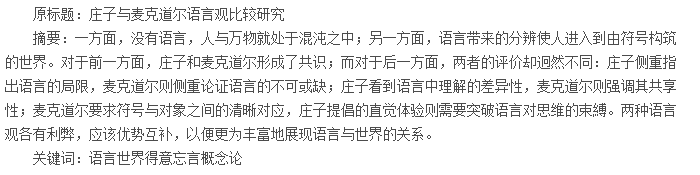
庄子的语言观有其深刻、独到之处,他揭示了语言现象的复杂性、语言的局限性,以及名与实、言与意、心与物、语言与权力、语言与世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等丰富内容。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十分关注语言问题,不再把语言仅仅当作思维的工具,而是把语言当作反思自身传统的起点和基础。本文将对庄子和美国当代分析哲学家麦克道尔(J.McDowell,1942~)有关语言与世界、语言能否表达最高真理两方面作一粗略比较,以揭示中西方思考语言问题的异同、两者相互借鉴的可能,以及对进一步认识语言与世界之关系的启发。
一语言与世界
庄子和麦克道尔都肯定语言的重要性,即:没有语言,一切都将处于混沌之中。庄子说:“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庄子·齐物论》,以下引用《庄子》只注篇名)“道”因为“行之”才成为“道”;“物”因为“谓之”才成为“物”.“道”与“行”、“物”与“谓”是不同的:“物”(实、客体、所指、经验)是客观存在,“谓”(名、言、能指、概念)是人所创造的语言符号,“谓之”则是对“物”的命名。在“名”与“实”、“言”与“意”之间,“实”与“意”是第一性的。“言者所以在意”(《外物》),即语言是用来表意的,它承载着人赋予这个符号的意义。这里,语言是一种工具,“名”从属于“实”.关于“名”与“实”,庄子一方面认为“名”反映着“实”,他说:“名者,实之宾也”(《逍遥游》)、“名止于实”(《至乐》)。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名”是约定俗成的,与“实”不存在严格的、固定的对应关系,他说:“周遍咸三者,异名而同实,其指一也”(《知北游》),异名同实、异实同名的情况时有发生。他还说:“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天道》),“名”虽然是反映“实”的符号,它的形成却有任意性、偶然性和变迁性。
当然,“实”也无时无刻不处于生灭变化之中,有着不确定性。庄子“物谓之而然”表明,因为给不同的物不同的命名,我们才将一物与他物区别开来,认识到事物如其所是的那个样子。“名”虽然从属于“实”,但“名”并非仅只位列“实”的旁边以备用,也并非先于人类而备好的将要贴给万物的标签。其实,“名”也是“实”得以完成和能被思考的场所,没有被语言说出来的自然万物无法被思考。所以,“名”、“实”也可以说是同时共在、互相成全的。语言是人有意作为的结果,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天地万物之所以存在,之所以是其所是,取决于主体认识的能力。没有语言,人与万物就处于混沌之中。对此,庄子说:“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珍也。请言其珍: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辨,有竞有争。”、(:《齐物论》)“道”本是没有边界的,为了用语言去达到那个“是”则出现了“畛”(“畛”即“边界”、“界畔”)。
他还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寓言》)没有语言,世界是齐同一体的;一旦使用语言,原本一体的世界便显现出左右、伦义、分辨,以及轮廓、形状、色彩、大小等的差异。当代语言哲学也有同样的理论,认为正是通过语言,包括人在内的万物才得以如是存在,并因着这些符号才形成了存在于语言之中的人的世界。海德格尔说:“词语也即名称缺失处,无物存在(ist)。惟词语才使物获得存在”;“词语才把作为存在着的存在者的当下之物带人他的‘是’(ist)之中,把物保持在其所是中,与物发生关系,可以说供养着物而使物成其为一物”[1];“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2].伽达默尔也认为语言就是能被理解的存在,不可能有语言之外的世界存在,存在就是在语言中的存在(Sein)。他说:“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3];“世界本身是在语言中得到表现。语言的世界经验是‘绝对’的……语言和世界的基本关系并不是意味着世界变成了语言的对象。”[4]关于语言使人与环境分离、脱离混沌的情形,庄子描述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
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齐物论》)天地、万物与“我”本来融为一体,当人在说这个一体之一的“一”时,“一”已经是通过概念化的理解而形成的抽象的名称或符号,而非客观存在之物本身;“一与言为二”则是指:一旦使用语言,就打破了“万物与我为一”的状态而成为“二”.人于是从所栖居的环境之中脱离出来,进人到清晰、分辨的语言世界之中,进入到由象征构筑起来的符号系统之中。语言将世界一分为二:一个是自然界,一个是通过语言、按照语言法则而建构起来的意义世界。麦克道尔也同样重视语言,原因在于语言能力与他的关键术语--“概念能力”密切相关。他沿着康德、维特根斯坦、塞拉斯等人关于语言、概念、经验的思路,在《心灵与世界》一书中试图通过将塞拉斯提出的“理性的逻辑空间”(thelogicalspaceoferasons)纳入到自然世界之中,来避免自然主义把人的心灵当作在经验世界之中受因果律支配的自然现象,同时也避免膨胀的柏拉图主义(rampantplatonism)将身与心、理性与自然一分为二的后果。
他通过论证经验是概念的,从而让人类特有的自发性(spontaneity,它是来源于康德的概念,指理性的能动性)和理性领域与被动性(passivity)-起构成我们的经验现象。麦克道尔提出,正是“概念能力”将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动物单凭自然赋予的感官在环境(environment)之中生存,人类则需凭借教育以获得自发性而生存于世界(world)之中。环境是人和动物共享的,“世界”则为人类所独有。麦克道尔将既是自然的、却又自成一类的与人有关的一切,包括那些为人类所独有的、在人类生活中起作用的东西称为“第二自然”(thesecondnature),它出于自然却又高于自然。
“第二自然”的思想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在亚氏那里,学习做有德性的人就是将德性变成自己的习惯或第二自然。[5]人类凭借单纯的动物性就拥有了第一自然,这是与生俱来的,而第二自然是通过学习获得的。麦克道尔发挥了这一古希腊的哲学观念。他说:“作为结果的思想与行动的习惯就是第二自然。”[6]“我们不需要说我们除拥有纯粹动物也拥有的那些非概念性的内容外,我们还有其他东西,因为我们能将那种内容概念化,而它们则不能。我们应该这样说,我们拥有动物也有的那种对环境特性的知觉性感觉,但我们拥有的方式是独特的。
我们对环境的知觉性感觉已经被纳人到自发性领域。这使得我们与动物区别开来。”[7]在麦克道尔看来,人之为人的显著特征在于他脱离了动物的直接性和本能性,人能把与动物共享的直接性纳人到由理性构筑的第二自然里。正如有学者所言:“也正是在第二自然中,超出因果律领域的意义和价值才进入我们的视野之中。第二自然的边界和第一自然的边界在某种意义上是重合的,但是在第二自然的产生过程中,人的理性(自发性)已经被动地参与其中。”[8]庄子虽然没有提出“语言是我们的第二自然”这样的思想,但他同样认为语言不是自然的,而是习得的。他说:“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
(《齐物论》)刮风和说话都有声音,但语言不是刮风那样的自然现象,而是道出了实在的东西,即语言总是有内容的。他还说:“其以为异于數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齐物论》)即:具有表意功能的语言不同于小鸟发出的鸣叫之声。关于语言的习得,庄子说:“婴儿生,无硕师而能言,与能言者处也。”(《外物》)唐代道教学者成玄英疏解这句话说,婴儿无需专门的大师而能说话,此“非由运知,学而成之也”[9].这里明确强调:使用语言不是本能具有的,而是学习的结果;学习语言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与能言者处”.学习语言的能力是本来具有的,但真正会使用语言则需要学习。“言非吹”、“异于鷇音”、“与能言者处”这些表述都表明,庄子认为语言出于自然却又高于自然。由于概念性、自发性、第二自然、理性空间等的存在,使人类除拥有动物的环境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语言是最为重要的内容。没有语言符号的帮助,我们无法将两个观念清楚地区分开来。基于此,索绪尔声称,“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_.人们给世间万物和各种现象以不同的命名,因为有了具体的名称,混沌的世界才得以在语言名称的表述之下变得轮廓分明,为人们所感知、所认识,并得以运用语言来管理整个世界。在语言的召唤下,人与世界相互生成了对方。二得意忘言与概念论。
有了分辨,人走出混沌,进人了由符号构筑的意义世界、象征世界、人文世界。对这一现象,庄子和麦克道尔的评价迥然不同:(1)庄子的语言观不乏对语言的批判性反思,他提出“得意忘言”,最终要忘记语言才能让人与万物重归于一。麦克道尔却论证了经验的概念性,由于心灵本身也是概念的,于是,在语言里心灵与世界重新关联起来。(2)庄子看到了语言表达的差异‘认为各种理解难以达成共识、形成“公是”[11].麦克道尔则将语言看作一个社会里所有成员共同继承的传统’重点论述其共享性。庄子对语言的批判性反思内容非常丰富,这里仅分析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语言有其适用的范围。庄子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秋水》)“有名有实,是物之居;无名无实,在物之虚。可言可意,言而愈疏。……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
(《则阳》)由此看出,“物”、“言”、“意”、“道”处于不同的层次。通过语言能说清楚的仅仅是“物”.虽然人们勉强对“道”进行了命名,但那也是人的假借,“道之为名,所假而行。”(《则阳》)人所能够确切拥有的知识,只是关于“物”的因果联系,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以语言形式呈现的各种知识体系。对于形而上的“道”,语言则显得无能为力。庄子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大道不称”;“言而愈疏”(《则阳》)。囿于语言之于世界的无奈,“不言”成为最好的诉求。“得意忘言”表达了在思维中摆脱语言的企图。在庄子这里,思维有时并不把语言作为必要的条件,语言也不是思维的唯一载体。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都无法把握瞬息万变的世界,道家于是开启了以整个身心融入万物运化的体悟之路。除了“不言”,庄子认为认识主体可以通过“心斋”、“坐忘”、“外物”等特殊的方法“知道”、“得道”、“体道”,即通过排除心与外物的阻隔,使心灵归于空寂,进人“万物齐一”的境界,最终超越语言和思维,克服“言不尽意”的困境,把握无限之“道”.由此,庄子指出了一个语言难以企及、心却能游至的世界。这个世界更为重要,人却无法获得关于这个世界的绝对知识。所以庄子说:“知止其所不知,至矣。”(《齐物论》)庄子建议:“至则不论,论则不至。明见无值,辩不若默”(《知北游》),“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BP:忘记语言和概念,保持沉默才是最高的境界。对于此,维特根斯坦也曾说过:“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12]第二,语言在去蔽的同时,也产生了遮蔽。庄子说:“辩也者,有不见也”;“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齐物论》)
人为的、区分性的名言概念有使真实的世界隐藏起来的危险,并造成对“道”的“亏欠”:“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齐物论》)由于这种区分,我们便产生了爱憎、好恶、取舍等附加在“物”上的人为评价。其实,事物只有一个根本属性--存在,所谓是非、善恶、美丑、成毁、大小、众寡,都是人为添加的;原本混然一体的万物在人的分辨之下呈现出高下、优劣、利弊的不同,甚至使实际上相互关联着的事物显现为真理和谬误。既然这些衍生物是人为添加的,并不真实,由它们组成的所谓客观真理本身也就受到了质疑。庄子认为不存在绝对确定的、必然的、不容质疑的真理。对世界的理解可以有无限的可能形式,“语言一世界”(word-world)也包含着其自我实现的无限的可能方式。第三,庄子质疑了语言与权力结合带来的强制。儒家、墨家都认为“名”能准确表达“实”.墨家主张“以名举实”(《墨子·小取》),荀子提出“制名以指实”(《荀子·正名》),“名”、“言”变得十分重要。孔子非常重视语言媒介的作用,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
儒家力图通过树立语言、经书、圣人之言的权威性,以此来规范现实社会,突出了语言的政治伦理功能。庄子却认为儒家推崇的“圣人之言”是“糟魄”(即“糟粕”,“魄”是“粕”的借词),他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天道》)《天道》篇还记载了轮扁将桓公所读的圣人之书说成“糟魄”,他说:“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这里,庄子借轮扁之口说出圣人之书是“糟魄”,强调个体应重视独立思考和切身体验,不要盲目崇拜古人和权威。对此,庄子还说:“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天运》)儒、墨都将自己的言论作为是非的标准,并在此标准之上建立起各自的道德体系和社会制度。
庄子认为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做法。当时社会既有的制度,不但不能解决当下的社会危机,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恰是它们导致了世人的苦难以及社会的动乱。在庄子看来,世人之所以以书为贵,是因为书籍记载了圣人的言语,这些言语传达了某种意义;但实际上真正给出意义的那个存在却是不能言传的。庄子以此质疑了“正名”、“正言”的语言独断,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压抑和意识形态束缚上3]现当代哲学也反思了传统理性主义将真理的客观性加以绝对化的倾向,如福柯认为,知识与权力是共生体,“我们被迫生产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权力的真理”[14],而这种真理总是属于某种“知型”.由此可见,这种解构与庄子的质疑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儒、墨不同,庄子把语言作为达意的手段,认为目的达到后可以抛弃手段,甚至认为最高的境界是忘记语言。对于麦克道尔而言,语言作为第二自然是心灵与世界之间不可缺少的联系。
他围绕语言进一步证明:语言能力赋予我们概念能力,概念能力渗透到经验之中并使得经验本身成为概念能力的实现。所以我们并不是用语言来表达思维,而是借助于语言来实现思维,用语言进行思维。没有语言,就没有思维。[151语言既是思想的承担者,又是思想的界限。麦克道尔缜密地论证了以语言作为基础的经验的概念性,从而突出了语言的不可或缺性。如上所述,庄子已经有了“我们是以概念的方式来经验世界”的思想萌芽,麦克道尔则明确提出思维与经验都是概念的,经验是以概念的方式在描述世界。他试图以此来打破思维与经验的分野。心灵在世界之中,但不是受到因果律制约而丧失了自由的被动存在,而是发挥了概念化的能动作用的主动现象。
上述观点被称为概念论(conceptualism),与之相反的观点叫作非概念论(non-conceptualism)。后者认为经验的某些内容是非概念的,经验还需要一个概念化的过程。麦克道尔的概念论则认为,经验的内容是彻头彻尾的概念的东西,经验本身是对世界的概念化。只有在概念能力的拥有者那里,知觉才使得我们接触世界而不只是应付环境。[16]庄子认为,由于主客变化无常以及“成心”,而使得各种理解难以通约、不可让渡、不可传达,因此重点论述了其差异性。如对于“得道”那种模糊的感觉,庄子形容说:“形解而不欲动,口钳而不欲言。”(《田子方》)这里,庄子指出这种私人感觉、主观印象难以变成公共话语。事物对于“你”就是它向“你”显现的那样,对于“我”就是它向“我”显现的那样。对同一事物的诠释会因个体及具体情景的差异而呈现出无穷无尽的可能性,解释者之间难以形成“公是”.对于麦克道尔,文化是公开性的,意义在一个群体中是公开的。
只要被言说的对象是同一个,就已经产生了通约性,它们就不只是私人对象,而是公共对象。以语言形式展开的精神活动也是公开性与公共性的,其应用是社会性的。从根本上说,这样的精神活动是一种公开可见的活动,它的天然居所不是在个人的心灵和头脑中,而是在广场、庭院、市场等公共场所。所以麦克道尔重点论述了语言的共享性。他认为语言、概念是一个社会中所有成员都共同分享的、先于我们而存在的传统,因为这个传统我们才得以生活在一个意义世界之中。经验具有概念内容,意味着经验主体能够与其他社会成员因共同继承的语言传统而共享经验。我们的语言能力已渗透到知觉之中,所以我们是以一种为社会成员所共享的概念的方式来经验世界的。他说:“在使人类成熟中起关键作用的教育里,学习语言最为重要。被接纳进一种语言,人类就被引人到某些已经体现着被公认了的概念之间的合理联系之中。
首次被接纳进一种语言,这种对自我产生限制、体现了心灵的语言是先在于自己的,这也得以让她适应这个世界。……语言是传统的储藏室,储备着历史地积攒起来的那些解释何事之为何事的智慧。每一代继承这个传统的人们对此都有所修改。继承传统的一个常设性义务就是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如果一个人意识到在这个连续性中占据其位置的潜能,这与获得那种能思考、有目的的行动的心灵是一样的,首要的就是接纳进一种传统。”[17]在麦克道尔这里,概念、语言是所有社会成员共有的东西。就像一个人不可能具有私人语言一样,一个人也不可能具有私人概念。当庄子说婴儿能言是与能言者相处时,也可以由此推出,婴儿习得的这种语言是每个人从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继承而来的社会成员共享的传统,因而具有通约性。语言不是私人对象,而应该是公共对象。但庄子更多地是从语言作为表意工具,以及语言要表达的内容具有不确定性出发,看到了一个难以达成共识而争论不休的世界。
结语
庄子和麦克道尔在都承认语言重要性的前提下,讨论了不同的问题。庄子面临着古代社会以名欺实、盗名欺世、名实的混乱加剧着社会的无序这一现实,侧重指出了语言的局限。在哲学上,庄子论证了我们之所以能够产生认识是因为语言把混沌的世界分离了,语言的目的在于表达思想,但最高的“道”却超越了语言,于是“辩不若默”成为最好的选择。麦克道尔所面临的则是当代社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哲学日益自然化的现实。当代盛行的各种物理主义如取消论、还原论物理主义、非还原论、同一论、特性二元论等,都声称所有关于心理的事实都是以物理事实为基础的。
物理世界最基本的规律就是因果律,心灵在物理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形而上学、宗教、伦理、自由意志都成为一个物理世界多余的假设。麦克道尔在论证经验是概念的同时,修正了心灵是受制于因果作用的物理现象的理论,弥合了心灵与世界二分的传统形而上学思路。他的概念论重视语言的正面作用,试图通过论证知识中语言、概念与经验的共时性,以解决现代哲学中潜在的二元论问题,论证了我们用概念建构起来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因果律作用于其中的物理世界,更是一个实在的世界、一个与我们有感应关系的世界、一个心灵在其中有确定位置的意义世界。
最后,麦克道尔的分析哲学强调符号与对象之间的清晰对应,追求语言表达的客观性、精确性、科学性,强调思维与语言之间的同一性。庄子则提倡一种整体思维和直觉体验,这种体验与语言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需要在明晰化、确定化的表达之外,使用一种开放性的模糊语言,以摆脱语言与意义之间逐一对应的僵化关系,突破语言对思维的束缚。这两种语言策略各有利弊。逻辑语言所对应的逻辑思维方式为了保持认知和推理的严密性,往往带有片面、孤立、静止的倾向。庄子提倡的“卮言”、“忘言”等言说方式有指称不清晰、推理不缜密的问题。
今天我们需要在保持这种语言的洗练、绚美和简洁的特色时,增加明白、清晰、准确、富有逻辑等特征,使得中西语言能够优势互补,以更为丰富地展现语言与世界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