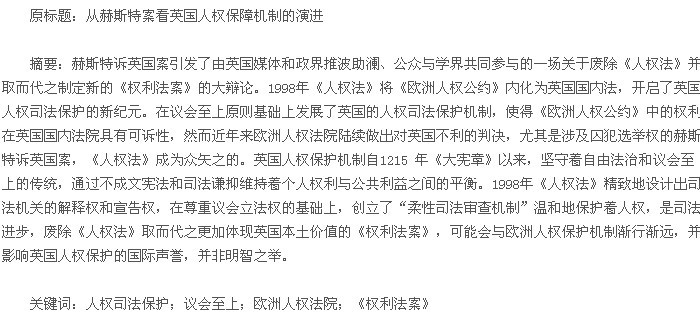
一、问题的提出
赫斯特案以及近期发生的一系列案件使得英国与欧洲人权法院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英国民众的不满加上政党和媒体的推波助澜,矛头所向直指1998年通过的《人权法》(Human RightsAct),甚至有极端的观点声称英国应该退出《欧洲人权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拒绝由远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来裁决英国国内的人权问题。关于废除《人权法》并制订一部新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的呼声日益高涨,围绕着是否需要以及建立一部什么样的《权利法案》的讨论在英国社会形成了一场由媒体、学者、政客和民众共同参与的大辩论。
(一)赫斯特案的基本情况
约翰·赫斯特(John Hirst)是一名因过失杀人而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囚犯,由于被禁止行使选举权,2001年包括赫斯特在内的三名被判刑的囚犯向英国高等法院起诉,但被判败诉。之后赫斯特单独向欧洲人权法院起诉(Hirst v. the United Kingdom)。2004年3月,欧洲人权法院对该案件进行了审理,并一致认为,英国法律未考虑犯罪的性质或严重程度,而直接禁止所有囚犯行使选举权的规定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一议定书》(以下简称《第一议定书》)第3条①。该议定书的第3条规定,在确保人民自由表达意见的条件下,以适当的间隔和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立法机关的权利。
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囚犯被剥夺人身自由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丧失了公约所规定的对其他基本权利的保护”。英国政府则声称该项禁令是正当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和惩罚罪犯,同时提高公民责任意识和对法律的尊重;然而,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并未发现任何证据支持‘剥夺公民选举权遏制了犯罪’这一观点,同时认为,不考虑其罪行或个体情况而对所有囚犯不加区分地施以这一惩罚,表明在该惩罚与违法者之间并不存在合理关系(rational link)”②。英国《人民代表法案》中禁止所有在押囚犯行使选举权的规定与《第一议定书》第3条相背,因此英国违反了其条约义务。
欧洲人权法院接受了英国所称的“成员国在如何规定禁止或限制囚犯行使选举权这一问题上应当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的观点,但也指出,由于构成了对《第一议定书》的违背,必须对其现有规定作出改变。尽管法院要求进行立法上的变更以使之符合《第一议定书》,但法院并未对于英国如何修改法律提出细节上的引导,因为依据《公约》,这一权利属于成员国自由裁量(margin ofappreciation)的范围。“法院认为这是一个存在广泛自由判断余地的领域,应当由国家立法机构来决定限制囚犯选举权在当代社会是否仍具有正当性;以及,若具有正当性,应当如何达到一个公平的状态。特别是,应当由立法机关来决定对选举权的限制是否应作出调整;但法院所不能认同的是‘不加区分地禁止所有正在服刑的囚犯行使选举权’,认为这并非一个可接受的‘自由判断余地’原则的结果。”
③2005 年,英国政府向欧洲人权法院大法庭提出上诉,认为“被判入狱之人已被剥夺其在国家治理上发言权”。2005年10月,大法庭以12比5的票数否决了英国政府的上诉,并再次强调,对囚犯选举权不加区分的禁止显然违反了《公约》。判决之中强调:“毫无疑问,依据英国当前的法律规定,一个囚犯是仅仅因其‘犯罪而成为被囚禁者’这一事实而被剥夺了公约权利;《公约》之中也不存在任何余地容忍、包容一个民主社会仅仅基于可能违反公共舆论而自动剥夺公民选举权。”
④由于英国未能履行上述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对其立法作出修改以符合《公约》,对《第一议定书》的违反这一问题在格瑞斯(Greens & M. T.)一案中再次被诉至欧洲人权法院。原告认为拒绝将其登记入国内和欧洲选举的选民登记册违反了《第一议定书》的第3条。2010年11月23日法庭再次判决英国政府违反了自由选举的权利。法院发现英国政府未能修改其“完全禁止”⑤的法律,甚至从未按照欧洲人权法院在赫斯特案判决中的要求去尝试进行立法修改。法院认为英国政府应当立刻提出立法建议来修改法律,并在由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所确定的时间框架内使之得以施行⑥。
(二)英国囚犯选举权问题的由来
在英国,囚犯的选举权被视为一项有限制的权利,对于这一权利,国家依法可以在某些情况下进行干预。这一权利可能需要平衡个人权利与更广泛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存在明确的理由,并且是为达到正当目的时干预才可被允许①。英国剥夺囚犯政治权利的做法可以追溯至1870 年《没收法案》(Forfeiture Act of 1870),在该法案中提出了“公民死亡”(civic death)②这一概念,否认了罪犯的公民身份,任何犯叛国罪或因犯其他罪而被判处十二个月以上监禁的人在其服刑期间均不得享有选举权。
1969 年的《人民代表法案》引入了一项特别条款,规定“在 1967 年的《刑事犯罪法法案》对 1870年《没收法案》修改后,被证明有罪之人在被关押期间依法不得行使选举权”。1983年的《人民代表法案》(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 1983)整合吸收了上述规定,该法案第3条进一步规定“任何人,一旦触犯与选举有关的罪行,即丧失资格10年”。在1983年《人民代表法案》基础上修订而产生的1985年和2000年《人民代表法案》中延续了此规定。该法案使所有被判处监禁而正在服刑的囚犯在服刑期间丧失选举权,而只有那些在押候审的人可以参加选举:任何被证明有罪之人在被关押于刑罚执行机构履行判决期间(或是在被关押期间违法脱逃者),依法在任何议会或地方政府选举中均不得享有选举权。
(三)欧洲人权法院判决后英国的法律发展
在欧洲人权法院作出赫斯特案的判决后,英国并未成功修改其选举立法以符合《公约》规定,甚至并未进行此种尝试。这一问题在英国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大多数民众反对囚犯拥有选举权,他们认为下议院应当积极表达这种主张,而不是让那些“并非本国国民选举产生的外国法官”来决定;还有一些人认为英国应当退出《公约》,站在其公民一边,确保议会至上原则。也有人考虑到更为长远的问题,英国作为《公约》原始签署国所应承担的责任,贸然退出或拒绝执行可能对其他缔约国和非缔约国的影响。
在格瑞斯案判决后,2010年12月20日,政府宣布将提出立法建议,允许被判处监禁少于四年的囚犯在英国议会和欧洲议会的选举中享有选举权,除非量刑法官认为不适当③。2011年2月,下议院投票234票比22票对“不加区别地禁止(blanket ban)行使选举权”的规定表示支持。尽管仍在考虑对法院六个月的“最后通牒”作出回应,政府要求欧洲人权法院再次将这一问题提交至大法庭,希望议会对于该项规定的支持可以迫使欧洲人权法院屈服。4月11日,该项诉求再次被驳回,法院再次要求英国在六个月内提出立法修改建议。与此同时,英国国内的民粹主义和狭隘者(pop-ulist and illiberal forces)伺机掀起对欧洲人权机制的又一轮抨击,甚至要求退出《公约》④。2011年9月6日,由于斯高珀拉诉意大利(Scoppola v. Italy)⑤案(案情类似于格瑞斯案)的出现,英国向大法庭提出延期以参考该案件的审理结果,法院批准于该案作出判决之日再起算六个月期限。该案判决于2012年5月22日作出,判决中法院再次强调了赫斯特案的判决,即不加区分而自动地剥夺所有囚犯的选举权与《第一议定书》第3条相悖。2012 年 11 月 22 日,英国政府公布了一项含有三条建议的《选举资格(囚犯)法草案》,由上下议院的联合特别委员会(Joint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Draft Bill)进行立法前审查(其中两条建议允许在一定监禁期限之内的囚犯享有选举权,期限为6个月或者4年;第三条建议则考虑了当前立法中完全禁止囚犯享有选举权的规定①),联合特别委员会于2013年12月18日公布了审查报告,建议政府通过颁布“赋予某些囚犯选举权”的法律以遵守欧洲人权法院关于赫斯特案的判决;并建议该法案应在2014-2015年国会立法之初提出,该报告建议赋予所有应服刑期为12个月及以下的囚犯在英国议会、地方议会和欧洲议会选举中的投票权,并且,考虑到囚犯选举权恢复后的重新适应(re-habilitation),依其预定释放日期 6 个月前应当允许其登记进行选举(此类适用于刑期在 12 个月以上者)②。但直至今日,英国关于赋予囚犯选举权的立法修改仍被搁浅③。
欧洲人权法院遵循了数十年来系统发展出,且已被许多先进自由民主国家的宪法法院所接受的法律原则: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不加区分的限制本质上是不符合比例原则的④。法院并未要求英国给予每个囚犯以选举权,只是认为“囚犯有权利不因不加区分、自动的原因”而被剥夺选举权。
英国所需做的不过是使该种禁止与违法行为的性质或所判决的刑期相适应,并赋予国内法院判断每个个体罪犯情况的权利;因此存在多种立法上的选择可以使英国的法律在符合《公约》的同时,使那些犯了严重道德错误的人在立法机关的选举上不享有投票权。许多违法犯罪之人并不需要剥夺选举权,而也有许多存在刑事犯罪的人不必加以囚禁却需要剥夺其选举权;因此,不加区分地禁止(blanket ban)不具有正当性⑤。
意欲废除这部“将权利带回家”的旨在内化《公约》使之在英国国内具有法律效力的《人权法》,英国似乎又一次徘徊在与欧洲人权机制离合的十字路口。分析这场大辩论的来龙去脉,还需从英国的人权发展过程以及英国的法治传统开始。
二、英国传统人权保障机制的特点
英国经过长期的政治斗争和法律演进过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权保障法律制度,其中不成文宪法传统下的法治原则和议会至上原则是主要的特点。
(一)不成文宪法传统下的法治原则
英国经过几个世纪漫长的发展最终形成现在的宪法体系,英国是典型的不成文宪法国家,英国宪法渊源于各种成文或者不成文的法律文件,包括成文的宪法性法律,涉及宪法制度的法院判例和已经确立不成文宪法惯例。英国虽然没有编撰的成文的宪法,但是它不成文的宪法体系很大程度上扮演着类似于其他成文宪法国家宪法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不成文的宪法体系被认为是一种可更好调整的宪法类型,它可以根据实际惯例和实践来确定宪法的内容而不被固定或形式的法律规定所束缚。英国的宪法是根据历史发展不断累积起来的法律条文和惯例的综合体,可见英国宪法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渐进式地发展起来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①。英国公民权利的实现是通过权利限制权力来实现的,它并不像一些成文法国家,通过宪法来规定公民享有哪些基本权利进而权利能够得到相应的保障。梳理英国的历史不难发现,从1215年《大宪章》到1679年的《权利法案》都规定王权要受来自议会制定的法律的制约,使得“法律在上,王权在下”的思想得以确立。这些都说明英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法治传统的国家,英国自跨入文明社会起,它的习惯法就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崇高的权威。光荣革命之后,议会权力和立宪政体得以确立,英国资产阶级以《权利法案》的形式规定了人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宣布了“法治”为原则的宪法文件,并且在启蒙思想家的法治思想影响下,形成了“英国人只受法律的统治”的法治模式,英国的实践表明,这种模式的实际运行是以议会至上原则为前提的,即制定法律的权利属于代表人民意志的议会,议会通过“法律统治”把公权力限定在法律规则之下,进而实现对于个人权利的保障②。
法治原则的基本含义:第一,法律至上,除法律外任何人的行动不受阻碍,“人民受法律治理”,犯法之人“除法律之外,再无别人可将此人治罪”。第二,任何人没有特权,任何人犯了法必须与民同罪。第三,关于个人权利的一般宪法原则都是司法判决的成果而不是权利宣言之类的空论。但是不成文宪法传统下法治的模式也有其本身的局限性,英国是奉行议会至上的宪法原则的国家,它就会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如果议会没有法律拘束,容易使议会拥有像历史上国王那样的专制特权进而有悖于法治的精髓。像一些成文法的国家都存在司法上的违宪审查制度来审查议会的立法,就英国司法机关审查议会立法的权限来讲,英国并不存在违宪审查,因为英国奉行的是议会至上的宪法原则,司法机关没有权限来审查议会的立法,议会的立法权限不受限制,但是在英国议会只能通过公众的舆论和英国的传统对其进行无形的约束。1998年《人权法》生效之后,第3条规定“如有可能,基本立法和次级立法必须以一种与公约相一致的方式被解释并赋予效力”,这说明英国法院在议会至上原则的前提下在处理涉及侵犯《公约》权利的案件时,法院可以审查议会的立法并适当地修改和解释议会的立法以便使得国内法符合《公约》的规定。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法院对于违宪审查的权力,为防止议会立法侵犯公民权利设置了一道保障。
(二)“议会至上”的原则
议会至上原则是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实现英国公民权利保障的重要原则。议会至上的概念,一般需要区分其政治意义和法律意义。法律意义是指议会拥有制定或不制定任何法律的权力,英国法律不承认任何团体或者个人拥有推翻或废止英国议会立法的权利。从政治意义来讲是指议会是主权的载体,议会的意志在英国处于最高的地位,英国的戴雪是率先提出议会至上概念的人,但是他说的议会至上概念仅限于法律意义,因为政治意义上的议会至上仅具有相对意义,无论对内对外都达不到“绝对、至高无上、永恒的权力”。戴雪认为议会至上的性质包括议会有无限制的立法权力和议会立法权力的最高权威性③。
追溯英国人权保障的历史,不难发现议会在争取权利和自由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早期的英国法中并没有“议会至上”的概念,议会立法在当时的立法体系和法律渊源中不占主导地位,法庭认为习惯法和自然法则超越议会的立法,所以当议会立法同传统的法律渊源发生冲突时,议会立法往往被宣告无效。英国议会制度产生于中世纪早期,当时的议会主要是指大贵族组成的议事会,随着国王和贵族矛盾的激化,如《大宪章》、《权利请愿书》中国王都被迫接受议会提出的权利主张,尤其是1322年颁布的《约克法令》进一步规定了“议会中的国王”的原则,即一切重大国家政治事宜均须由国王在议会中加以处理,没有议会的同意国王不得擅自决定,这就是以法令的形式肯定了议会的法律地位。到了16世纪,以限制王权为核心的议会至上思想开始出现,17世纪早期查理一世统治时期,曾经解散议会经历了无议会的专制统治时期,这在某种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直至1688年的光荣革命,使得议会在与国王的斗争中取胜,法庭也与议会站在一起进而确立了议会的主权地位①。《权利法案》确认了英国应该享有的13项权利和自由,以宪法的形式保证国王服从议会,遵守议会的立法,议会的权力高于王权的原则得以确立,主权的重心开始从王室转移到了议会,议会开始成为了“主权者”②,确立起英国现代的君主立宪制。1701年议会通过《王位继承法》,进一步将王权置于资产阶级控制的议会之下,英国议会至上原则得以进一步确立和巩固。
在英国长期的普通法传统中,议会至上原则逐渐发展为英国宪法的核心原则,议会至上主要包括两项内容:第一,议会拥有无限的立法权。第二,议会的立法权不存在竞争,在议会方面,议会的权威不容质疑,立法权由议会独占,并且议会的立法范围极为广泛。议会所制定的成文法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必须遵从,司法机关无权对议会制定的成文法进行审查,这也表明英国议会至上原则的特点,即法院不能挑战议会法律的有效性,如果法律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只能由议会自身按照法定的程序制定新法,并遵循“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从而将议会至上进一步发展为当前议会至上③。
英国的法治传统逐渐发展了具有英国特色的“政治性宪法”,即由民选代表决定争议的法律问题,而不是由法院作最终决定。但同时议会、行政机关、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公共权力部门必须尊重正义、公平和法治的基本原则④。这些原则是经过长期的政治斗争和法律发展形成的,可以追溯到1215 年的《大宪章》。17 世纪议会和国王的冲突成就了英国率先建立起民选政府优先、尊重宗教宽容和言论自由的基础,后来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又逐渐补充了扩大选举权和尊重个人权利与法治。英国尊重自由的传统也深刻影响了战后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对《世界人权宣言》和《公约》都有积极的贡献。
人权是充满争议的概念,是否构成人权的侵犯通常会存在深刻的分歧。尤其是如何平衡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冲突,相对于司法而言,政治领域更适合解决正义、公平、权利冲突等有争议的问题。如英国议会对同性伴侣立法和移民政策的设计有最终决定权。但完全依赖政治过程保障人权和法治也存在不足之处,因为在由多数人决议的政治体系中,少数人、弱势群体容易受到歧视和其他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如果民主意味着代表一国之内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大多数,那么就必须建立一种机制,让每个人平等自由地参与民主的过程。而且,大部分国家的日常运行被行政机关操控,通过政府经常对议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就限制了议会有效地问责政府、警察和其他公共机构,公共权力部门享有宽泛的权力,难以受到有效的约束。当议会立法机关意欲保护个人权利时,行政机关常处于支配性的地位。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法院逐步发展为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人权保护的过程中,这是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趋势,不仅发生在英国,其他国家也类似。那就是赋予当事人向法院提起司法审查的权利,行政机关需要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和对个人权利的影响。这使得没有政治权力的个人和组织能够借助法院这个平台挑战缺乏正当性的法律,法院对行政和立法机关合法行使其权力起到制约作用。
然而,对于法院在何时以及如何介入人权保护中,换言之,谁享有最终的决定权,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实践。美国、德国、南非等国家的法院被宪法赋予了广泛的权力,可以推翻违反人权的立法,而在英国,法官可以推翻违反人权的行政机关颁发的行政法规,但最终立法权仍掌握在议会手中。
三、欧洲人权法院与英国人权保障机制的关系
(一)英国对欧洲人权保护机制的贡献
与当前英国国内舆论声讨欧洲人权法院为舶来品相反,欧洲人权保护机制中流淌着英国血统,反映着它自由法治的传统精神。欧洲人权保护机制的产生很大程度是受到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影响,国际社会在构建人权体制的同时,欧洲国家也在激烈地讨论着欧洲人权保护事宜,早在1946年,英国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其演说中第一次倡导和推动创建欧洲理事会。由非政府组织倡导的“欧洲统一运动国际委员会”于1948年5月在海牙召开了欧洲大会,来自英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等国的代表积极发表意见,大会决心通过人权宪章的形式来保障欧洲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并且希望可以建立一个公正的法院通过法律裁决的方式来实施此宪章规定的权利。
1948 年 6 月英国国会的代表团包括温斯顿·丘吉尔作为起草委员会之一对于草拟《公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公约》的起草和撰写是在大卫·麦克斯韦·法伊夫(David Maxwell Fyfe)的监督下完成的。英国参与《公约》的建立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它规定的权利和自由深深地根植于英国,其最终版本受到英国人权思想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关于权利的定义方面。1950年11月4日欧洲理事会通过了《公约》,并且英国作为第一个国家在1951年加入了《公约》,奈尔勋爵(Lord McNair)作为英国法律学者于1959年当选为欧洲人权法院的第一任领导①。英国在促进欧洲人权机制构建的同时也受到其深刻的影响,尽管长期以来英国对于《公约》持保守的态度并反对将公约的权利纳入到英国的国内法律体系中,部分原因是英国认为公约规定的权利英国国内的法律已经给予了很好的保护,没有必要进一步援引《公约》的权利。但是随着国际及区域性人权机制的逐步完善及对于人权保护的加强,英国国内则日益凸显对于人权保障的弊端,这也是英国进行国内人权改革的重要原因。
(二)欧洲人权法院判决对英国的影响
欧洲人权法院作为《公约》的司法实践机构,秉承动态解释方法(即将其视为活文件(living in-strument),根据当前的社会情势和观念解释公约中的权利,如古德温诉英国案),在处理法院判决与成员国的关系上,法院遵循自由裁量余地原则,允许成员国在执行《公约》标准时考虑本国的特殊国情,采取自由裁量的措施,使得一国在衡量事实情况和在适用国际人权公约时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欧洲人权法院对英国人权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但这并不是说英国总是扮演败诉国的角色,事实上,据统计,绝大部分以英国为被告的案件并未达到立案标准,因此不具有可受理性。
在1966-2010年间,大约有14460件个人起诉英国的案件被递交至欧洲人权法院,绝大部分被驳回,其中只有1.3%的案件法院判决英国败诉①。然而就是这微乎其微的败诉判决推动了英国人权法的发展。英国较好地执行了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一方面是履行国际义务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英国珍惜其良好的人权国际声誉的需要。
英国传统对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模式是以尊重公民的消极自由为核心,公民作出任何行为的前提是考虑是否存在这样的自由,但是不成文宪法传统的英国并没有对于自由和权利的明确规定。
《公约》虽然规定了公民的广泛权利和自由,英国也是缔约国,但是鉴于条约法在英国国内的地位问题,实际上公约并不能在英国国内产生直接的法律效力。正如奥利弗勋爵解释:“根据英国宪法,未经国会许可,英国国王缔结条约的特权不得扩及改变法律或授予个人权利,或剥夺个人在国内法中所享有的权利,除非条约经过国内立法纳入到英国国内法律体系中,否则条约并不是英国法律的一部分。”
②英国法院也一直遵循不直接援用国际条约的司法传统,即认为《公约》在被引入英国国内法之前没有法律实施效力③。 丹宁勋爵法官(Alfred Thompson Denning,1899-1999年)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公约》在纳入英国法之前,英国法官并不必然受该公约及欧洲人权法院判例的约束:“应该让英国法院注意公约所阐明的原则和例外,但不要因此而受到它的限制;应该让法官斟酌情况接受,或舍弃或变通公约的条款以适应我国的环境;应该让议会重视斯特拉斯堡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但不能完全服从他们。应该由议会决定是否采用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以及是否使其成为我们法律的组成部分。不能让我们受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对我们的普通法一无所知的法官所做的判决的约束。”
④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开始正视其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不足,并对英国既有的权利保障模式进行思考。从1970年至1990年,各种呼声要求制定或者通过《人权法》或者将《公约》纳入到英国国内法,这些意见来自政治界、独立团体、议会内外等各个方面。1997年普选结束,民政局长杰克·肖(Jack Straw MP)发表了名为“把权利带回家”的白皮书,该议案只是劳工党倡导的一揽子民主革新的一部分,其还包括政府权力下放、上议院改革和情报自由,将《公约》纳入国内法体系,以利于当英国法院破坏公约规定的权利时能够提供很有效的救济,但是涉及公约的问题其最终的裁决权仍然归属于斯特拉斯堡法院。这将使得公约权利能够“更巧妙和有力地植入到我们的法律中”⑤,最终1998年11月《人权法》得到了女皇的同意,并于2000年10 月 2 日正式生效。1998 年《人权法》的主要目的是使英国在《公约》的框架下可以更好地实现其国际职责和对于国内侵犯公约权利的情况能够提供有效的救济。
(三)1998年《人权法》确立的人权司法保障机制
1998 年的《人权法》包括了 22 个条文,其中并没有将《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全部权利都纳入进来,它删除了第1条(关于国家保障权利和自由的义务)和第13条(关于获得有效救济的权利),由于英国并未批准《公约》第 4议定书和第 7 议定书,因此也就没有包括这两个议定书所保障的权利①。该法在尊重议会至上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英国特色的柔性司法审查制度,精致的制度设计巧妙地平衡了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关系,并通过法院行使解释权和宣告“不一致”权,温和而有效地保护人权。
第一,1998年《人权法》通过之前,英国原来的国内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是基于普通法的原则,任何人有权做法律未加禁止的任何事情,但是1998年《人权法》的通过及实施使得英国法律在决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首先必须考虑到《公约》的存在,因为《人权法》规定:法院或者法庭在决定一个与《公约》有关的问题时必须考虑任何出自公约的法院和制度的法律性主张及相关程序:包括(1)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决定、声明或建议;(2)根据人权公约第31条的规定而接受欧洲人权委员会的意见;(3)欧洲人权委员会作出的与人权公约第26条或27条第2项有关的规定。由此可见,《公约》实际上成为英国法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②。
第二,《人权法》第3条要求各级法院检查议会立法及其授权立法是否符合《公约》的规定,不论该立法或者授权立法是在《人权法》通过之前还是生效之后,第4条授权法院在议会立法与《公约》不一致的情况下有权作出不相符的宣告。
第三,《人权法》的生效其最直接的效果就是英国公民的公约权利如果在国内受到侵犯的话,可以直接在英国法院主张权利救济,这就大大避免了之前申诉至设立在德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所要耗费的大量的时间、金钱与精力。可见《人权法》的颁布实施实质上赋予了英国法院有限的司法审查权,其实施促进和改善了英国人权的司法保护制度和司法改革,并增强了英国的司法能动主义倾向。适用《公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英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四,《公约》与英国法律的“结合”对于英国的立法过程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98 年《人权法》第 19 条规定:(1)在上议院或下议院负责法案的王室大臣在对法案进行二读前必须:(a)作出一个其认为法案的规定与公约权利一致的声明(“一致声明”);(b)作出一个虽然其认为不能作出一致声明,但政府仍希望(议会)能继续这个法案的声明。(2)该声明必须是书面的,且须以作出该声明的大臣认为适当的方式公布。可见议会的法律起草者和提出议案的部长们必须考虑到与《公约》的“兼容性”问题。这将是对英国“议会至上”宪法原则的巨大挑战③,但是并没有根本上动摇“议会至上”作为英国宪法基本原则的地位。
第五,《人权法》的通过对于法律解释方面也产生了影响,具体就是《人权法》第 3 条规定:(1)应尽可能将对基本法和附属法的解释和效力与公约规定的权利保持一致。(2)本条(a)适用于任何时候颁布的基本法和附属法;(b)不影响任何不一致的基本法之效力、继续适用或执行;和(c)不影响任何附属法的效力、继续适用或执行,如果(不考虑任何废除的可能)基本法不禁止不一致的存在。
这就表明英国法院在今后解释法律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公约的存在并且尽最大程度以与公约权利最为符合的方式和法律用语来解释英国议会的立法。
1998 年《人权法》并没有创设新的权利,只是将《公约》中的相关权利纳入到国内法的体系里。
1998 年《人权法》是英国人权改革的重要成果,它突破以往英国国内人权保护的模式,将《公约》规定的权利保护模式引入到国内法体系之中,规定了公民享有公约规定广泛的权利,也明确了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时需要采取的明确法律救济模式和程序。1998年《人权法》生效之后,英国法院可以实施审查议会立法的活动,也即是在诉讼活动中,如果出现与议会立法有关的问题,法官可以依据《人权法》第3条的规定,对和《公约》不一致的立法,法院可以视情况对立法作出尽可能符合公约的解释,这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法院的解释权和“不一致”宣告权。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英国由此建立起柔性违宪审查制度。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人权法》没有动摇议会至上的基础,仍然是英国宪法最核心的原则。
《人权法》和一系列法案的通过使得英国人权保护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总体来讲,现存的英国人权法能够得到法律学者和法官的支持,但是同时也面临着批判。2007年劳工党开始咨询构建新的《权利法案》,其他的一些政党也加以呼吁。评论者指出需要重新审视英国和斯特拉斯堡法院的关系,他们认为英国《人权法》和斯特拉斯堡在法理上太贴近了,在他们看来,这将阻止英国法院在法理上作出本国成长性的突破,更不能够很好地体现英国的价值。另外一些评论者指出《人权法》是依照公约权利建构的,所以某种程度上不尊重英国传统法律和管理模式,英国《人权法》赋予英国法院过渡的权力来干预民主决定,故此有扰乱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之嫌①。他们希望可以制定一部新的《权利法案》(A Bill Of Rights)来替代《公约》框架下的1998年《人权法》,这样的呼声和辩论,迫使英国政府建立了人权法案委员会,其专门负责研究英国是否需要新的《权利法案》来保护和延伸保护现存的权利和自由。
四、从《人权法》到“权利法案”?
在《人权法》刚刚生效之初,曾被盛赞为“这个国家三个世纪以来拥有的第一部权利法案”②。
但近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一部新的“权利法案”的辩论,并且在政党之间似乎已经形成了一致,认为需要这样一部新的“权利法案”③,不同的是需要一部什么样的新的“权利法案”。
(一)辩论之中的一些主要观点
1.以新的“权利法案”来反映英国本土价值(Britishness)
《人权法》号称“将权利带回家”,但实际上,在制定之前并未向公众进行公开咨询,并将《公约》全盘吸收,使之不再可能具有美国《权利法案》一样的标志性地位④。英国首相卡梅伦就认为:“一部现代英国‘权利法案’……来界定使我们成为一个自由国家的那些核心价值”⑤。一部新的“权利法案”将注重公众在立法上的参与,使英国人有相对于《公约》和《人权法》的“主人翁感”。卡梅伦的主要观点是以一部英国本土的(home-grown)法案来促进欧洲人权法院“后退”(back off),以减少对英国议会主权的妨碍。但这一观点并不正确,更狭窄、特定化法案将使英国免受欧洲人权法院判例影响的观点是对欧洲人权法院自由裁量余地原则的误读。《公约》的整体目标在于在欧洲范围内为基本权利的保护提供一个最低标准,德、法等国的状况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目标。而卡梅伦却宣布将这一目标作为废除《人权法》的主要目的①。
在赫斯特案中,在欧洲人权法院判决英国“不加区分地禁止”的立法违反公约权利并要求进行修改之后,下议院仍然对这一立法投票表示支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英国对欧洲人权法院的排斥、厌恶——英国民众不愿由欧洲人权法院来对本应由英国议会决定的事项进行裁决,因为它们无法反映英国本土价值。
此外,对英国本土价值的强调还有一个目的,一部具有象征性的“权利法案”有助于加强国内团结统一,以应对近年苏格兰等地的分裂趋势。
2.在“权利法案”中增加新的权利
前文已述,《人权法》的制定是将《公约》纳入到国内法体系之中,而《公约》制定于20世纪50年代,且其条文中主要规定的还是传统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因此有观点认为,应当在新的英国“权利法案”之中吸收经济和社会权利,如健康权、居住与受教育权等,从而为英国人提供更为完整的人权保障;同时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纳入其他国际人权条约(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等)。此外,人权联合委员会还提出对发展权等第三代权利的吸收②。
3.限制对“不受欢迎群体”的保护
《人权法》未能真正被接受而根植到英国法律框架的一个原因是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在该事件发生后,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便将《人权法》视为“反恐战争”的一个障碍,特别是在法官作出拒绝在存在受酷刑的危险的情况下将可疑外国嫌犯驱逐出境的决定之时,其中便包括那些被控参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者③。《人权法》也由于为寻求庇护者、非法移民及其他“不受欢迎的群体”提供了过多的保护而受到右翼媒体的攻击。
4.限制法院权力以维护议会至上
英国人坚持议会至上的传统,因此对“非经民主选举”而产生的法官有自然的不信任感,相形之下更加倾向于依赖民主选举而产生的议会代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如前所述,《人权法》在生效后,法院在人权保障中有了相当重要的位置,通过行使“一致解释”权和“不一致宣告”权,对立法机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尽管其“不一致宣告”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但数据表明立法机关大体上严肃地对待了法院所作出的“不一致宣告”:2011年8月的一个数据表明,截至当时,议会对法院所作出的19个“不一致宣告”之中的18个进行了积极回应,修改了存在冲突的立法④。可见,法院这种权力的存在对于立法机关的权威即议会至上事实上构成了一定的影响⑤,尽管它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英国议会至上的传统。
(二)对“权利法案”辩论的评析
在1997-1998年的议会辩论中,将《公约》纳入到英国的国内法仅仅是第一步⑥。从这一点看,适时地对《人权法》进行修改也是其长久立法规划的一部分,出现对新的“权利法案”的争论也是可以理解的。从对“英国价值”的强调上看,英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法治传统的国家,其长久的历史积淀可能确实造就了一些英国所独有的价值,但《公约》的目的在于为欧洲范围内的人权保护提供一个最低的尺度,并且为成员国留出自由裁判空间,一方面保障欧洲范围内的人可以享有最低限的人权保护,另一方面也促进成员国在最低限度的水平上依据各国不同的情况给权利以更多的保护;对英国本土价值的强调对于加强公众参与、促进国家团结统一可能确实有益,但这一目的完全可以在自由裁量余地之内实现。进一步看,自由裁判余地原则也间接地尊重了英国的议会至上原则,英国议会只要为公约权利提供最低限的保护,欧洲人权法院便无由对其提出苛责。
通过一部新的“权利法案”来吸收更多的权利也可以从自由判断余地原则角度来理解。《公约》为成员国所提供的是人权保护的一个“最低标准”,并且《公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公约》及其议定书在内容上主要包含的是公民政治权利,仅有受教育权等极少数权利可归类为经济社会权利,因此作为成员国的英国完全可以越过《公约》而通过国内法给予这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人权保护,并且可以考虑将第三代权利也纳入到新的“权利法案”之中。这也就是使新的“权利法案”能够为更多的权利提供更多的保护(HRA-plus),而不是与之相反(HRA-minus)。
《人权法》生效后,法院作出了许多受到政治家、媒体、公众讨论批评的判决,其中不少都与对前述少数群体的保护有关,前文所述的赫斯特案亦是一例,类似的还有对同性恋者的保护、对非法移民的保护等等。对少数人群体的权利保障是必要的,因为这可以反映一国整体的人权状况;但这种保护也需要在立法、司法、行政方面注重少数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在不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而引起广泛批评的前提下为少数人群体提供尽可能多的保护,当然这种平衡需要很细致的把握。
《人权法》构建了一种柔性的司法审查制度,但这种在规范设计上具有“柔性”的制度事实上使法院在人权保护中起到了较强的作用,这种作用就集中体现在“一致解释”权和“不一致宣告”权之上。尽管《人权法》赋予法院的这种权利对议会至上原则有所影响,但如前所述,它并不能动摇英国议会至上的传统,并且这两项权力亦是经过“精巧”设计而尽量使之在不破坏议会至上的前提下为人权提供尽可能多的保护,司法系统相对于立法系统的地位仍然是依附的(subordinate),因此应当为法院保留这两项精妙建构的权力。
构建一部体现英国本土价值的“权利法案”是可行的,但这并不必然要抛弃《人权法》和《公约》。“权利法案”应当为更多的权利提供更多的保护,在《人权法》的基础上吸收新的权利,使英国人权保障的范围更为广泛。同时应当保持法院在《人权法》框架下所享有的权力,使之在不违反议会主权原则的前提下继续在人权保护方面发挥作用。在新的“权利法案”出现之前仍然应当充分发挥《人权法》框架下的人权保护功能;而新的“权利法案”的构建应当是在《人权法》基础上的进步。
五、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坚守传统中稳步变革
纵观英国人权发展道路,自英国1215年《大宪章》诞生以来的近八百年,人权保障机制的发展历经了思想形成、理论建构、革命行动和法制建立的过程。人权思想是与革命相伴而生的,且具有渐进性和稳步发展的特点。正是在教会和贵族与国王的斗争中,诞生可被誉为英国最早的人权立法——1215年《大宪章》,开创了以法律限制王权的先河。在人权法律的表现形式上,英国的人权立法在1998年《人权法》之前一直延续着不成文的传统,但是缺乏成文宪法并没有影响英国人权保护的水平,无论是1215年《大宪章》,还是其后的1628年《权利请愿书》、1679年《人身保护法》和1689 年《权利法案》以及难以计数的习惯、令状、判例等,构成了英国人权保护的自由传统。议会至上的宪政原则历经几个世纪的洗礼一直被英国人坚守着,即使1998年《人权法》也未根本动摇这一传统。改良而不是革命是英国民主宪政发展的特点,从历史和现有经验来看,废除《人权法》并非明智之举,不仅可能与欧洲人权保障机制渐行渐远,而且可能损害英国人权保障的国际声誉,甚至降低英国的人权保障水准。比较可行的办法仍是改良和协商,首先充分发挥《人权法》设计的温和的柔性司法审查制度,不断修正与《公约》不一致的国内法律,完善国内人权救济途径,由此通过“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来减少法院裁定案件具有“可受理性”的数量。其次,欧洲人权法院也应坚持司法谦抑的原则,适用国家自由裁量原则,缓解与英国的紧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