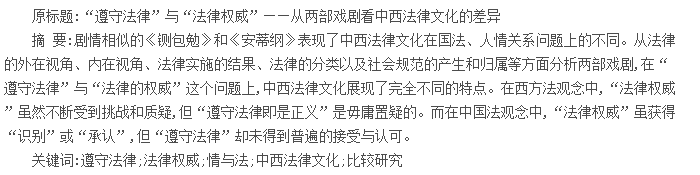
本文将以法哲学经典命题“遵守法律”和“法律权威”为核心,以两部代表性戏剧《铡包勉》和《安蒂纲》为模板,运用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流派的命题式分析方法,讨论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
一、引论
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这一宏观课题,涉及法哲学、法制史、文化研究等诸多领域,从 20 世纪90 年代开始就广为中国法学家关注。一批兼有中西法律文化研究扎实功底的学者围绕这一主题、从不同角度加以研究,产生了许多独具匠心而至今仍有影响力的丰富学术成果,法学家试图通过比较 中西法律文化揭示古代中国法的“ 基本 精神”。学界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讨论中西法律文化:第一,以(文化)类型学方法,反对简单套用西方法律概念解释古代中国法,通过找寻中西古代法律的核心精神,展现不同法律文化对各自制度设计的独特安排,如梁治平著《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张中秋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二,从法律职业人(讼师、律师)的角色、价值、权力、所处的诉讼机制和历史命运等角度,或者从法与人的关系(包括人性论、人伦关系和人格差异等方面)角度阐述中西法文化的差异,如陈景良著《讼师与律师:中西司法传统的差异及其意义》《法与人:中西法文化人格差异的解读》。
第三,从单一法学部门或法律行为进行比较,剖析中西法律文化差异,例如王宏治著《从中西立法过程比较〈唐律〉与〈民法大全〉》。第四,以法制史的研究方法,系统论述中西法治历史渊源与演变过程,如夏勇著《法治源流:东方与西方》。第五,从具体法学家的思想入手研究中西法律文化,如林端著《中西法律文化的对比——韦伯与滋贺秀三的比较》。
已有的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多注重法律制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以诠释法律文本和史料为主要研究手段,力图重现和解释经验性的历史事实,其不足之处在于,缺乏西方法理学经典命题式的研究方法。命题式的研究强调论证或证伪一个命题,将经验性材料作为论据而不作为结论,例如,以往的法律文化研究注重说明或解释“中国古代法是什么”,法理学命题式的研究则注重辨析“中国古代法如何看待或处理某个法律命题”。命题式的研究区别于直接套用西方法学概念的研究方法,它不是简单使用西方的概念来对应中国法的现象,例如用 right对应“权利”,用 power 对应“权力”,用“概念”concepts 解释现象 phenomenon,而是基于论证式的研究方法讨论问题。命题式的研究也不同于经验性的研究,经验性的研究是命题式研究的必要铺垫,命题式的研究必须依赖和借助经验性研究已有的成果和结论。经验性的研究是命题式研究的基础,而命题式研究是对经验性研究的升华。
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力图继续拓展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的领域,借鉴美国法律与文学研究流派的研究范式,引入英国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命题式研究方法,以“遵守法律”这个经典法理学命题为核心,试图从比较分析情节相似的《铡包勉》和《安蒂纲》两部戏剧入手,展现中西文化在国法、人情关系问题上的巨大差异。
本文将从法律的外在视角、内在视角、法律实施的结果、法律的分类以及社会规范的产生和归属等五个方面分析两部戏剧,展现中西法文化的不同面貌。本文区别于以往从历史渊源、部门法、法学家思想、法律职业人等不同类型的研究,也区别于从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宗教、体系、结构、价值等宏观性的研究,而将关注点凝聚于一个法理学根本命题“为什么应当遵守法律”之上,通过人们广为流传的戏剧揭示人们普遍接受的法律文化核心,探讨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
二、遵守法律与法律权威——从两部戏剧说起
《铡包勉》和《安蒂纲》这两部情景类似、影响深远但内核迥异的戏剧集中反映了“遵守法律”这个命题。通过分析这两部戏剧所展现的法文化的差异,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西方对于“遵守法律”这个命题的不同理解。本文将揭示,中国法以家庭伦理为主这个论断虽然较为准确地勾画了中国法的基本精神,但若将其与政治伦理作比较研究时,尤其是与西方对于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关系相比较时,该论断则有其局限性。在“遵守法律”与“法律的权威”上,中西文化展现了完全不同的特点。
索福克勒斯在其创作的伟大戏剧《底比斯三部曲》中塑造了悲剧英雄俄狄浦斯王,并且在最后一部《安蒂纲》中用大公主安蒂纲和新国王克雷之间的冲突,再次展现了无法逃脱的宿命这个悲剧性的主题。安蒂纲与克雷的对抗,体现了西方法律文化中的经典论题:在国家法之上存在着永恒不变的普遍正义。在黑格尔哲学中,这一古希腊悲剧还反映了“城邦政权所体现的带有精神方面普遍意义的伦理生活”和“家庭所体现的自然伦理生活”这两种“最纯粹的力量”之间的矛盾。自然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对立,以及城邦伦理和家庭伦理之间的冲突,体现了古希腊哲人对法律本质的深刻思考。这两种对立,实际上并没有对错正误之分,克雷和安蒂纲的主张都有正当的理由,并且都是“绝对本质性的”主张。作为国王的克雷有义务维护城邦的安全,维护政治权力的权威和尊严。在义务和职责的约束下,克雷作为城邦的权威代表必须惩罚叛徒,以此保证城邦法令的权威和执行。另一方面,安蒂纲认为她有义务履行同样神圣的且有自然血缘关系为支撑的家庭伦理责任,如果违背自然法的这一根本原则,城邦法的正义将无从谈起。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明确声称这种对立和矛盾“是最高的伦理性的对立,从而也是最高的、悲剧性的对立”。
家庭伦理与城邦伦理之间的冲突,情与法之间的冲突,以及戏剧中它们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凸显了《安蒂纲》的悲剧因素。不仅安蒂纲本身是反抗世俗王权的悲剧英雄,国王克雷的行为和命运也呈现了另一种伟大的悲剧意义。他在维护城邦利益和政权合法性的时候,不得不严厉惩罚亲人。正如苏力教授在评价这部戏剧时指出,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看,克雷代表的是“正在形成、尚不稳固但必将在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城邦政治制度”,因此,克雷代表的是一种“变革的力量”。克雷必须挑战已经长久确立的家族伦理体制和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克雷不仅是城邦秩序的维护者,他还是新制度的革新者以及旧秩序的反抗者。
在班考夫斯基的代表作《合法生存——法中之情与情中之法》一书中,安蒂纲与克雷的悲剧在于他们都无视对方的世界“:他们都以法律的名义保护自己,但在各自坚持己见时却丢失了人性”。他们都在自己认同的一套价值体系中与世隔离。克雷坚持城邦的规则,安蒂纲坚持神的法律,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法与情之间可能或者必然的冲突,他们只看到了规则,而忽略了偶发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的生活。“他们都希望生活是清晰可预知的,因此他们都忽视了情感的因素。”
亲情与国法之间的激烈冲突,在中国戏剧中也经常出现。被神化的包公形象,是中国最为著名的正义法官的代表。民间关于包公铡其侄包勉的故事,正好体现出在亲情与国法发生冲突时,中国的戏剧家和老百姓所期望和接受的“理想情境”。《铡包勉》一剧,是描写包公对于犯有贪污受贿罪的侄儿包勉,面对其情深义重的嫂嫂吴妙贞的说情,也毫不通融,依法处死包勉的故事。这一戏剧情节虽然正史无考,但是从相关史实与包公所立的《家训》中可以看出包公秉公执法、不顾私情的一面。
三、以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命题方法
看两部戏剧的差异仅从戏剧本身看,包公和吴妙贞的冲突与克雷和安蒂纲的冲突非常相似。两部戏剧都涉及国法与亲情。然而细究起来,两部戏剧凸显了中西方对国法、人情问题思考的巨大差异。根据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代表人物哈特在其代表作《法律的概念》一书中创见性提出的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的划分,戏剧中的人物持法律的内在视角,戏剧的创作者和我们这些阅读者都属于外在视角。持内在视角的人,他们的行动和他们对法律的看法有直接联系,法律往往影响着他们的决策和行动,甚至直接是他们行动的理由。而对于持外在视角的人而言,法律与行动的理由之间并无如此紧密直接的联系。
第一,我们从法律的内在视角分析两部戏剧中人物的行动和其行动的理由。《安蒂纲》中的克雷和安蒂纲根据不同的法律采取了不同的行为。《铡包勉》中的包公和吴妙贞同样也根据不同的规则而产生分歧。包公强调“王法条条,昭然在目,不可违抗”,而吴妙贞则痛斥包公“恩将仇报,忘恩负义,丧尽天良”。然而,西方戏剧中的安蒂纲与克雷最终没有达成妥协,安蒂纲以死亡捍卫她心目中的神法,《铡包勉》中的吴妙贞却最终妥协于王法。实际上,戏剧中的吴妙贞从未质疑王法的正义性,她一开始痛斥包公的理由是包公作为执法者并没有网开一面、高抬贵手、法外留情。在包公辩解之后,吴妙贞内心也“恨儿子包勉,不该贪赃枉法,按律治罪,理所应当”。吴妙贞最后不能接受的是“失去终身靠养”,因此想一死了之。而在包公承诺奉养吴妙贞之后,吴妙贞才终于“深明大义”,原谅了包公。
在这两部戏剧中,行为人对于国法与人情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安蒂纲》中,行为人直指国法与人情不可调和的冲突,用通融人情的神法质疑不通人情的国法,对国王所代表的国法尊严采取轻视、不接受、对抗和不妥协的态度。而《铡包勉》中的行为人都是认同王法的权威性,仅仅是在执法官能否高抬贵手、瞒天过海地轻判罪犯上有分歧。在《铡包勉》中,并没有法律和正义的二元化的区分,法律是一元化,法律就是王法,而王法就是正义。
第二,我们从法律的外在视角来看两部戏剧所反映的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安蒂纲》的创作者和对其广为流传与分析的阅读者,都发现了法律与正义的可分离性,也因此发展出了实证法学派和自然法学派之间长久的辩论:恶法亦法还是恶法非法?
从神法到自然法,西方法律文化中始终保留着对超越于世俗国家规则的自然正义的敬畏。这种自然正义包含了对人性本身的宽容,对人之常情的理解和保护。因此,安蒂纲刚烈地追问:违背人情的法,算不算得上正义的法?而从戏剧情节本身的设计和后人的阅读与传播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这一质疑是“同情”而“赞赏”的。《铡包勉》中的吴妙贞却不同,她并未质疑法律的正义,而是质疑执法者本身的道德缺陷,即恩将仇报。王法对于她来说,虽然是不可违抗和质疑的,但是却是可以“绕过”和“欺骗”的。戏剧的写作者和后来的阅读者,虽然同情吴妙贞的不幸,但更多的是对于包公这个执法者的“一边倒”的赞赏,也就是对该剧中的包公不欺瞒王法、必须秉公执法这一点上的赞同。从法律的外在视角来看,西方的读者更多地保持了对法律本身正义与否的审慎态度,而中国的读者则更多倾向于对于王法本身就是正义这一点的强调。
第三,从戏剧中的案件结果来看,司法者或裁判官的结局非常不同。《安蒂纲》中的克雷不仅仅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他本身就是政权的最高统治者。然而,《安蒂纲》中的这位执政者虽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过错,结局却非常不幸。他为了维护城邦的利益和政权的稳固,做出合乎城邦利益的判决,却最终受到命运的惩罚。安蒂纲死后,他自己的妻儿也随之死去,戏剧作者以这个隐喻剥夺了克雷这个执法者享受人情温暖的权利。戏剧作者在《安蒂纲》中所隐含的回答就是:法律与人情本身就不相容。《铡包勉》中的包公不仅得到了吴妙贞的谅解,也得到了世代人的爱戴,成为中国的“司法之神”。
在包公身上,人们虽然传唱他的秉公断案,传唱他“法不容情”,却通过他对吴妙贞承诺赡养,以及其他包公戏中他对于百姓的同情和爱护,对司法者寄予了一种“执法有情”的愿望。同情和保护弱者的司法官包公成为人们心中正义的象征、法律的代言人。而《安蒂纲》中的王者克雷却是西方法律的代言人,孤独、冷酷而无情。
第四,安蒂纲将亲情产生的权利和义务超越于实在法,将其归于神法的范畴。而吴妙贞对于亲情权利义务的理解,并没有超越王法。《安蒂纲》中的家庭伦理与世俗法律之间二元对立,而《铡包勉》中的家庭伦理却隐藏在世俗法律的控制之下或范围之内。前者强调超越于国家的亲情,而后者则默认从属于国家的家庭。安蒂纲表述的是超越的、永恒的亲情权利和义务,吴妙贞承认的是世俗的、不超越王法的亲情。根据西方对法律的划分,法律分为国家的法、社会的法、自然法。安蒂纲将亲情置于自然法的领域,而吴妙贞的亲情属于社会法中家庭法的部分。因此安蒂纲指出了国家法与外在的自然法的对立,而吴妙贞指出了国家法与内在的家庭法的冲突,两者讨论的是不同的冲突。
第五,对于社会规范的调整,西方法律文化中产生了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的秩序”和哈特的“承认规则”这样的理解。社会规范与国家法律不同,不是人们刻意建构的理性,不是人们行为的理由而是人们行为的结果,或者是人们对已经存在的规则的识别与认可。西方的社会规范也不同于自然法的规则,它不是恒久不变的真理或正义,而是同国家法一样属于世俗的、经验的世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也有与西方类似的区分,例如法家学说偏重于国家法,老庄和墨家学说都谈及自然法,而儒家强调的礼实际上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之上的身份等级制度,是社会规范中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仅以家族伦理为尺度的一种社会规范。因此,中国的礼治秩序强调的是个人对于家族的从属,个人必须与其他人发生联系,必须在家庭关系中寻找自己的坐标。当包公秉公执法的时候,他代表的是一个政府的官员对国家法的职责,参照的是国家法的坐标体系。而吴妙贞则试图用家庭恩义关系来指责包公,说包公忘记了自己的家庭责任和家庭从属关系,实际上是以儒家血缘身份制度和从属关系来责备包公。值得注意的是,吴妙贞并未质疑包公所维护的法律,也就是说在国家法的层面,吴妙贞是认同包公的职责的。因此,在儒家法所调整的社会规范和法家法所调整的国家法发生冲突时,戏剧中的吴妙贞和包公都认同国家法的最终权威性。因此,《铡包勉》中的吴妙贞虽然值得同情,但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因素。《安蒂纲》中的两位主人翁同样是亲属关系,但安蒂纲自始至终都没有控诉克雷本人不顾亲情,她控诉的是克雷的法律违背了神法。在这个意义上,安蒂纲是以另一套规范来控诉国家法的不义,也因此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因素。
四、结论
从以上五点对中西两部戏剧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即与西方法观念相比,中国法的基本精神是否表现在强调家庭伦理上?如果仅从以家庭伦理关系来调整社会规范的“礼”着手,或者仅从中国古代的家国式、君父式治理模式看,中国法的确强调家庭伦理,以血缘关系建立身份等级制度,并且将其他的社会关系容纳于这样一套家庭伦理的调整体系内,例如师生关系,君臣关系,都比拟为家庭内的父子关系。然而,如果将国家法这套参照系统也纳入我们的视野,我们会发现,恰恰是在这两套体系并存的时候,中国将社会法纳入国家法,强调国法的最终权威,而西方则强调社会法与国家法的分离,强调神法或自然法的更高权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法的基本精神,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强调国家法、实证法的唯一和最高的权威。只不过儒家在尊重以君主为代表的国家法的最终权威时,用亲情关系来弱化法律的机械与严苛,在“法不容情”时寄希望于执法者“法外开恩”,弥补由于严格执法而产生的法律不得民心的僵化局面。因此,与西方相比,中国法的特点不在于更强调家庭伦理,而在于特意将家庭伦理放置在政治伦理的调整范畴内,而西方则更强调这两者之间的分离、对立与不可调和的冲突。
另外,对于“为什么要遵守法律”这个问题,两部戏剧也体现了中西法文化的差异。《安蒂纲》中的安蒂纲与克雷都遵守着各自认为正义的规则,安蒂纲面对克雷的惩罚,并未以“违抗法律才是正义”作为借口,而是提出更高的法来强调“遵守法律”的正义。因此安蒂纲和克雷都承认“遵守法律”的道德。只不过双方对于“法律是什么”有不同的认识。对安蒂纲而言,恶法不值得遵守是因为恶法非法,只要她所认可的法律,就应当遵守。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要提出承认规则来阐明法律是什么。他无异于进一步解释了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论题“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应当是制定良善的”的前半段。用哈特的承认规则来看安蒂纲的行为,我们能进一步提出疑问:“人们”对法律的识别与“安蒂纲”对法律的识别是一回事吗?“安蒂纲”所识别和承认的法律才是法律吗?在戏剧中,除了安蒂纲之外,虽然有人同情和理解她的行为,但人们更多的是承认、识别和遵守了克雷的法律。
因此,安蒂纲反抗的实质是在识别和承认法律上产生出的问题,而并非仅仅是不遵守法律的问题。而《铡包勉》中吴妙贞对于国法并不存在“识别”和“承认”的问题,更隐蔽的问题是对于“法律的遵守”的问题。吴妙贞希望包公能够网开一面,因为包公位高权重,“可以”徇私枉法。如此一来,我们看到了吴妙贞的局限:在对国法这一最终权威的识别和承认上,她并不存在质疑;但即便认识到了这一最终“权威”,她仍然希望执法者包公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能够绕过这一权威。也就是说,在吴妙贞这里,法律的权威性不是问题,但“是否遵守法律”在此语境内却成了一个问题。《铡包勉》广为流传、受人歌颂的是包公在巨大的人情压力下仍然能够秉公执法,严格遵守法律。但很可惜的是在其他的包公戏剧中,包公是否“遵守法律”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他能否惩恶扬善获得民心才是根本的问题。
由此可见,“遵守法律”这一行为模式本身在西方的语境下就是正义,只不过存在国家法和自然法的分别。而在中国的语境下,“遵守法律”的结果决定了行为本身是否正义。包公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所称颂的司法之神,在于他的裁判指向了人们所认可的惩恶扬善的结果,而非程序正义。
参考文献:
[1]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18―250.
[2] 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论纲 [J] .江海学刊,2002(3).
[3] 何勤华.中西法律文化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327―328.
[4] 梁治平,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个文化的检讨[J].比较法研究,1987(2).
[5] 公丕祥.全球化与中国法制现代化[J].法学研究,2000(6).
[6] 陈景良.讼师与律师:中西司法传统的差异及其意义——立足中英两国 12―13 世纪的考察[J].中国法学,2001(3).
[7] 陈景良.法与人:中西法文化人格差异的解读[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6).
[8] 王宏治.从中西立法过程比较《唐律》与《民法大全》[J].比较法研究,2002(1).
[9] 夏勇.法治源流:东方与西方[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0] 林端.中西法律文化的对比——韦伯与滋贺秀三的比较[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