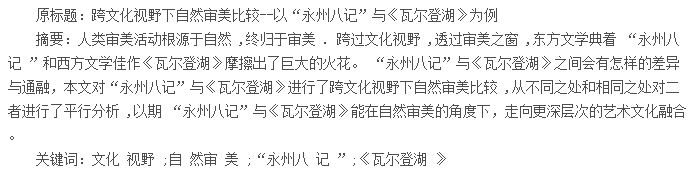
引言:“永州八记”是中国山水文学的典范,《瓦尔登湖》是西方自然文学的代表,中国文学大家柳宗元和西方文学妙手梭罗借“永州八记”和《瓦尔登湖》变现出了个人享誉盛名的审美高位,尽管柳宗元和梭罗身处于不同的国界、生长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受着不同文化气息的熏陶、秉承着不同的精神理念,但是,柳宗元和梭罗对自然审美的追求与向往不约而同。 站在中西方文化的视角下,可以得知,因人而美的永州山水是巧夺天工的, 在纯美中绽放的瓦尔登湖是自然亲切的,“永州八记”和《瓦尔登湖》向世人所展现的终究是生命与自然的相互融合,合二为一是柳宗元和梭罗的共同理想。 一方面,这是一种至高至纯的审美之境,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自然之境。 如此一来,“永州八记”和《瓦尔登湖》
在跨文化视角下,攀登上了自然审美境遇的高峰。
一、 中西方自然审美的概述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中,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议题,也是文学创作中经久不息的主题。 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南齐的陶弘景就道出了人类与自然之间妙不可言的关系,“自然之美是人类恒久的热爱,东方如此,西方亦然”,这句出自于山中白云的古话忽视了东方文化同西方文化的界域,向世人阐述了自然审美之于人类整体的重要性。
大自然是人类劳动生存的场所,也是人类认知审美的对象。 大自然的风光旖旎秀丽,其绚烂多彩的艺术价值连续不断地吸引着古今中外的人们, 人类在大自然中得以延续,大自然也是人类认知的源泉,换言之,大自然是人类审美的良师益友,也是人类审美活动的根源渠头。
自然审美是艺术领域的重要内容,突出表现在文学创作中,是文学创作中经久不息的主题,文学作品将自然之美融入字里行间之中,铸就了一部又一部文学经典。 当自然之美还没有进入审美视野的时候,大自然是纯美的,并非艺术领域中的自然审美。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站在大自然面前,精心地进行了一番审视与考究,文人骚客们将人类的情感投入大自然,为大自然增添了一丝文化气息,为大自然赋予了自人类一项美学意义,使审美文化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得以流传和延续。 中西方的自然审美根出同处,从孕育到发展,再从发展到成熟,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自然审美为中西方艺术文化烙上了刻骨铭心的印记。
在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影响下,自然审美的发展程度略有差距,除此之外,中西方自然审美方式和自然审美理念不尽相同,但在共同的文化视野下,东方自然审美和西方自然审美必然有其相合之处。 在自然审美前进的脚步下,中西方自然审美深受历史文化的影响,在潜移默化中透出了各自的自然审美特征和自然审美旨趣。 跨过文化视野,透过审美之窗,中西方文学的差异和通融显而易见,本文强调了东方文学典着“永州八记”和西方文学佳作《瓦尔登湖》之间摩擦出的巨大火花,在新时代下为人类重新思考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思维视角。
二、 跨文化视野下“永州八记”与《瓦尔登湖》的自然审美比较
(一)“永州八记”的“人美”与《瓦尔登湖》的“纯美”
“永州八记 ” 与 《 瓦尔登湖 》 共同的审美追求是 “ 发现自然”,“彰显自然”,大自然在柳宗元和梭罗的笔下被赋予了诗情画意的美。 在进行细致比较之后,“永州八记”与《瓦尔登湖》在趋同的审美层面上,又富有各自独特的风格,也就是“永州八记”与《瓦尔登湖 》的差异性 . “永州八记 ”与 《瓦尔登湖》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永州八记”的作者柳宗元在主观意识牵引的作用下,展现了因人而美的自然,即“永州八记”的“人美”;与之相反,《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在一生之中不断追求独立于人类主观意识外的自然审美,独立于人类主观意识外的自然是一个纯粹的世界,即《瓦尔登湖》的“纯美”.
柳宗元笔下的“永州八记”,承载着柳宗元的个人怨忧和胸怀情志,柳宗元在出巡永州游历美景中,常常透露出个人的情愫,将人性化的一面融入审美的选择。 在柳宗元眼中,永州山水之美宏大壮阔,有清流侧湍、翠羽成荫之美,更有清冽凄寒、幽怨特异之美。 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直抒胸臆,“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峻为类”一句正表现出了柳宗元个人的挺立不群;在“其石之突怒堰赛,负十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 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面上者,若熊黑之登于山”一句中,柳宗元对怪石意象情有独钟,承载了柳宗元的人生感悟和执着追求[1]. 审美是道德的表象,“永州八记”的字字句句都蕴含了柳宗元生命意义 ,借“人美”的自然,释放自己的灵魂。
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借自然之景和自然之韵呈现了一番大自然的纯然景象。 《瓦尔登湖》中的自然景物紧紧围绕于自然万物的自生、自律和自化,独立于纷扰的人世,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是本色的、纯然的,也是富有生机的。 “那安静的鱼的客厅,那儿充满了一种柔和的光,仿佛是透过了一层磨砂玻璃照进去的似的, 那细沙的底还跟夏天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一个并无波涛而有悠久澄清之感的,像墟拍色一样的黄昏正统治着”,“脱去了夜晚的雾衣,它轻柔的粼波,或它波平如镜的湖面,都渐渐地在这里那里呈现了,这时的雾,像幽灵偷偷地从每一个方向,退隐入森林中……”,在《瓦尔登湖》中随处可见本色的自然,将个人解释和主观判断远远褪去,梭罗如诗人一般,用生命的本质感知自然,呈现了一个“纯美”的自然,掀开了自然柔美的面纱[2].
“人美”和“纯美”的差异性否定了“人事万物的尺度”这一传统观念,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从文化角度凝视了自然,给予大自然关怀,在“人美”和“纯美”寻求到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与和谐。
(二) “永州八记”的“有我”与《瓦尔登湖》的“无我”
在本质上,审美活动是一种情感活动,自然审美意识产生于人类的内心世界,是人类对自然的情感性关注,也是人类对自然的情感性体验。 柳宗元和梭罗分别在“永州八记”和《瓦尔登湖》中巧妙地运用了移情手法,寄情于景,情景交融,以此渲染自然审美。
柳宗元笔下的“永州八记”,体现了作者的明珠暗投,一腔忧愤油然而生。 柳宗元将自己的幽怨哀愁与自然山水相交,与清泉怪石相伴,在奇山丽水中扼腕长叹。 “永州八记”处处有情,字字珠玑,字里行间中流露了柳宗元的愤慨幽怨。 柳宗元放浪于山水之中,寄情于人理之外,“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抒情于“有我”之醉,所以有“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3].
在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作者展现了一番“无我”之境。
“在每一个小山, 平原和每一个洞窟中, 都有霜从地里出来了,像一个四足动物从冬眠中醒了过来一样,在音乐声中寻找着海洋, 或者要迁移到云中另外的地方”,“小溪向春天唱着赞美诗和四部曲”,梭罗将自己化身于明媚春日里的小溪,自由自在,欢娱快乐;“那安静的鱼的客厅,那儿充满了一种柔和的光”一句形象地描绘了水底世界的安静与柔和,满满的都是黄昏下的清澈。 梭罗在一种“无我”的视野下审视自然,欣赏自然,以一颗纯粹的赤子之心聆听自然,此乃“无我之境”的大成所在。
(三) “永州八记”的“万化冥合”与《瓦尔登湖》的“自然之子”
就中国哲学来讲,审美意识下“人”与“物”的交融就是“天人合一”. 在自然审美的凝神观照中,不论是柳宗元的“尚奇”还是梭罗的“喜美”;不论是“幽静凄美”中的“歌咏离骚”,还是“纯美自然”中的“生机灵动”;不论是柳宗元在“人美”下的“有我”,还是梭罗在“纯美”中的“无我”,柳宗元和梭罗在作品中都体现了人类与自然之间永恒的互生互谐。
柳宗元笔下的“永州八记”,蕴藏着作者独特复杂的内心世界,溪水的清澈凛冽,游鱼的无忧无虑,翠木的旖旎披拂,坚石的奇伟怪异, 大自然的景物处处饱含柳宗元的特殊情感。 柳宗元举目而望,山无棱,地无角,仿佛置身于浩瀚无垠的宇宙之中。 “清冷冷状与目谋,滑滑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如此心旷神怡,万物瞩目,可谓是“心凝形式,与万化冥合”. 柳宗元内心苦楚,“心凝形式,与万化冥合”是柳宗元毕生的审美诉求[4].
梭罗笔下的 《瓦尔登湖》, 勾勒出了瓦尔登湖的和谐静谧。 梭罗与大自然亲密无间,以礼相待,将鸟雀视为“邻里”,将青松视为“挚友”,将鹞鹰视为“蓝颜”,梭罗说“步行八英里或十英,专为了践约,我和一株山毛榉,或一株黄杨,或松林中的一个旧相识”,梭罗与自然之间没有间隔,将自然亲切地成为“人类的母亲”、“我们伟大的母亲”,面对琥珀,梭罗说“瓦尔登,是你吗”;面对大地,梭罗说“难道我不该与土地息息相通吗? 我自己不也是一部分绿叶与青菜的泥土吗? ”,梭罗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与大自然的共鸣,被成为自然审美视角下的“自然之子”.
在自然审美的指引下, 柳宗元选择了悲鸿的永州山水,梭罗选择了寂静的瓦尔登湖畔,一种平衡与协调在人类与自然的紧密联结中缓缓溢出, 这也是人类对自然的钟爱于赞美,是诗性智慧上的自然追求。总结:总而言之,生命与自然的相互融合与合二为一是柳宗元和梭罗的共同理想,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襁褓,也是人类心灵净化的殿堂。 本文以“永州八记”与《瓦尔登湖》为例,在跨文化视野下比较了中西方自然审美,以期指引人类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参考文献:
[1] 吕国康。新世纪柳宗元研究的动态与进展[J].运城学院学报 ,2014,01:36-42.
[2] 向天渊。跨文化视野下的新创获 ---评 《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 》[J].外国文学研究,2011,04:145-146.
[3] 代迅。审美态度的恰当性:中国当代美学的自然美[J].社会科学战线 ,2011,04:141-153.
[4] 薛富兴。自然审美批评话语体系之建构[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1:99-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