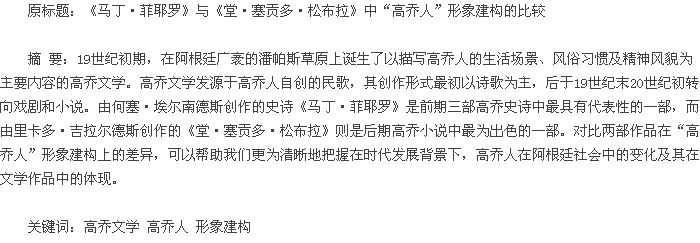
一、高乔人与高乔文学
自西班牙殖民时代起,在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上就生活着这样一群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殖民者与土着印第安人结合而产生的印欧混血种人以及土生白人(西班牙殖民者的后裔),在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以牧牛、马为生,他们被称为“高乔人”.“高乔”一词最合理的词源解释来自于印第安土着语言阿劳加语中的词语“古阿乔”,意思是“没有母亲的”“私生的”“孤儿”.这刚好道出了高乔人身份认同感的缺失。这些“草原的孤儿”终日过着流浪的生活,辽阔的草原赋予了他们放荡不羁、崇尚自由的天性,而半草原半荒漠的艰苦生活环境则锻造了他们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格。高乔人喜爱弹唱(这是他们用以排遣无边寂寞的方式),在劳作之余便在小酒馆中弹起吉他琴,将自己的生活经历编成通俗易懂的民歌演唱给听众听。其中一些出色的弹唱者成为“巴雅多尔”(payador,义为“弹着吉他席地吟唱的民间歌手”),而他们即兴创作的民歌“巴雅达”(payada,义为“即席诗歌、即席吟唱”)则为高乔文学的产生提供了最原始的参照。后来,一些诗人开始模仿巴雅多尔,用通俗的语言创作描写高乔人生活的诗歌,从而使高乔文学完成了从口头到文字、从民歌到诗歌的过渡。由诗人何塞·埃尔南德斯创作的长篇诗歌《马丁·菲耶罗》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它“使高乔叙事诗真正达到史诗的规模并赢得了崇高声誉”[1](P67).高乔诗歌的成功使得作家们看到了将这一文学主题拓宽至其他文学领域的可能性。于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高乔生活为主题的其他文学形式,如散文、小说、戏剧等悄然兴起,并逐步取代了高乔诗歌的地位。其中,由里卡多·吉拉尔德斯创作的《堂·塞贡多·松布拉》便是高乔小说中一部不朽的佳作,而它的发表也标志着高乔文学进入了尾声。
二、《马丁·菲耶罗》中高乔人形象的建构
《马丁·菲耶罗》是阿根廷诗人、政治家何塞·埃尔南德斯于1872年发表的一首长诗,诗中高乔“巴雅多尔”马丁·菲耶罗以自弹自唱的方式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抒发了对当时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和对高乔人悲惨命运的哀叹。诗人用简单质朴的语言,通过马丁之口揭露了冰冷的社会现实,从而引发了下层高乔民众的强烈共鸣。而本诗也因其对“高乔人”这一带有独特民族印记的群体的描绘而成为阿根廷民族传统及民族精神的载体,达到了史诗的高度。1879年,应读者的需求,何塞·埃尔南德斯又发表了一部名为《马丁·菲耶罗归来》的续篇。
细细品读《马丁·菲耶罗》便会发觉,在这部作品中,“高乔人”的形象建构是复杂、多层次的,并且带有一种世俗感。诗人没有对高乔人的性格弱点加以掩饰,相反,他以客观的态度表现出高乔人性格的多面性,用质朴的文笔描绘了高乔人的生活百态。阿根廷作家米格尔·卡内在其写给埃尔南德斯的信中指出,后者写出了“真正的高乔诗句”,并称赞其作品“毫无矫揉造作之感”[2].何塞·埃尔南德斯自己也曾说:“书中特定环境里的人物应当讲他自己的、特定的语言,要有他自己的个性、风趣和天然的缺点。”下面,谨以主人公马丁·菲耶罗及其好友克鲁斯之子皮卡蒂亚两个人物形象为例分析作品中高乔人的形象建构。
(一)马丁·菲耶罗:自然赋予的野性与受到压迫后形成的“野蛮”不难发现,在《马丁·菲耶罗》中,同其他高乔人一样,主人公马丁·菲耶罗身上是带着一种自然赋予的野性的。他放荡不羁、桀骜不驯、争强好胜而又勇敢无畏、崇尚自由,茫茫原野任其驰骋,拓展了他心中那片广阔的天地,也成就了他那不凡的豪气与胆识。正如他自己所高声吟咏的那样:“羊群里我是头羊,牛群里我亦称王,生来便不同凡响,不服气可来较量。/风险当前无所惧,白刃加颈有何愁?艰难困窘般般有,几曾见我锁眉头?/茫茫大地何足道,我志无垠更辽阔。毒蛇岂敢把我伤,骄阳不炙我前额。/自由是我的荣光,生活像飞鸟一样。任何人休想追上,一旦我展翅翱翔。/我未曾享受爱情,但自由给我报偿;苜蓿草权作卧榻,身披着闪烁星辰。”这孤傲的草原之子身上所散发出的原始的野性,如同潘帕斯正午的骄阳,炙热、浓烈而又充满生机。
然而,高乔人固守的那份与世无争的宁静还是被现代“文明”的步伐打破了。他们被卷入时代的洪流,被迫参与到与土着印第安人的作战中。边关艰苦的生活条件、沉重的劳役、残酷的刑罚、长官的腐败昏庸使他们的身心遭受到了巨大的折磨,仿佛是失去了自由、被迫进行劳作的马儿,因而时常愁绪万千,感慨自己命运悲惨、命途多舛。在《马丁·菲耶罗》中,马丁对自己在边关度过的岁月的讲述就是当时高乔人戍边生活的真实写照。
马丁·菲耶罗在一次小酒馆的演唱中被抓而分派边疆。边疆军营生活条件异常艰苦,马丁在承担繁重的劳役的同时受尽了上司的凌辱,不仅时常遭受皮肉之苦,心灵上也受到极大创伤。最终,他实在无法忍受,便毅然选择出逃。在讲述自己的戍边生活经历时,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其内心的酸楚与愤怒。谈到兵士的住所时,他这样描述:“这些个破楼烂堡,老鼠都不屑一顾,耗子洞远比它好。”[4](P21);面对长官的昏庸贪腐,他义愤填膺,却也有苦难言:“让这些坏蛋坯子,被贪心胀破肚肠!……我恰似沙漠雏驼,对他们无可奈何。倒不如暂且装死,也免得惹下大祸。虽然是心中有数,且装作昏聩梦魔。”[5](P41-42)而“哨兵事件”使他彻底认识到,高乔人在这个“文明”社会中的地位甚至还不如那些一无是处、懦弱无能的“外国佬”,这最终使他下定决心一定要逃出这个无底牢笼。经过几年戍边生活,马丁逐渐认清了这个所谓“文明”社会外表下所隐藏的一些丑陋的本质。
与此同时,社会不公和生活艰辛所产生的愤怒和惆怅也在他心底不断堆积,几乎使他崩溃。而当他好不容易逃出樊笼、重获自由时,家产被收、妻离子散的现实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文明”社会的压榨和步步紧逼使他内心积压已久的负面情绪瞬间爆发,如同火山喷发一般,让他热血沸腾,几乎失去了理智。带着一种近乎于绝望的野蛮,他如一头猛兽发出了怒号:“那时候我曾经发誓,比豺狼更狠十分!/我可是像只猛虎,小虎崽已被偷光,不叫他败下阵去,也让他逃亡他乡。”[6](P59)从此,他再不甘心屈服于命运的摆布,决心誓死反抗:“我不负天下之人,但我也至死不屈。谁再想将我坑害,定叫他枉费心机。/尽管都说高乔人,如愚似痴官马魂。每逢苦难压头顶,无人胆敢不屈身。我看为人莫认命,只要心中血尚温。”[7](P59)成了亡命之徒的马丁·菲耶罗变得愈发野蛮冲动、肆意妄为,“这一次非同以往,酒醉后大打一场”[8](P61),并最终因此犯下杀人的罪行,但他却认为这是为保命而进行的合理的自卫,甚至还有点“维护名誉”的色彩:“一见你烧酒沾嘴,就骂你高乔醉鬼;一见你踏进舞厅,就诬你极不正经;只有靠自卫造反,要不然……早晚完蛋!”[9](P74)……最终,他发誓要“用钢刀利器,将道路重新开辟”[10](P72).马丁的悲剧不是一个个案,而是“文明”对所谓“野蛮”进行压制的背景下,高乔人边缘化处境和内心痛苦挣扎的缩影。
(二)玩世不恭、精明狡诈与第一部不尽相同,何塞·埃尔南德斯于1879年出版的续篇《马丁·菲耶罗归来》少了些大起大落的情节,多了些相对平静的、世俗化的描写,从而突出了“高乔人”形象的多面性,同时也使之更为饱满、鲜活。智利着名文学评论家阿图罗·托雷斯·里奥塞科在其着作《拉丁美洲文学简史》中这样写道:“《马丁·菲耶罗》的确有着两个不同的西班牙先例--罗曼采和流浪汉小说……就后者的情况来说,马丁有时候具有某些流氓的品性,可是在另外两个人物:老人比斯卡查和皮卡蒂亚身上,则表现了西班牙‘皮卡罗’(西班牙语,意为流浪汉)的所有的伎俩和哲学。”[11](P149)托雷斯·里奥塞科提到的西班牙文学中的“流浪汉”形象的确在《马丁·菲耶罗归来》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其中,马丁好友克鲁斯之子皮卡蒂亚就是这种流浪汉形象的典型。“皮卡蒂亚”(picardia)在西班牙语中有“狡猾”“玩世不恭”之意,而此名即是对此人性格特点的暗示。皮卡蒂亚年幼丧母,又不知生父为何人,只好独自在草原上四处漂泊流浪。家庭温暖的缺失和社会生活的磨砺使他过早地感受到了世态炎凉,变得玩世不恭而又精明狡诈,活脱脱一副西班牙流浪汉经典形象“小拉萨路”的翻版。作品中有两个情节充分展现了其性格特点。第一个场景发生在皮卡蒂亚被信奉天主教的嬷嬷们收养期间。嬷嬷们教他念祷词,而他却心不在焉,与身旁的姑娘调情,从而念错了祷词,丑态百出,令人忍俊不禁:“那嬷嬷教我学说:‘圣教的那些信条。’我的嘴不听使唤,直急得心似火烧。我看了黑妞一眼:‘圣妞的那些信条。’”[12](P280-281)嬷嬷们训斥他,他十分窝火,便在心底里暗自祈求:“让她们连同祈祷,统统到地狱里面!”[13](P282)……第二个场景是他在逃离嬷嬷们的管教后到小酒馆谋生,与酒馆老板在牌局中串通,通过各种作弊伎俩骗人钱财。其中,对这些骗人伎俩的描写可谓淋漓尽致,将皮卡蒂亚精明狡诈的个性充分展现了出来:“牌故意叫人看见,装得像疏忽一般,对方便孤注一掷,其实早中计受骗。因为只露出假的,真的却藏在后面。玩蒙特更要仔细,这一点切记心间。手指需一齐用力,将纸牌攥紧遮严。找座位要高一点,光线应来自后面……”[14](P286)可以说,皮卡蒂亚代表了高乔人的另一种形象,即深谙生存之道、游走在市井角落的流浪汉形象。这种形象与前文提到的野性与野蛮共同构成了高乔人性格的多面性,也体现了《马丁·菲耶罗中》中高乔人形象建构的复杂性。
三、《堂·塞贡多·松布拉》中高乔人形象的建构
《堂·塞贡多·松布拉》的作者里卡多·吉拉尔德斯1886年出生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因从小生活在父亲的庄园而对当时草原上高乔人的生活和风俗习惯十分熟悉。1926年,他发表了小说《堂·塞贡多·松布拉》,标志着其文学创作达到了巅峰。这部作品因其对高乔人形象的完美化描绘及其所使用的独特的艺术手法而成为阿根廷高乔文学中不可忽视的经典着作,同时这部作品的发表也标志着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高乔文学进入了尾声阶段。
在高乔人形象的建构方面,这部作品与《马丁·菲耶罗》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这部作品中,高乔人的形象不再是一种真实的、复杂的全景式建构,而是被理想化、完美化,被提升为一种脱离了真实的虚幻存在。下面仅以小说主人公堂塞贡多·松布拉为例分析该部作品中高乔人的形象建构。
(一)虚幻的存在首先,正如其名字的含义所指示的那样,吉拉尔德斯创造的堂塞贡多·松布拉这个形象,与其说是一个有血有肉、实实在在的人,倒不如说是一个理想化的完美存在,是一个虚幻的“影子”(西班牙语中sombra意为“影子”“阴影”)。小说开端,在堂塞贡多首次出场时,作者便直接点明了这一点:我仿佛看见了一个幻影,一个影子,一个转瞬即逝的东西;它更像一个思想,而不像一个生物;它是以一种漩涡的力量拉着我,把我吸进河水深处的东西。[15](P9)而在小说的末尾,当堂塞贡多离开“我”,重新消失在茫茫草原深处时,作者重申了这一事实:那渐渐远去的,与其说是一个人,还不如说是一个思想。突然,他消失了,使“我”的思考脱离开了目的物。“松布拉……影子……”,“我”反复地说着。
(二)兼具多种美好品质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堂塞贡多·松布拉具备了几乎所有高乔人所应具备的美好品质:沉稳、镇定、耐心、坚毅、友善、包容等等。他能够出色地完成驯马师的工作,将暴躁的野马驯得服服帖帖,也能够从容应对警察局长的无理挑衅而面不改色;能够忍耐长时间艰苦的赶场工作,风吹日晒雨淋而没有丝毫抱怨,也能够以宽广的胸襟和气度容忍他人有意或无意的冒犯,有时还不忘加上一两句自嘲以调节氛围……同时,他还具备一种普通高乔人不具备的品质:博学多才。他不仅精通赶牲口师傅的学问、驯马师傅的巧计,医术十分高明,而且在寻欢作乐方面也毫不逊色,弹唱、舞蹈、作诗样样精通。而所有这一切,也“仅仅是他广博学识的一个小小的火花”[17](P68)……总之,可以看出,作者就是要将所有美好品质全部移植在堂塞贡多身上,塑造一个完美的理想化存在。
(三)热爱自由同其他高乔人一样,堂塞贡多对自由也有着深深的热爱与崇敬,这使他始终一个人过着孤寂的生活,而决不肯停下流浪的脚步。关于这一点,作者是这样描述的:可是在这一切之外,在这一切之上,堂塞贡多最热爱的还是他自己的自由。他是一个自由自在的独来独往的人;对于他,与人们的长久相处,结果只会引起一种无可避免的厌倦。作为行动,他最喜欢的是不停地行走;作为谈话,他最喜欢的是自言自语。
(四)神秘性除此之外,堂塞贡多·松布拉还有一个十分特别之处,那就是他的神秘性。在叙述者“我”的眼中,堂塞贡多“是一个‘蒙面的人',一个神秘的人,一个说话很少的人,一个在潘帕斯草原上令人疑惑、令人钦佩的人”[19](P14),他知晓许多关于巫师和魔鬼的传说,有时还能够预知未来。
“我”也曾对此产生疑惑:“为什么我的寄父那么肯定堂西斯托的孩子病重?……难道他相信巫术?他讲的那些故事,是一本正经地讲的吗?”[20](P120)……然而,“我”知道这些疑惑终究是找不到答案的:我的头脑再发热也没有用。我已经明白,堂塞贡多不会答复我[21](P120).或许,正是这些神秘的元素使得堂·塞贡多原本就虚幻的形象更加飘忽;而也正是这些元素的添加使得《堂·塞贡多·松布拉》这部作品脱离了纯粹的现实主义的范畴,蒙上了一层奇幻而又迷人的色彩。
四、产生差异的原因
从客观环境与主观因素两方面来考虑,《马丁·菲耶罗》与《堂·塞贡多·松布拉》中高乔人形象建构的差异与社会背景的变化及作者自身经历的不同有着密切的联系。
《马丁·菲耶罗》创作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罗萨斯的独裁统治刚刚宣告终结,阿根廷正站在国家统一后实现发展与进步的新的历史节点上。米特雷政府及萨米恩托政府均代表了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央集权派的利益,他们提倡效仿欧美,通过工业化、鼓励从欧洲移民、引进先进教育制度等措施尽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在对待高乔人这一土着群体的问题上,中央政府却秉持一种漠视甚至歧视的态度。中央政府将高乔人当作阿根廷通向“文明”的障碍,萨米恩托总统本人就曾利用流浪法等措施镇压高乔人。这导致了当时高乔人在社会中被极度地边缘化,社会地位十分低下。
《马丁·菲耶罗》的作者埃尔南德斯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政治家。他对高乔人的处境抱有同情和怜悯,并主张维护其权利,提高其社会地位。埃尔南德斯曾明确指出:“高乔人应当成为公民,而不是贱民;应当既承担义务又享受权利。他们的文化应当使其地位得到改善。”[22](P56)在这部作品中,埃尔南德斯用冷峻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对高乔人的生活境遇的改变及心理活动进行了刻画,描绘了高乔人独特的个性以及他们逐渐被“文明”社会逼入死角的过程中所进行的绝望的挣扎与反抗。可以说,《马丁·菲耶罗》这部调子略显沉重、带有些许野蛮色彩的作品是当时高乔人社会处境和生活境遇的真实写照,反映了作者对他们的同情与怜悯,同时也是作者为他们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而向当时社会发出的呐喊、提出的抗议。
高乔人的足迹最终还是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阿根廷畜牧业的发展,一道道带刺的铁丝篱笆将原本宽广的潘帕斯草原分割为片片牧场,而失去了自由驰骋天地的高乔人也从此走下马背,走进牧场成为了牧业工人。原来那个飘扬着马蹄声和巴雅多尔的琴声与歌声的草原高乔时代从此结束了。
与现实中高乔时代结束相反,20世纪初,随着民族主义在拉丁美洲的萌芽,本已消逝了的高乔英雄主义精神作为阿根廷民族精神内涵的核心又一次在阿根廷人心中复活,“高乔人从此一跃成为神圣的民族原型”[23](P57).而童年在庄园与高乔人共度的那段岁月在里卡多·吉拉尔德斯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心底里的那份高乔情节随着岁月流逝非但没有褪色,反倒愈发浓厚,像一杯陈年老酒,散发着诱人的醇香。因此,他希望用自己的文字留住高乔人,留住他们的桀骜不驯、他们的勇猛坚毅和他们对自由的向往,让后人在对文本的阅读中慢慢地体会、感受,即使那只是一个经过了精心修饰的、不那么真实的“影子一般的形象”.可以说,《堂·塞贡多·松布拉》是里卡多·吉拉尔德斯献给逝去的高乔英雄主义的一首挽歌。小说开头的这段献辞便是作者最由衷的心声:“献给我故乡的父老们。/献给我不认识,却是本书灵魂的人们。/献给高乔:我心中神圣地保藏着的高乔,犹如圣体匣保藏着的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