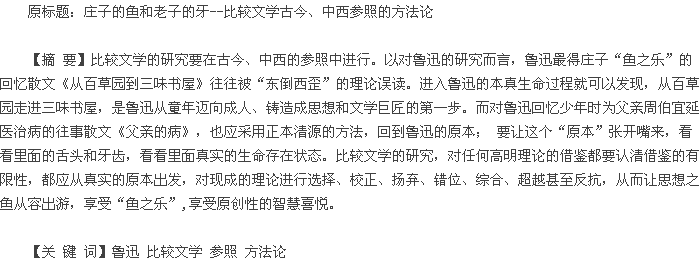
一、引子: 鱼之乐
在先秦诸子中,写鱼写得最多、最好,也最有灵性的,是庄子。这些鱼可以变化。“北溟有鱼,其名曰鲲,化而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鲲本来是小鱼,它竟然能变化成背宽几千里的大鹏,“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些鱼还会说话。涸辙之鱼乞求庄子给它斗升之水来救命,不然就要“索我于枯鱼之肆”.当然写得最有灵性的是庄子和惠施濠梁观鱼。庄子看到白色的小鲦鱼从容出游,感叹“鱼之乐”,惠施说: “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之乐'?”庄子说: “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鱼之乐‘?”在庄子看来,人是与万物一体、与万物同化、与万物同游的,因此能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
濠梁观鱼的哲学,渗润着禅宗。六祖慧能《坛经》说: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五灯会元》记录道明禅师的话,就变成“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思想资源就是庄子形容的那条有知性和灵性的鱼。这就沿用下来。南宋岳飞的孙子岳珂《桯史》就说: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甚至连通俗小说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中也讲: “对人说梦,说听皆痴;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鲁迅在《热风·题记》、《故事新编·序言》中,都使用了“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鲁迅不喜欢《庄子·齐物论》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思想,主张爱憎分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 Hercules) 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 Antaeus) 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但是现代作家中,鲁迅是采用庄子语言最多的一人。这可能是由于庄子语言锦心绣口,注入了生命的感觉,以之审视生命,别具神采。鲁迅提供了古今文学的错位接受的范式。
有错位,才有创造。如果没有错位,就是拾人牙慧,就是邯郸学步,如鲁迅所感慨的: “中国的古书里有一个比喻,说: 邯郸的步法是天下闻名的,有人去学,竟没有学好,但又已经忘却了自己原先的步法,于是只好爬回去了。”邯郸学步的故事与濠梁观鱼一样,都是《庄子·秋水篇》中的寓言。
对于外来理论的借鉴,不管它如何新鲜、如何前沿、如何启迪人智,同样也应采取错位接受、有限接受、选择性和超越性的接受,甚至逆向性的接受。
西方人创造理论,是立足于他们所拥有的传统脉络、当时思潮和现实需要。他们没有到过中国凤阳的濠梁来观赏濠水养大的鱼: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不要把自己的“第一感觉”埋没了。笔者在牛津、剑桥访问的时候,曾经讲了鲁迅喜欢阿 Q的 Q 字,大写起来是脑袋后面拖着一根辫子,借以解剖国民性别具深意。一位世界知名的文学理论家听了后感到非常惊讶,闻所未闻。其实这在鲁迅研究界,只是常识而已。西方理论家没有认真地关注中国河里的鱼,那么我们又怎能不加选择、不加超越地用他们的理论来谈论自己的“鱼之乐”呢?中国学者应该负起责任,给自身的文化和文学经典一个根基牢靠、又能与当代世界进行深度对话的原创性说法。
二、走进鲁迅的百草园
笔者想谈一谈鲁迅最得“鱼之乐”的回忆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它以明快俊朗的文字,如诗如画又舒卷自如地展示了一个妙趣横生的童心世界,浑如天籁般浸润人心,脍炙人口。尽管世变风移,它却魅力永驻。它屡次与《故乡》等作品一样,成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教材中不可缺席的篇目,发挥着陶冶情操的渗润功能。令人感慨的是,对于其中充满童趣的“鱼之乐”,考察者往往与一片童心相对,极力追求高深。在借鉴外来思潮时的姿态,难免出现某种“东倒西歪”: “东倒”就是倒向苏俄理论,说百草园是儿童的乐园,三味书屋是封建教育制度的牢笼; “西歪”就是援用西方大传统、小传统的理论,认为百草园属于传奇志怪的自由空间的小传统,三味书屋属于四书五经的禁锢人性的大传统。总之采取二元对立的思维,认为百草园中的童年鲁迅是如何“幸福”,进了封建教育的学塾后,每日面对晦涩的“之乎者也”,是如何昏暗、枯燥、森严、无味,如何“痛苦”; 少年鲁迅实在值得同情,他无可奈何地承受着“失乐园”的悲哀了。这类阐释是不是已经回到鲁迅生命过程的原本了呢? 这是值得商量的。百草园是鲁迅故家的后园,一个普通的菜园。
鲁迅说: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 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如此乐园,当然值得处在离乡飘泊的过客生涯中的鲁迅对它怀着深深的眷恋。鲁迅推重“野草”,姑以百草名其童年乐园,野趣大于雅趣,异于文人雅士给自家花园所起的雅号。以百草之园来容纳妙趣橫生的童心世界,对于展示自然人性的天真烂漫,是再合适不过了。三味书屋在鲁迅故家迤东一箭之路,是寿怀鉴设帐授徒的地方。鲁迅于1892 年 11 岁时进入三味书屋,在那里求学 6 年。
所谓“三味”,据寿镜吾之子寿洙邻讲: “若三味取义,幼时父兄传说,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诸子百家味如醯醢。”周作人也证实,“三味”的意思是“经如米饭,史如肴馔,子如调味之料”.那么这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四书五经”范围,“三味”的“三”,意味着多,经、史与诸子百家并列,不止于四书五经。“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对课又超出了经、史、诸子的范围,指向诗词训练。
百草园的泥墙蔓草中,掩藏着鲁迅孩童岁月的好奇心和痴心的秘密。回忆起来,心头都会窃窃偷笑,笑得心尖儿酸酸的: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 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 云雀) 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这里用了“不必说……也不必说……”的句式,似乎要省略过去,但是把云雀称为“叫天先生”,乃是将童趣由大地放飞到苍空的点睛之笔,岂能忽略? 但是这仅仅是对百草园的开始,如果停留于此,那么精神家园还是肤浅的。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入到“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那里更有“无限趣味”: 可以听到自然的声音,看到自然的蠕动,尝到自然的滋味。不是因为肚子饿,而是为了精神的饥渴: “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 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象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象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象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这简直就是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了。
为什么要写美女蛇的故事? 写美女蛇,就将百草园与长妈妈的世俗世界、怪异神秘的超现实世界加以综合,从而使百草园附加了叙述的复调和多元的意蕴。许多散文写得缺乏深度,就是由于少了这种复调和张力。百草园是一个有深度的世界,令人还存在着对自然的尚未认知而产生的畏惧感和神秘感: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因畏惧和神秘而出现的紧张,是生命力机制的本能反应。这种紧张反应,因“美女蛇”的故事而升级: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 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 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 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 高 枕 而 卧。他 虽 然 照 样 办,却 总 是 睡 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 门外象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百草园没有溪流和鱼,却多了杂草和美女蛇;表层上没有庄子式的“鱼之乐”,但深层处却增加了鲁迅式的阴郁和忧患,接上了中国民俗心理的地气。这里既有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鸣蝉、黄蜂、叫天子的明朗格调,又有泥墙根一带油蛉、蟋蟀、蜈蚣、斑蝥、何首乌、木莲、覆盆子的丰富生命和无穷趣味,再加上美女蛇的充满迷惑和恐怖的神秘莫测,这样的精神乐园,就不是单调、肤浅的游乐园,而是具有深度的生命投入的意义生成之园。
《圣经》记载,伊甸园中的人类始祖,受蛇的诱惑偷食知善恶树的禁果,导致失乐园。鲁迅写美女蛇的时候,是否受过伊甸园中据说是撒旦( Satan) 化身的毒蛇故事的触动,无从考证。然而,自从少年鲁迅担心美女蛇在墙头窥视,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 “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之后,他就在精神发展阶段的意义上,开始走向失乐园了。只是冬天下雪,支起竹筛捉鸟,才有点乐趣。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他捉鸟时的性子跟“张飞鸟”所差无几,就是性子急,所获有限,多少有些意兴阑珊了。他被送去上学,“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 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向草和虫告别,牵引着恋恋不舍的情思。
三、如何阐释三味书屋
随之出现三味书屋,研究者对它的感受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似乎连鲁迅也留下一个“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评论者看见“最严厉”三个字,往往神经过敏,或者拿出“东倒西歪”的大理论来,说鲁迅的童年有两个世界,一个其乐无穷,一个阴森可怕,简直是四书五经的正统文化排挤掉传奇怪异的奇幻空间。实际上,进入鲁迅的本真生命过程就可以发现,只有百草园而没有三味书屋的鲁迅,是难以想象的,根本无法铸造成思想和文学巨匠的鲁迅。从百草园走进三味书屋,迅哥儿长大了,从他的童年迈出了走向成人的第一步。进入三味书屋的少年鲁迅,自然存在着一个性情趣味的精神转型的过程,这个坎子必须跨过去。
他不能不知调适地止步在百草园阶段,人的生命在于动,如《老子》四十章所说“反者道之动”.比如他初入三味书屋,还存在着这样的精神关注: “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 ……‘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不知道! ‘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这种趣味和他在百草园中欣赏“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14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是相似的。当然如果更开明一点,可以对其好奇心进行和风细雨的引导。但这位要求少年专心读书的老夫子,摆出“师道尊严”的谱,未免有些生硬,在晚清时期这并不奇怪。从学生请教后的心理反应来看,他对老师还是尊敬的,并不感到这有多么昏暗、森严。
三味书屋的书房,实际上是如此书房: “中间挂着一块扁道: 三味书屋; 扁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孔子是缺席受拜的,意味着有点改良气息。因而,在三味书屋还存在着某些“百草园趣味”的缝隙,或有限空间。这就是“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那里去了?‘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 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矩,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 ‘”应该说,在晚清时期如此处理学生上课时走神寻乐,还算通达人情。恐怕今日的老师也不能放任课堂秩序不管。
在先生严厉督责下的读书情形,也不是正襟危坐,而似乎是多声部的合唱,甚至荒腔走调: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读书只是“一阵”,难说过分枯燥。有人念《论语》,有人念《幼学琼林》,有人念《周易》而念错了字,有人念《尚书·禹贡》而念错了行,各人的程度和进度是很不划一的。至于老师呢,“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在学生们念得人声鼎沸时,他并非板着脸孔、踱着方步、检查申斥,而是加入这荒腔走调的合唱: “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 ~ ~ ; 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 ~ ……‘”先生念的是清朝武进人刘翰的《李克用置酒涶同赋》,极力渲染唐末沙陀部枭将李克用在宴席上狂舞玉如意、斟满金制的扁形大口酒杯、意气淋漓、忘乎所以的张狂情景,念时却把“玉如意”念作“铁如意”,“倾倒淋漓”念作“颠倒淋漓”,又拉开长调的颤音“呢、噫、嗬”的,摇头晃脑地陶醉于其中。多么可爱的老人,多么难忘的学塾场面,这是旧时学塾中难得一见的奇观。任谁在少年时看见课堂是这么一幕,都会津津乐道。鲁迅回忆起来,眷恋之情溢于言表。如此景象,又怎么能说是枯燥呢?
对于老师的陶醉态,学生们当作看戏取乐: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日后说“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是对老师的文学趣味平平的调侃,却是带着温情的微笑的调侃。
而且乘着先生读书入神,各自又耍弄起小把戏: “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象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 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断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鲁迅就像他影绘小说绣像一样,活灵活现地影绘出一个老夫子的带点名士派的天真放达的灵魂,可爱极了。他在回忆“三味书屋”这位博学、严厉、善良的老人中,寻到了几分敬意,几分开心,几分笑影,充满着深深的眷念之情。全文叙写了自己从可以说是“无限乐趣”的“乐园”到全城“称为最严厉的书塾”的人生过程和心灵历程。它给人的启示是: 人要成为“成人”,是不能只有百草园的,他也应该有自己的三味书屋。
鲁迅与庄子相似,都是在离乡飘泊的途中写心灵的文章。庄子三十多岁漫游于濮水、濠水一带,《庄子·刻意篇》说: “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他作为江海之士,垂钓于濮水,观鱼于濠梁,是对于庄氏家族经安徽西北部、河南东南部一带,从楚国逃亡到宋国的老路线进行频频反顾; 对于他自己而言,则是避开“苦心劳形以危其真”的处境,超越中国之君子或中国之民“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局促的精神状态,自己“洒心去欲,游于无人之野”,追求着“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鲁迅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则是 1926 年 9 月初到厦门大学,远离“乌烟瘴气”的古都文化界的笔墨官司,又有丰厚报酬; 海滨气候暖和宜人,曾作函致H. M 兄( 害马,即许广平) ,说“海滨很有些贝壳,捡了几回”.《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是他从记忆中捡回的漂漂亮亮的贝壳。这也是鲁迅的《忆江南》。
白居易《忆江南》词云: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白氏所忆,是他的宦游地; 鲁迅所忆,是他少年生命中早已逝去却无限眷恋的乐园。无论百草园还是三味书屋,都值得他眷恋,研究者不应将其精神家园割裂或碎片化。庄子说: “忘足,履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鞋子合适就忘记脚,腰带合适就忘记腰。
我们不必将充满童心的作品,硬要削足就履,或者束腰瘦身以赶时髦。创造性的理论,应该是从深入发掘事物存在的本真及其相互关系得来的。
四、第二引子: 舌头和牙齿
庄子是上承老子学派的,但他追求逍遥、齐物、道无所不在,就与老子存在着根本性的错位。《老子》八十一章五千言,总共两次写到鱼。三十六章说: “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示人。”这条鱼还在水中,因此庄子引用过这句话。六十章也讲到鱼,但那条小鱼已经在锅里了: “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关心治国,因而他西汉初期与黄帝学说捆绑在一起,成为“君人南面之术”,庄子反被边缘化了。庄子是到魏晋时期才进入时代意识的中心。
闻一多说: “一到魏、晋之间,庄子的声势忽然浩大起来……像魔术似的,庄子忽然占据了那全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他们说: ’三日不读老庄,则舌本间强。‘尤其是《庄子》,竟是清谈家的灵感的泉源。从此以后,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闻一多所引的“他们说”,来自《世说新语·文学篇》,原话只讲到老子: “殷仲堪云: ’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大概闻一多也是对之进行错位借鉴了,但他所描述的魏晋思潮,是绘声绘色的,颇有感染力。
《说苑·敬慎篇》讲了一个老子的故事,讲的是老子的老师常枞病得很重,老子去问候老师,说:
“先生病的不轻啊,就没有’遗教‘可以点拨弟子吗?”老师说: “你即便不问,我也有话告诉你。”他张开嘴让老子看: “我的舌头还在吗?”老子说: “是的,还在。”“我的牙齿还在吗?”老子说: “已经掉光了。”老师就问他: “你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吗?”老子说: “舌头保存得好好的,岂不是因为它柔软么? 牙齿掉光了,岂不是因为它刚硬么?”常枞老师说: “嘿嘿,是了。天下之事已尽在其中了,我没有更多的话告诉你啦。”受此启发而发明的“柔胜刚,弱胜强”
的学理,成了《老子》最有特色的思想之一。但《老子》是将这个学理和水联系起来的: “天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莫之能先。其无以易之。故弱胜强,柔胜刚,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正言若反。”
老子看到水,首先想到的不是庄子的鱼,而是道,如《老子》八章所说: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又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
以舌头、牙齿论道的故事,《说苑·敬慎篇》接着又记载叔向与韩平子的对话。叔向是晋国上卿,与子产、晏婴同时代,年岁长于老子、孔子。他回答韩平子关于“刚与柔孰坚”的问题,说: “臣年八十矣,齿再堕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 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又曰: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观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刚强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毁而必复,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坚于刚也。”
叔向引述老子的话,见于今本《老子》四十三章、七十六章。这是文献记载上老子著述流传出来的最早的竹简。笔者对之进行历史编年学定位后发现:
它传到叔向手中,早于孔子适周向老子问礼三年;老子写出后也须二三年才能传到叔向的手中; 如果老子在孔子问礼三年后才离开洛阳出关,那么老子在洛阳写道德之书用了将近十年。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私家著作,并非出关时的急就章,而是“十年磨一剑”的呕心沥血之作。《老子》书的故乡,是洛阳。
这样,我们就可以呼应着当时东周首都成周,就文本而对老子的生命形态进行分析了。
从叔向将老聃言与“齿再堕而舌尚存”并列而言来看,常枞病重时启发老子的话,似乎老子后来还说过。有意思的是,鲁迅的历史速写《出关》也将这句话安在老子的嘴上: “老子又笑了起来,向庚桑楚张开嘴: ’你看: 我牙齿还有吗?‘他问。’没有了。‘庚桑楚回答说。’舌头还在吗?‘’在的。‘’懂了没有?‘’先生的意思是说: 硬的早掉,软的却在吗?‘”鲁迅自称“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因此对牙齿相当关心。1930 年五十岁因“牙齿肿痛,全行拔去,易以义齿”( 许寿裳《鲁迅先生年谱》) .鲁迅的小说《风波》描写九斤老太已经七十九岁了,常说她16年青时,“天气没有现在这般热,豆子也没有现在这般硬”,可见她的牙齿不顶事了; 但舌头还好,一股劲地念叨着: “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可惜七十九岁的九斤老太不是哲学家,体悟不出“舌柔齿刚,柔弱胜刚强”的大道理,她只是懵懵懂懂地感觉到中国的命运。按照鲁迅写《风波》的 1920 年往上推,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实在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她是一个混沌的悲观主义者。
五、父亲的病与名医的药引
既然常枞、老聃是从自己的舌头和牙齿上反省得到“柔弱胜刚强”的学理,那么真正独到的理论,就不能简单地依赖外在的直线移植; 而应该在借鉴的同时,加深对自身文化和生命的内省,张开自己的嘴,体验自己的舌头和牙齿,这样得到的理论才可能连着我们的神经和血肉。否则就是“牙齿肿痛,全行拔去,易以义齿”,属于与自己神经、血肉脱离关系,外在地安上的“理论义齿”了。好看是好看,但咀嚼起来,少了一点滋味。既然鲁迅说: “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听说牙齿的性质的好坏,也有遗传的,那么,这就是我的父亲赏给我的一份遗产,因为他牙齿也很坏。于是或蛀,或破,……终于牙龈上出血了,无法收拾。”那么,不妨考察一下鲁迅回忆少年时为父亲周伯宜延医治病的往事散文《父亲的病》。
读一篇文学作品,首先想到的是对之进行细读和内省性的生命分析呢,还是一看到题目上的“父亲”二字,就急急忙忙地寻找“理论义齿”,联想到“父与子”、“大传统与小传统”一类外来的理论框架; 或者读下去之后,用弗洛伊德性心理分析之类的理论对之进行硬套和曲解? 比较文学要赢得声誉,就要做得深入,要使专家看了也觉得你是内行,而且使专门的内行感到开眼界,有启发。不要使外行看了似内行,内行看了实外行。比如说,有人挑剔鲁迅回忆“父亲”、“母亲”除了这篇《父亲的病》之外,其余作品多是只言片语,从表象上看,也是极其单薄的。既质疑什么因子使鲁迅这样的“人间至爱者”忽略了“人性”的基本元素“父爱”和“母爱”;又生拉硬扯地把藤野先生、长妈妈说成是鲁迅对“父亲”、“母亲”的“文化想象”.其实,鲁迅的母亲鲁瑞( 1858 -1943) ,是一个性格坚韧刚强的杰出母亲。中年丧夫后,她坚毅应对家庭破落、生活贫困的挑战,艰难持家,支持三个儿子鲁迅、周作人、周建人成为举世瞩目的大才。鲁迅十八岁离乡到南京求学,“我的母亲沒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自便; 然而伊哭了……”( 《吶喊·自序》) 她后来随儿子在北平长住,性格乐观、开朗,母慈子敬,相处怡怡; 年过古稀,还向青年人学织毛衣,反复地拆拆织织,终至连复杂的花纹也能织出来。鲁迅还调皮地说: “我的母亲如果年轻二三十岁,也许要成为女英雄呢! ……”由于她高寿,死在鲁迅之后,鲁迅不及写专门的回忆文章。但是鲁迅连自己的笔名都从母亲鲁瑞的姓,又怎么可以轻言鲁迅忽略了人性的基本元素“母爱”呢? 这样的比较文学,能够赢得学界的尊重吗?
正本清源的方法,还是要回到鲁迅的原本,让这个“原本”张开嘴来,看看里面的舌头和牙齿,看看里面真实的生命存在状态。《父亲的病》一文的原本,在于它对自己亲历的中国乡镇民间医疗保障的生存状态,作出了刻骨铭心的批判和反思。从溢于言表的悲愤中,足以证明鲁迅对父亲之爱是何等深切。鲁迅嘲讽《二十四孝图》中某些愚与妄、甚尔有些残酷的“孝行”,自己却以幼小之躯,不避寒暑,承担着为重病的父亲延医求药的责任。鲁迅父亲周伯宜( 1861 - 1896) ,考取会稽县学生员后,屡应乡试未中。因鲁迅祖父周介孚科场案发,家道中落,酗酒发病; 1893 年冬至 1895 年秋冬,病势日加严重,直至 1896 年 10 月 12 日( 农历九月六日) 去世,终年三十七岁。请来治病的医生姚芝仙据说做过太医,给慈禧太后治过病,绍兴人称之“姚半仙”,出诊架子甚大。他推荐的医生何廉臣 ( 1860 -1929) ,曾任绍兴医学会长,清季创办《绍兴医学报》,著有《总纂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等书,校订刊刻古医书 110 种,名曰《绍兴医药丛书》,在保存中医血脉上竭尽心力。但一个人不能以其终生成绩掩饰日常行医上的敛财、敷衍、故弄玄虚的劣迹。少年鲁迅与之打了两年交道,从家庭变故的刻骨铭心之痛中,对之愤、讽有加; 并将何廉臣的名字,按谐音方式颠倒为“陈莲河”,如此可得晚期谴责小说以文字学游戏隐喻现实人物名字的妙处,避免了一些节外生枝的名誉权纠纷。
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为病重的父亲延医寻药、终至不治,是少年鲁迅“三味书屋”时期在社会大课堂的见习。他的精神经历了由希望跌入绝望的一遍又一遍的搓揉和震荡。这场人生磨难深刻地影响了鲁迅早期思想曲线。这段思想曲线上的两个路标: 一是父亲的死,导致两年后到南京学工科的鲁迅留学日本时弃工科而学医,以期“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 二是后来在仙台医科专门学校学医时受“幻灯片事件”的刺激,于1906 年后鲁迅弃医从文。
行文开头有引子: “大约十多年前罢,S 城中曾经流传过一个名医的故事”,他一味地敛财、拿架子、故弄玄虚,把活人医死,又借死人索取厚金,在一种制造悲剧的喜剧行为中,所谓医德和医艺成了笑谈。这种写法,有如鲁迅谈论话本小说“起首先说一个冒头,或用诗词,或仍用故事,名叫’得胜头回‘---’头 回‘是 前 回 之 意; ’得 胜‘是 吉 利语。---以后才入本文”( 《中国小说史略》第四讲) .这种“得胜头回”引导着全篇,隐喻着全篇。
全篇用讽刺的笔调写了庸医误人。鲁迅曾经和这名医周旋经年,诊金昂贵且不论,“药引”就相当难得: 生姜两片; 竹叶十片去尖,是不用的; 起码是芦根,须到河边去掘; 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却使得父亲的水肿逐日利害,将要不能起床。鲁迅对其“医者,意也”的理论极尽嘲讽之能事,他看到病人病入膏肓,便极其诚恳地说:
“我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这里还有一位陈莲河先生,本领比我高。我荐他来看一看,我可以写一封信。可是,病是不要紧的,不过经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一到危急时候,便荐生手自代,使自己完全脱了干系。
下一个打交道的名医是陈莲河,他的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 “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又有“败鼓皮丸”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清朝的刚毅因为憎恨“洋鬼子”,预备打他们,练了些兵称作“虎神营”,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也就是这道理。事后回忆,鲁迅难免对这类“名医”行医的做派和方剂毫不客气,嘲讽其实质在于巫医不分,故弄玄虚,作贱人命以索取钱财。
《呐喊·自序》对此还耿耿于怀: “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这种“骗子说”曾引起后人议论纷纷,甚至义愤填膺,认为“鲁迅反对中医”; 但人们从未从中反思,其时流行于乡镇间的中医理论和论证方式,是否需要作出根本性的改革或改进? 这种理论和论证方式,如何面对现代科学知识的挑战? 若有深刻的反思意识就可以省悟到,鲁迅的心理行为超前地蕴含着一个重大的命题,即中医现代化的命题。
但其时的名医陈莲河心中并无这个命题的踪影,依然在说: “我有一种丹,点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见效。因为舌乃心之灵苗……价钱也并不贵,只要两块钱一盒……”最后就是推卸责任了: “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
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不能要求一个名医包治百病,医术也有对沉痾痼疾束手无策之时。问题在于要给人一个合理的应对和令人服气的说明,不能只盯住钱串子,又把责任推给鬼神; 两年的时间不算短,名医架子不能给人信赖感,反而一依赖,连架子也坍塌了。因而鲁迅只好感慨: “S 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并且谁也还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因此无论什么,都只能由轩辕岐伯的嫡派门徒包办。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而且觉得’舌乃心之灵苗‘.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最后这句“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是发聋振聩的,它生发出对中国人“宿命”的沉重思考。中国社会的生存环境使如此“名医”成为以“巫医不分”的鬼话饶舌的“舌头”,而百姓却如“牙齿”一个个掉落了,可不令人愤慨也乎!
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对中医蕴涵着的伟大经验,鲁迅后来是肯定的: “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我们一向喜欢恭维古圣人,以为药物是由一个神农皇帝独自尝出来的,他曾经一天遇到过七十二毒,但都有解法,没有毒死。这种传说,现在不能主宰人心了。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 医药也如此。这么一想,这事情可就大起来了: 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证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纪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而且这书中的所记,又不独是中国的,还有阿剌伯人的经验,有印度人的经验,则先前所用的牺牲之大,更可想而知了。”( 《南腔北调集·经验》) 有如此伟大的经验作支撑,就更应该支撑起一座可被现代世界认同的理论和方法的雄伟大厦,而不应斤斤计较别人针对具体情境说话的轻重。谁的舌头、牙齿,谁就应该自我珍惜,才不至于说话漏风,吃饭乏味。
六、“枯鱼之肆”中找来的理论需要重新激活
令鲁迅刻骨铭心的,还有父亲临终的一幕。衍太太这个精通礼节的妇人,说应该给父亲换衣服;将纸锭和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还一再催促: “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 ”于是一片叫声,叫得父亲已经平静的脸忽然紧张,微微睁眼,仿佛有些苦痛,一直叫到他咽了气。“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 ’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 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到写这篇回忆散文时,作者耳中还鸣响着在衍太太催促下呼叫“父亲! ! ”的声音,觉得这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人在感情悬崖上所受到的刺激,可能烙下难以除去的疤痕。鲁迅指认,这疤痕是作为世俗礼节之象征的衍太太烙下的。他记下这如陨石袭来的变故和灾难,也就留下了鲁迅心地里至为柔软的人性人情。这里开始积蓄了鲁迅对世俗礼仪憎恶和复仇的某些因子,“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然而有博士文章却要从“枯鱼之肆”中寻找理论,拿着没有经过创新激活的弗洛伊德学说解释《朝花夕拾》中包括《琐记》在内的衍太太,指证她在少年鲁迅潜意识中,兼具“母亲”和“恋人”的双重角色。理由是鲁迅还很小时,偶然走进她家去,她正在和她的男人看“春宫图”,将书塞在他的眼前,但见画着房屋,有两个人光着身子仿佛在打架。正迟疑间,他们便大笑起来了。父亲故去之后,鲁迅也还常到她家里去,不过已不是和孩子们玩耍了,却是和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谈闲天。但是,鲁迅其时只有十六岁,比衍太太的儿子还小三四岁; 而且鲁迅不仅把衍太太看作世俗礼节的代表,还把她描绘成表面充好人、背后散布流言的角色。流言是鲁迅深恶痛绝的,岂能让兼具“母亲”和“恋人”的双重角色承担这种令人嗤之以鼻的罪衍?
解除“理论遮蔽”就不难发现,父亲的病和死,是少年鲁迅经历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在思想和感觉上第一次遭遇偌大的社会,因而他感觉到的痛和恨、希望和绝望,潜在地植入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化观。这里的“药”,令人想起小说《药》中的人血馒头,以馒头蘸着烈士鲜血,当作治疗痨病孩子的药引。“药引”已经成了鲁迅批判社会愚昧和麻木的心理情结。由此,鲁迅由父亲的病拓展为考察中国的病,以致形成了“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美学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他第一次遭遇社会时,就隐隐地积蓄着它的指向和定势。指向和定势的延伸,就多级推进地出现了弃工学医、弃医从文的人生坎子。在一定意义上说,父亲的病所引发的精神反应,经过不断发酵,成了他后来文学开拓的潜在的原动力之一。
鲁迅撬开黑暗的社会口腔,看清它的舌头和牙齿,得到的并非“柔弱胜刚强”的学理,而是从“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发出的呐喊。中国现实拥有中国自身的文化血脉、文明形态和当下生命。中国现实社会的“务实大文本”,与古代的或外国的理论“务虚泛文本”之间存在着不应抹煞的距离。距离所在,就是现代性思想原创的必要和可能的空间之所在。这就导致比较文学研究对任何高明的理论的借鉴都要认清借鉴的有限性,认清外来理论的所谓“世界性”,是“有缺陷的世界性”,都应从真实的原本出发,对现成的理论进行选择、校正、扬弃、错位、综合、超越甚至反抗,从而让思想之鱼从容出游,享受“鱼之乐”,享受原创性的智慧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