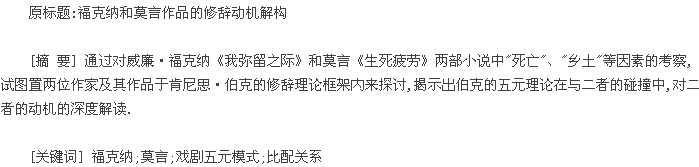
一、引言
被冠以美国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头衔的威廉·卡斯伯特·福克纳(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是蜚声美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作家之一.国外针对福克纳及其作品的探索可称得上全面且深入.不仅有专门研究福克纳的期刊(TheFaulkner Journal),专门以福克纳为中心的研讨会(如密西西比大学举办的一年一度"福克纳和约克纳帕塔法"研讨会),而且相关的论文和专着更是不一而足,例如,Sarah Mahurin提出在研究福克纳小说时,不仅应当留意未见因素,更应当留意缺场因素[1].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畅销多个国家,对许多文学大师产生深刻影响,如萨特、马尔克斯、沈从文、莫言.莫言受到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启示","大着胆子"将他的"高密东北乡""写到了稿纸上".[2]
关于福克纳和莫言的比较研究多围绕故乡而展开,多集中于乡土文化、故乡神话等方面,数量不是很多.现今比较详尽的一本是朱宾忠的专着《跨越时空的对话:福克纳与莫言比较研究》,该书从创作道路、文艺思想、作品主题、角色塑造等方面对福克纳和莫言进行对比研究,认为两者各有侧重,但莫言在人文关怀意识、艺术手法等方面比不上福克纳.[3]但张志忠在为此专着作序时指出该书过于倾向于意识形态方面.[4]本文将尝试从修辞角度进行两者的对比解读.
具体说来,在肯尼思·伯克搭建的大修辞新修辞框架内,通过伯克的戏剧五元理论,从福克纳和莫言作品中的"死亡"、"乡土"等指称意义切入,对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和莫言的《生死疲劳》进行阐释,解析主要因素以及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探寻两位作者的修辞动机.
二、戏剧五元模式下的因素比配
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在建构他的修辞理论体系时,运用"象征(symbol)"这个概念囊括了所有的语言标记和符号,通过"辞屏"(terministic screen)来戏仿阐释人们类似拍摄时镜头和滤镜影响的象征手段使用.词汇或者术语的本质决定了它必定是"现实的选择"(a selection of reality)和"现实的折射"(a deflection of reality).[5]
故而,"才使得目的和动机能够在象征行动中得到体现和实现".语词的运用,或者说"象征"的使用,出于不同的修辞动机、迫于不同的修辞形势,并非呈现本相,而是"不可避免地突出某些色彩、彰显某些特征,甚至歪曲某些形象".[6]
伯克构建的"表演"(act,或译为"行为")、"场景"(scene,或译为"情势")、"演员"(agent,或译为"施事者"、"执行者")、"道具"(agency,或译为"方法"、"手段")和"目的"(purpose)的戏剧五元模式(dra-matic pentad)正是观察解析话语和动机的绝佳"辞屏".其中,"演员"或者"施事者"或者"执行者"指完成某一表演或行为的个人或群体,不仅包括行为主体,还包括"共同施事者"(co-agent)以及"反施事者"(counter-agent)."表演"或"行为"包括所有带目的、有意识的行动或行为."场景"指的是施事者执行主体行动或行为时的大背景、处所势态等."道具"则是施事者完成"表演"或者行动的时候为达目的而采取的一切方法、工具或策略.而"目的"是指行动行为的目标或者期望取得的效果.可以这么说,此五种要素对"何人、何事、何处、如何、为何"作出了回答.[7]
而伯克凸显这些关键点是为了"揭示动机是在五大元素相互联系而形成的一个复杂动态关系网络内产生的".由任意两个元素"耦合"可以组成多个"比配关系"(ratio),例如"行动/情势"、"施事者/目的"等,各个元素"互相依存、渗透、转化".而对于这些关系的认知和使用能帮助我们"对感兴趣的某一象征行动的动机加以推测和确认",作为"一种话语或修辞策略",它可以感染受众、说服受众,"使之接受某一特定视角和观点".[6]
(一)死亡的表演
《我弥留之际》是福克纳的代表作之一,亦是其"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系列的着作中的一部.该小说主要叙述一位美国南方农民一家为实现妻子艾迪的遗愿-安葬在约克纳帕塔法的县城的娘家,经历了各种艰辛苦难.《生死疲劳》作为莫言的代表作品之一,通过土地改革时被枪决的地主西门闹以及他的六道轮回的化身驴、牛、猪、狗、猴以及大头婴儿的叙述和经历,涵盖了20世纪50年代到新世纪中国农村五十年的变化史.
两部书都紧紧围绕着死亡这个主题.死亡,对于看似主宰万物的伟大人类而言,永远是一场急欲挣脱却无法逃离的命运.在《我弥留之际》一书中,艾迪的死亡是作为导火索的一种行为,一种"表演".围绕着艾迪的将死和死亡,共同施事者们接二连三出场.杜威·德尔用扇子给躺在床上的艾迪扇风,卡什寻找合适的寿材,后在窗下为艾迪制作棺材,考虑到各种因素,把它打造成斜面交接形的,而在艾迪死亡后,一家人为按照她的遗愿将她送回娘家安葬,踏上了磨难不断的征途:卡什为救落水的棺材一条腿被压断,达尔被关进了疯人院,朱厄尔不得不失去了心爱的马;德尔被药房伙计欺辱等等.
莫言在《生死疲劳》的开场就提到人死后去往的阴曹地府,而后又描述了西门闹死亡当天的场景--"他们用一杆装填了半葫芦火药、半碗铁豌豆的土枪,在距离我只有半尺的地方开火,轰隆一声巨响,将我的半个脑袋,打成了一摊血泥,涂抹在桥面上和桥下那一片冬瓜般大小的灰白卵石上……".[8]
接下来的故事更是由一场接一场的死亡和转世构成,西门闹转世成的驴、牛、猪、狗、猴,每一世的死亡都为下一世的再生作出了铺垫,为六道轮回埋下了伏笔.
根据伯克戏剧五元理论,我们可以将死亡作为一种"表演",那么在《我弥留之际》中,艾迪就是负责此表演的演员,他们之间就构成了施事者/行动这样的比配关系,而艾迪的丈夫、她的儿女们以及惠特菲尔德等邻居、路人组成了该行为的共同施事者和反施事者;在《生死疲劳》中,西门闹则是第一个表演死亡的演员,他与死亡之间产生了施事者/行动的比配关系,而由其转世而成的驴、牛、猪、狗、猴和世纪婴儿蓝千岁接续进行着此种比配关系,同时,原先属于西门闹的妻子们、长工蓝脸、蓝脸的邻居黄瞳、西门屯一度的最高领导人洪泰岳、阎王、牛头马面等都成为共同施事者或反施事者.福克纳和莫言都通过对各色人物之行为、语言、外表、内心的细微描写,让受众明确感知到人物丰满生动的性格和心理.通过这样的比配关系分析,不难看出两位作者对"人"的极大兴趣与高度关注.福克纳所感兴趣的是"人","对与他自己、与他周围的人、与他所处的时代和地方、与他的环境处在矛盾冲突之中的人感兴趣".[9]
他主张"作家就是要尽量以感人的手法,在可信的动人场面里创造出可信的人物来.作家对自己所熟悉的环境,显然也势必会加以利用".[10]
莫言认为"人的命运和遭际,以及在动荡的社会中人类感情的变异和人类理性的迷失"应该予以关注.[8]而"一部文学作品要想激动人心,必须讲述出惊心动魄的故事",必须"塑造出性格鲜明、非同一般的人物".
(二)乡土的场景
作为《我弥留之际》故事发生的大场景,20世纪早期的美国南方,经济两级分化严重,对于贫穷的白人而言,生存环境极为艰难,不仅要在恶劣的天气和贫瘠的土地中挣扎求存,还须忍受富有白人甚至黑人的轻视.小说开卷即展露了落败的乡村场景,"棉花房是用粗圆木盖成的,木头之间的填料早已脱落.这是座方方正正的房屋,破烂的屋顶呈单斜面,在阳光底下歪歪扭扭地蹲着,空荡荡的,反照出阳光,一副颓败不堪的样子……(The cotton-house is of rough logs,from between which the chinking has long fallen.Square,with a broken roof set at a single pitch,it leans in emptyand shimmering dilapidation in the sunlight...)".[11]
而当时南方社会的农业本质属性决定了那片土地是人们生存的基础,在那片土地的情境中衍化出人们惯常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传统.
《生死疲劳》的主要场景也是依托于乡土--高密东北乡.整个故事也是围绕高密东北乡的农村土地改革展开的.里面的主要角色,无论是西门闹,还是蓝脸,都对这片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比如西门闹被鬼差带到人世投生时,提到对于高密东北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甚至了解"高密东北乡沼泽地开放的小花".[8]
西门闹很自豪地认为,"我虽是高密东北乡第一的大富户,但一直保持着劳动的习惯.三月扶犁,四月播种,五月割麦,六月栽瓜,七月锄豆,八月杀麻,九月掐谷,十月翻地,寒冬腊月里我也不恋热炕头,天麻麻亮就撅着个粪筐子去捡狗屎".年迈的蓝脸和转世为狗的西门闹躺入那一亩六分地中的墓圹,长眠于他们热爱的土地,陪同他们葬于墓圹中的还有土地上生长的珍贵农作物-麦子、豆子、谷子、玉米.正如墓碑的碑文所书,"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
美国的达维德·敏特曾这样评论福克纳:"福克纳比包括罗伯特·弗罗斯特在内的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一个美国大作家都更具有一个地区的乡土性.[12]
他是我们伟大的乡下人……然而他对自己出生的地方却恋恋不忘."而中国的张志忠如此评价莫言:"莫言,是一位从小在乡村长大、长期参加农业劳动、从里到外地打上农民印记的作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上仅见的农民作家.这不仅在于他对农村的熟悉,更在于他有农民的血统、农民的气质、农民的心理情感和潜意识……他的每一个毛孔里散发着热烘烘的乡土气息."[4]
当我们把福克纳和莫言各自的文学化后的故乡作为场景,并将情势/行动、情势/施事者等比配关系引入分析在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高密东北乡上发生的各种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可以感受到,经过福克纳和莫言天翻地覆似的解构和重构,现实故乡和文学故乡的拆放和交织,他们的乡土上生活的人物、发生的事件变得更为鲜活生动,引起受众更大的共鸣.
三、结语
福克纳在访问日本时对于为何把人描写得如此卑劣的回应恰恰解释了他创作的修辞动机--"那就是我太爱我的国家了,所以想纠正它的错误……设法显示它的邪恶与善良之间的差别,它卑劣的时刻与诚实、正直、自豪的时刻之间的差别……我们必须把邪恶的方面告诉人民,使他们非常愤怒,非常羞愧,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去改变那些邪恶的东西".[13]
这样饱含人文关怀的创作动机也处处渗透在莫言的创作中.正如莫言认为一个"有良心、有抱负"的作家应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进行他的写作","为人类的前途焦虑或是担忧",应该思索"人类的命运".
福克纳和莫言的作品相比较之下,可以发现,尽管二者所处的国度存在文化、民族、历史上的千差万别,其创作的修辞动机和修辞目的却有着不约而同的相似,无不投射出作者的主观意识,反映着作者对社会、历史和文化状态的关注.
对他们修辞动机的解构有助于拓展两者的研究视野.福克纳和莫言在各自的小说中,在以乡土为大幕的"场景"中,为达到各自的"目的",出色的"演员"们利用不同的"道具"尽情"表演",演绎出一曲曲悲欢离合.两位作者,可以说,将伯克所搭建的"比配关系"发挥得淋漓尽致.
参考文献:
[1] Sarah Mahurin. William Faulkner and the Seduction of the Unscene[J].Arizona Quarterly:A Journal of American Literature,Culture and Theory,2012(2):33-62.
[2] 王蒙,余秋雨,莫言,等.大声的自由[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3] 朱宾忠.跨越时空的对话:福克纳与莫言比较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4] 张志忠.莫言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5] Burke,Kenneth. 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
[6] 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7] Burke,Kenneth. A Grammar of Motives[M].New York:Pren-tice-Hall,Inc.,1945.
[8] 莫言.小说的气味[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9] 肖明翰.威廉·福克纳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10] 李文俊.福克纳评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11] 威廉·福克纳.我弥留之际[M].李文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12] 达维德·敏特.圣殿中的情网-小说家威廉·福克纳传[M].赵扬,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13] 李文俊".他们在苦熬"-关于《我弥留之际》[J].世界文学,198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