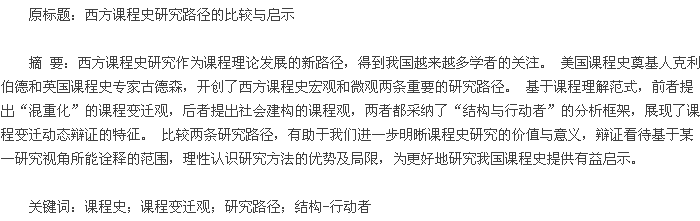
近年来,随着西方课程史专着的不断译入,我国教育界学者开始借鉴欧美研究路径尝试研究中国课程史。 被教育史视为“黑箱”的学校课程内在运作机制成为课程史关注的首要对象,学者们开始注重研究潜藏于课程背后的价值预设、 利益争斗及知识控制等。
然而, 由于主观意识的渗透和不同价值取向的影响,目前研究课程史仍缺乏一种科学、系统、有机的方法论,而处于机械、无序和简单化的窘境中。[1]
因此,如何合理地借鉴西方课程史研究方法,并有效地应用于我国课程史研究中,成为当下重要的议题。
美国课程史奠基人克利伯德和英国课程史专家古德森,开创了西方课程史宏观和微观两条重要的研究路径。 比较两种经典路径,可以发现,两者都秉持课程理解范式下的课程变迁观, 都不约而同地采纳了“结构与行动者”的分析框架,展现了课程变迁动态辩证的特征。 审视这一研究方法,我们需要回溯课程史研究的重要使命及理论基础,辩证看待课程史所能诠释的范围及研究价值,理性认识研究方法的优势及局限,为更好地研究我国课程史提供有意义的启示。
一、课程变迁观:“混重化”与“社会建构”
引入社会学“变迁”概念,是课程史不同于教育史研究路径的重要方面。 社会变迁理论从主张社会过程的必然性、必要性和不可逆性的机械发展框架,演变为强调人类的能动性、 事件的偶发性和未来的开放性。[2]
具体而言,研究社会变迁正在从宏大的历史架构转向阐释具体时间地点发生的“社会事件”,关注由个人或集体这些不同的行动者所引发的变迁。 基于此,克 利 伯 德 和 古 德 森 分 别 提 出 了 “ 混 重 化 ”(hybridization) 和 “ 社 会 建 构 ” (social construtionistperspective)的课程变迁观 ,试图从不同维度 、 不同层面解释课程历史发展过程的复杂性。
1.克利伯德关于课程变迁的“混重化”
克利伯德以美国课程历史脉络为主要研究范畴,关注的是重要课程学说和课程运动的历史发展,探讨各种利益团体和学派在这一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斗争与努力,偏向于宏观层面的课程史研究,代表作为《1893-1958 年的美国课程斗争 》( The struggle for theAmerican curriculum: 1893-1958)。
他引用社会学术语“混重”来说明课程变迁过程中受到各种意识形态、教育主张或学说交织、混合影响的现象。 这一观念是在反思、批判、解释课程钟摆效应和课程进步发展等结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他认为课程变迁中的每一种改革都具有特殊性,不能简单地根据主流课程意识形态对改革本质进行单一的、整体的判断,持课程钟摆效应与进步主张的研究者忽视了改革的复杂性与不可预知性,因此他从“混重”观念出发诠释课程改革的复杂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课程变迁观。
他以溪流为隐喻,将课程改革理解为“一种含有数股水流的溪流,一股又强过一股,从不会有哪股完全干涸,只有当气候和其他条件有利时,微弱或微小的川流才会取得更多的力量,而只有在促进新发现的条件不再盛行时,它才会式微”.[3]课程改革融合了各种努力,因而无法运用单一的尺度或标准去衡量。 克利伯德不否认改革的进步取向,但是反对透过一种概念去判断是否进步。 他提出“混合成功”的观点,主张以更为细致的方式考察课程改革过程中各种价值观,然后再分别探讨其对学校教育的实际影响,进而评估这些观念分别在哪个层面带来了进步或障碍。
克利伯德通过对国家层级的课程变迁、特定课程改革的组成内容,以及单一课程改革运动的变迁过程等方面的研究, 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混重化现象,故提出了“混重化”的课程变迁观。 他进一步指出,课程混重的情形与学校的公共性质有内在的联系,随着学校教育的普及化, 课程从私人领域转变为公共领域,课程不再是某一特定团体或族群的专利,越来越多的利益团体或个人有权参与学校课程的建构。 所以,克利伯德认为课程史研究目的不只在于探讨何种知识是真实的或有效的,更重要的是要针对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 将何种知识纳入或排除于学校课程之中;以及在此过程中,有哪些团体或人员参与其中,并发生哪些争执与辩论。 他主张的课程变迁混重化,充分反映了课程历史现象,不仅是各种理念的混合,同时也隐含了不同利益团体与实力的混合。
2.古德森关于社会建构的课程观
古德森以英国的课程历史脉络为背景,以学校科目演化过程为研究对象,基于生活史的视角将个别教师的生活历史与职业,和整体社会脉络及环境限制相联系, 探讨彼此的互动对课程变迁所造成的影响,偏向于微观层面的课程史研究。 其代表作为《学校科目和 课 程 演 进 : 课 程 史 的 研 究 》( School subject andcurriculum change: Studies in curriculum history, 中译本《环境教育的诞生》)。
他提出社会建构的课程观,是建立在批判课程处方观以及教育史研究弊端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他质疑从科学实证主义发展而来的课程处方观,认为其只是发展了一种理想的模型,而缺少对课程现象进行充分的解释。 他批判教育史研究课程发展,仅偏重教育外在因素,过度强调主流政治、社会力量对课程的绝对主导,而忽视了学校运作机制的内在制约。
古德森关于课程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学校层级的科目变迁。 他认为学校科目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概念,而以往研究常常采取哲学的观点,将其视为一种具备知识逻辑内在统一的学问,局限于学校科目演变描述既定事实,这是远远不够的。 对学校科目的理解,也可以采取社会学的观点,将其视为一种社会系统,是特定时期的社会建构物。 他指出,研究者在面对课程理论与实际时,要采取联结、对话和慎思的处理方式。 课程的社会建构除了要关照被规定的课程是如何建构,同时也要探讨它们是如何在实际过程中被协商与实施的。 换句话说,课程的社会建构要包括处方、实施、过程、反馈等方面,也要重视预设与生成、结构与主体,以及集体与个人的统整与对话。
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关注了不同群体和个人参与课程发展的协商、博弈与建构,课程史研究才显得鲜活和富有意义。 古德森认为课程史研究不仅解释了课程动态发展的过程,也提供了一个分析学校和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途径,因为学校科目变迁反映了社会文化选择是如何投射于学校的。 由此,课程史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对学校教育有进一步的理解。 另外,他认为课程史研究更为积极的目的,是对现有理论进行检验与再建构。 诚如他所言,课程史研究要能彰显历史 转 化 解 释 的 潜 能 (potential of transform ouraccount);[4]历史研究的角色应该去质疑及提供,有时要协助理论的产生。
二、分析路径:利益团体竞争与教师生活史
基于社会变迁的视域审视课程史,赋予了课程史研究新的问题、路径及方法。 在反思、批判早期工具理性价值观统摄下的课程研究时,克利伯德与古德森皆转向课程理解范式探讨特定历史时期的课程变迁,他们不再止于对“何时出现何种课程知识”或“谁的课程知识最重要”等问题的回答,而聚焦于“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课程知识是如何运作” 这一基本问题的探讨。
借鉴社会变迁理论,他们运用了“结构与行动者”的分析框架解释课程运作的历史过程,基于各自的研究问题及假设寻求影响课程变迁的动力机制。 克利伯德主要关注利益团体之间的竞争对国家课程的影响,古德森则从教师生活史的角度探讨教师个体及群体与学校科目相互作用的过程,展现了两条课程史研究的分析路径。
1.结构与行动者互动关系的分析框架
结构和行动者是社会学中的一对核心概念,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都可以归结为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课程变迁也不例外。 在社会学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着“强社会-弱个人”和“强个人-弱社会”的争论,体现在方法论上即整体与个体、客观与主观、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二元对立。 社会学家布迪厄和吉登斯试图超越社会制约性与个体能动性对立的争论,从挖掘社会与个人的互动关系上寻求两者的关联性和一致性。 布迪厄提出“惯习”概念将社会结构和行动者联系起来,“惯习是一种结构形塑机制,是社会行动者所具有的对应于其占据的特定位置的性情倾向, 惯习是一种生成结构,不仅塑造、组织着实践,并且生产着历史。 ”[6]吉登斯提出“结构二重性”的观点,认为社会结构既是行动者实践的媒介,也是其结果。[7]
克利伯德和古德森以“结构与行动者”的互动关系,来解释课程发展历史过程中所展现的动态辩证特性。 克利伯德分析了美国 20 世纪各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出现的不同利益团体如何参与学校课程的争夺。 他关注教育场域中横向之间的结构与行动者的互动。 古德森的分析路径则要复杂些,有横向互动,也有纵向互动。 横向方面不仅关注教育系统内部不同科目亚群体之间的互动,也关注教育系统内部科目团体与外在行动者的互动;同时他还以官方课程为“结构”,分析学校一级的行动者如何转化官方层级的课程,探讨了课程纵向的互动关系。
2.克利伯德关于利益团体竞争的分析路径
克利伯德关注横向之间的互动与其研究问题及研究对象是密不可分的。他在《1893-1958 年的美国课程斗争》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其分析路径主要是以利益团体的理论架构, 诠释课程变迁背后的各种斗争。
一是根据一致的意识形态及立场确定教育改革的利益团体,进而分析每一个利益团体对进步教育所作的诠释;二是在地位政略(status politics)的脉络下诠释各种利益团体如何争夺学科课程内容及形式,以及他们所珍视的价值与信念多大程度上被认可。[8]
台湾学者杨智颖在分析克利伯德其他作品的基础上,又补充了两条分析路径:一是政经社会结构和利益团体间互动的关系,二是中央层级的课程方案与地方行动者间互动的关系。[9]
克利伯德认为,利益团体之间的竞争会架构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脉络中,主流课程思潮的形成来自于社会结构与利益团体之间的互动。 虽然每一个历史阶段主流课程思潮的支持者都会企图去影响学校课程,但是并不会形成一种线性指导的关系。 在学校场域中,学校行政人员通常会在彼此矛盾的课程取向中采取政治的权宜之计(political espedient)。
3.教师生活史的分析路径
古德森在课程史领域研究独树一帜与其对生活史视角的强调和方法的开发是分不开的。 关注教师生活史,与他所持的社会建构课程观是一脉相承的。 他意识到影响课程实施效果及发展过程的核心因素是教师群体,然而每一个教师都是不同的个体,不同的职业经历、生活阅历形成了教师具有差异的教学观念与教学行为。 因此,课程研究不仅仅单纯地关注教学内容、课程设置等公共性、静态文本,而需要与教师个人生活紧密相连的动态分析。 他批判传统社会学实证主义模式忽略了行动主体的声音,而互动论与人种志方法论又过于关注情境与场合,忽视了与历史过程的联系。 他所提倡的生活史恰恰弥补了这些缺憾。 通过对教师个人传记、 观点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并与历史、社会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了基于教师生活史个体观照基础上的学校科目社会史的视角与方法。 他在《环境教育的诞生》一书中,通过对担任“乡村学习”科目教学的教师卡森进行访谈, 并结合他的信件、日记以及相关的会议记录、调查数据、文件档案等资料,研究了该教师生涯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观念和行为是如何影响该科目变迁的,同时社会结构又是如何限制该教师的决定的。
古德森所提倡的生活史视角,仍是基于结构与行动者动态辩证的方法论。 他设计了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个人生活层面,演变的过程是透过个人生活史的偶发情节和长期社会化过程;第二个层面是团体或集体层面,主要视专业、范畴、科目或学科的演变为一种社会运动,它同样会影响学校和教室中稳定和改变的形态;第三个层面是关系层面,针对不同时期,介于个人之间、团体之间,以及个人与团体之间关系的各种变动。[10]
古德森构思的分析路径,可以视为运用社会史研究方法于学校科目变迁研究中的一种尝试。 社会史学者科尔认为社会史是结构史与历史的结合,“关键在于将结构以及过程与行为以及经历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在历史上变化的、相互折射但不相互吻合的关系”.[11]
古德森关于教师生活史的分析路径始终是基于社会结构的大背景对两者动态辩证关系的探讨,目的在于了解学校科目被界定与建立的详细历史过程,同时验证、解释、修正所提出的研究假设。①
三、比较分析与启示
上述两种研究理路,突破了历史编年体的叙述史学方法,表现出某些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他们转变了传统历史编纂的角色, 不再仅仅承担史实的收集者、组织者和讲述者,而是带着自己的视角和理论观点去揭示课程背后特定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 学习借鉴要立足自身根基,在比较差异中取长补短,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课程史研究跳出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活力,另一方面不能忽视基于课程理解范式下课程史研究所面临的新问题。
1.研究目的:“以史为鉴”的再认识
以古鉴今,以史明镜,是我国古代流传至今的治史传统,似乎已然成为我们对课程史研究目的先入为主的观念。 如有学者认为,撰写课程史是课程研究者对“课程的过去”的一种叙述、形塑、重构和创造,是为了解决现实的课程问题或矛盾而回望过去,并寻求拯救之道。[12]
然而,慎言为今天的课程求解救之方,早已成为西方课程史学者普遍接受的观点。 课程史研究先驱阿诺。A.贝拉克(Arno. A. Bellack)甚至称之为“福音之罪”,②告诫人们理性认知课程史的研究结论。 那么,如何理解课程史研究的现代意义?
对课程史研究目的的重新界定,不得不从上世纪后半叶课程史在欧美兴盛的背景说起。 课程史研究会在美国成立,主要动力在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小学课程改革的主导权被学科专家夺取,课程理论陷入发展危机,美国学者开始转向历史研究的路径来重振课程理论的生命力,反思课程开发范式“非历史”之局限进而重建课程理论成为课程史研究的内在追求。 然而受概念重建运动影响, 课程领域的同一性陷入了危机。
阿普尔转换了斯宾塞之问, 提出 “谁的知识最有价值”,尖锐批判了传统课程被掩盖的政治本质。 课程不再作为理所当然的科学知识, 而被视为一种 “文本”(text) 并以不同的方式被确认和分析。 起初,对于课程理论重建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课程内涵的无限度扩张导致话语“混乱”却是学者们始料未及的,其所带来的不稳定性、 冲突性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课程的本质。
因此,基于课程理解范式下的课程史研究能否提供历史教训,受到学界高度的质疑,使得课程史研究的旨趣只能停留于“理解”层面。
目前关于西方课程史研究的意义,有学者总结了七个方面:①提供课程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复杂关系;②在历史背景下探究某个特殊时期的课程为何被教,是如何被教的,以及是为谁的利益而被教;③理解过去的课程是如何限制目前课程发展的;④为现在及未来课程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⑤提供学科的正式结构背后的人类活动的过程与动机;⑥帮助理解目前课程发展模式的评价;⑦协助了解已经被界定的专业与个人生活的历史。[13]
另有学者归结为四个方面:①为更好地理解学校教育的全面发展提供材料;②阐明与课程改革相关的过去的问题及相应的对于明智的实践的重要性;③具有批判的功能;④对理论建构具有作用。[14]
由此可见,课程史研究意义与价值并非直接解决当下课程实践所存在的具体问题,而更为强调从不同的视角对过去的课程进行诠释, 并赋予某种新的意义,强调的是反思、批判的理性意识。 今天的研究不同于早期的目的,在于注重课程学术品位的提升,关注课程理论的建构。 以往研究往往偏向于解释一些特定的事件,进而描述课程发展过程。 今天的课程史研究一般较为关注研究假设的验证与理论的测试,进而发展并建构新的理论。 古德森对英国环境教育科目的考察,提出的三个研究假设分别来自不同学者课程研究的理论观点,他通过研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验证与修正。 克利伯德和古德森都认为,可以通过历史个案研究来达到理论建构的目的。
所以对于课程史研究来说,需要重新定义“以史为鉴”的内涵,使之在促进课程理解,提升课程工作者反思批判意识的基础上得以实现。[15]
开展我国课程史研究,需要树立理性审视的反思意识,拥有多元理解的开放胸怀,在研究路径、方法论上下功夫,进而协助教师理解学校课程的实际状况,不断建构、修正和完善课程理论。 这才是课程史研究所应追求的“以史为鉴”的现代价值。
2.研究前提:视角及问题的再追问
课程史作为发生于课程理解范式下的一种研究路径,首要前提需要正视研究者的视角。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均是一种重构物(reconstructions),是历史研究者从自己的视角建构起来的。 课程史不是在讲述过去的历史,而是通过研究者的视角建构课程故事。
对研究者来说,理论视角影响了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也决定着他们分析问题的路径和方法。 曼海姆认为,“视角”不仅由思想形式决定,它也指那种纯粹形式逻辑必定会忽视的、思想结构中的质的成分。 观察者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的观点。[16]
对某一历史现象的关注程度往往因研究者的兴趣差异、经历差异而产生不同,从而得到不同的历史解释。 哈格里夫斯认为古德森对课程理论的创造性贡献来自于“边缘人”(marginal man)的经历。[17]
就研究视角而言,每一种理论都有其独特适用的对象和背后的基本假设, 本身也具有不断修正的功能。 至今仍没有哪一种研究理路可以全面诠释课程史的复杂性。 因此研究者在进行课程史研究之前,需要厘清是基于什么样的研究问题,以及采用哪些理论观点或哪些视角去思考研究问题。 “问题”存在于事物的不同层面,从大处着眼关系到事物的基本矛盾,从小处着眼关系到具体事件的争议。 克利伯德抓住了不同1实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 对课程不同层面问题的历史关注,展示了课程史学者发现历史的路径选择,多元视角提供了课程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多元的碰撞也推进了课程史的“客观”建构。
3.研究方法:“结构与行动者”关系的再辨析
“结构 ”与 “行动者 ”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所探讨的基本问题。 克利伯德和古德森引入这一对关系考量课程变迁的运作逻辑,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课程运作场域以及场域中结构与行动者互动形式的典型案例。 那么,我们还可以从哪些领域运用“结构与行动者”关系来分析课程史? 在课程变迁过程中,结构与行动者还有哪些可能的互动形式? 上述问题涉及了研究方法运用的范围, 需要进一步辨析的是研究方法的立论基础,即该如何理解结构与行动者的互动关系?
借鉴克利伯德和古德森的分析路径,我们可以从课程运作场域、结构与行动者互动方式两个维度分析课程变迁中可能存在的互动形式。 关于课程运作场域,具体有国家、地方、出版社和学校等,存在着不同利益群体对课程的角逐,可以分为教育系统内的场域和教育系统内部与外部所组成的场域;而互动方式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前者指在同一场域中,后者指从宏观场域到微观场域的转移,如地方或学校课程行动者对国家课程结构的实践与转化,因此会涉及不同的场域。对于结构与行动者关系的理解,社会学至今仍没有定论,不同的理论对两者互动关系给予了不同的解释。 曾占据美国社会学主导地位的功能主义强调宏大的结构体系,却淹没了行动者的微观活动,因而掉入了结构决定行动的理论预设陷阱。 在批判功能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结构主义、符号互动理论、结构化理论等,更多强调行动者的反思与实践,却也使结构-行动者关系复杂化了。
不同的声音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课程史研究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然而由跨学科发展所带来的学术专业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多元化发展的课程史研究呈现了理论基础多样化的发展态势,由于不同理论所使用的学术语言不尽相同,在进行课程史研究时,欲融合多个学术领域,势必遭遇“隔行如隔山”的学术专业问题。 如有学者质疑:“在脱掉‘忠实描述’的帽子而戴上‘社会冲突论’的眼镜后,是否应该或如何防止课程史使课程‘过度社会化',或者说给课程强加某些’意识形态‘? ”[18]因此,我们要审慎对待跨学科发展为课程史研究带来的活力,必须掌握引用理论基础的内在本质,防止“张冠李戴”、“贴标签”等弊病。
参考文献
[1]刘志军 ,王洪席。课程史研究:问题与展望[J].教育研究 ,2014,(8)。
[2](波)彼得·什托姆普卡。社会变迁的社会学[M].林聚任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6-7.
[3]Kliebard,H.The struggle for the American curriculum1893 -1958.Boston:Routledge&Kegan Paul,1986:208.
[4]Goodson, I. F. Subjects for study: Towards a social history ofcurriculum. In S. Ball & I. Goodson (Eds.), Defining the curriculum:Histories and ethnographies. London and Philadelphia: The FalmerPress, 1984:42.
[5]Goodson, I. F. The making of curriculum (2nd ed.)。 London:The Falmer Press, 1995:51.
[6]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83.
[7]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41.
[8]Kliebard,H.The struggle for the American curriculum1893 -1958.Boston:Routledge&Kegan Paul,1986:1.
[9][10]杨智颖。课程史研究观点与分析取径探析:以 Klibard 和Goodson 为例[M].高雄: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2008:82,121-122.





